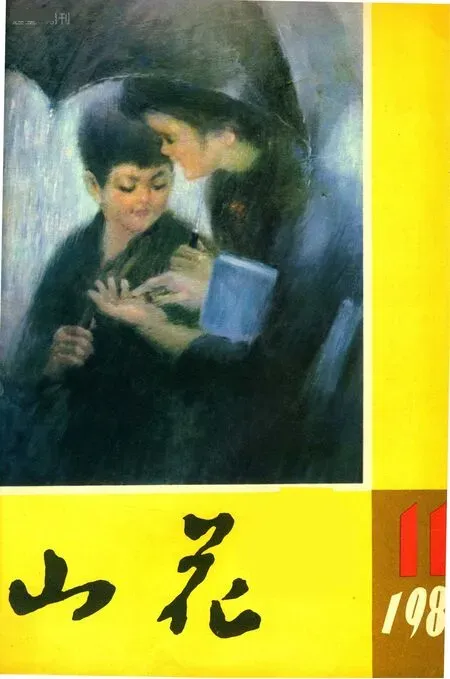地陷
光盤
地陷
光盤
付小清付小盆兄弟以及他們的父親失蹤四天后,村里人才猛醒過來。寧土坡立即帶上村里的中壯年人進山搜尋。他們一路尋找,一路叫喊,聲音在山林里回蕩。到傍晚,他們終于發現了地陷。地陷的位置非常隱蔽,如果不是聽見付小清的呼救,你就是經過它身邊也不一定發現得了。付小清用力大喊,快來人,快救命,我們在這里,我們快要死了!
初春的沱巴山區深處發生了地陷,父子三人乘電梯似的墜于離地面十幾米的洞底。這個地洞洞底面積十來平方米。地陷發生在連續暴雨之后陽光燦爛的日子里。
救援工作進行了數個小時。這些年寧土坡一直在城里混著,一直是沱巴山區外出務工人員的頭兒,就是在沱巴老家也有著極高的威信。寧土坡說,付小盆你一定要堅持,我們馬上救你上來!付小清說,小盆可能死了,他已好久沒說過話了。寧土坡吩咐人火速下山,去帶食物和繩子。留在原地的除了與付小清說話,還為他們提供水。地陷四周沒有水,他們尋過了,地陷四周只有比人還高的野草荊棘。寧土坡說,那我們輪流給你提供尿。但是剛開始兩個人的尿液都白費掉了。洞深有十幾米,尿在落向洞底時,并不能準確地落入付小清他們的嘴巴里。
我們能下去嗎?
天已經黑下來,洞下面的情況不明,不能貿然行事。而且下面的付小清說,很危險的,上面不時有泥土石頭掉下來。我父親腦袋就是在我們被困的第二天,被掉落下來的石頭砸中的。
你父親現在怎么樣?
死了。
小盆呢?
也快要死了。
返回村里的村民帶來了電筒,繩子和干糧。寧長興第一個被吊到洞底。在付小清的建議下,第一個救了付小盆。
付小盆已經死了。有人說。
不會的,付小盆是假死。他在洞里假死過好幾回了。好幾回我以為他死了,但喝過我的尿后又活過來了。付小清說。
無論生死,人們都不敢怠慢。但數小時后,沱巴衛生院的醫生說,小盆死了。付小清身體狀況不是人們想像的那么糟糕,他在醫院住了一天一夜就出院了。
人們在為父親清洗身子時發現他身上的肉殘缺不全,屠夫付全友說,這是刀子割的,我肯定!人們相信。就是說,父親身上的肉被人割了。
你父親的肉被人割了嗎?
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在付小清身上。付小清正低著頭,為父親擦洗身子,眼淚噼噼啪啪地往下掉。
我問你付小清,你父親身上的肉是你割來吃了嗎?!寧土坡說。
付小清轉身離開父親的身體。他弄來一些黑泥膏抹在父親身子上,最后這些黑泥成了父親身體肌肉的一部分,看上去父親就有了一個完整的身子。付小清愛好泥塑,在跟隨寧土坡到城里打工的這幾年,他見過無數的城市雕像,也有幸近距離地拜見過正工作著的雕刻匠(家)、泥塑匠(家)。這些藝術工作者通常都很熱情,他們會耐心地給付小清講解技術要領,甚至讓他親自參與泥塑活動。沱巴山區曾經有過泥人匠,但是沱巴的土質不好,工藝不精,泥人沒有市場,而且沱巴人自己也不愛擺放泥人,捏泥人技術就自然消亡了。當然捏泥人不等于泥塑像,這是兩個不同的藝術活動,都需要很高的藝術修養。
躺在棺材里的父親有模有樣,他那變黑的肉體與泥土同一顏色。眼神不好的人是不會分辨出這是一具有著一半黑泥巴的尸體的。
立在一旁的人們暗暗吃驚。
可是寧土坡卻輕蔑地說,泥就是泥,它能代替肉嗎?!小盆死了,很可惜,你呢,雖然活下來了,可你是怎么活下來的嘛!吃人肉,吃了親生父親的肉!你不是人,你是豺狼虎豹!
寧土坡的話很有煽動性,人們接著附和說,人不是野獸,就是餓死也不能吃自己父親的肉啊!
桃花吐蕾時,沱巴山區又像往年一樣安靜下來。青壯年成群結隊地跨過沱巴河走出沱巴,進入城市。留下來的都是老弱病殘,這些年,留下來的小孩也越來越少,打工的父母大都把孩子帶在身邊,花很大的代價讓他們進入城里的學校,或者至少進入打工子弟學校。孩子在身邊,對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很大好處。
付小清留了下來。他沒法不留下來。寧土坡說,我是不會再帶你進城的了,我從骨子里看不起你。離了寧土坡的帶領,付小清不知道能在城里干什么。他除了愛好泥塑,再沒別的技術。可是泥塑在城里怎么吃得開呢?城市需要雕刻,特別是藝術性很強技術性很強的雕刻。就付小清這水平,別說找工作,就是打下手人家都不要。
留下來也好。留下來后他就不用再看寧土坡他們的眼色,再也聽不到以寧土坡為首的人們對他的批判。付小清計劃為父親守孝三年,三年內,他拒絕看電視,打牌,喝酒,拒絕一切娛樂活動。初一、十五給父親上墳,平時家中香火不斷,供品不停。村上的留守老人們默默地看著付小清,對付小清的行為不作任何評價。
母親在三年前因病去世。父母留給付小清一座大大的瓦房,五六畝水田十幾畝甚至更多的地。茫茫沱巴山區,只要你勤快你就可以開墾出無數的田地。付小清只選擇離家最近的土質肥沃的水田,以及易于管理的地。他種水稻,也種沱巴傳統的旱煙、辣椒。
白天里沱巴村還略為有些聲音,而一到晚上整個就靜了。像一座無人的村莊,甚至像一座敞開的墳墓。村子的活力來自青少年,沒有青少年,村子就等于死亡。說這話的是寧代英,寧土坡的老父。寧代英76歲了,走路歪歪扭扭的,但說話還很有哲理,頭腦也還清晰。他還說,都外出打工,家鄉不要了嗎?付小清知道寧代英這話是說給自己聽的,但付小清裝作沒聽見。付小清沒有和任何人說話的欲望。

顧錚作品·拍點臺北夜晚吧
昏暗燈光下,付小清開始雕塑泥人。付小清試過了,認為沱巴丘的泥巴最好。沱巴丘是沱巴的一個地名。在沱巴,每一片土地,每一座山都有它的名字,它們就像城里的街道。對于一個農人,時間最多的是晚上,白天在農人眼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十分金貴的。在搶種搶插的時間里,付小清忙得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最后還是寧代英提醒了他:你人卵一條,種那么多田地干什么?付小清想,是啊,我一個人能吃多少呢?付小清就丟荒了一部分田地。可是田地是少了,白天里還是沒有一個所謂的空閑時間。他只能利用晚上來制作泥人。晚上時間漫長,只要有精力,你一直可以弄到天亮。但是晚上又是討厭的,它不能為你提供充足的光線。付小清晚上辛辛苦苦弄出來的泥人,第二天天亮一看,什么也不像。他總結出來,晚上只能打胚,白天才能制作泥人的五官。
付小清便開始大量地利用白天時間制作泥人。
沱巴一共有多少老人?好像還沒有誰正式統計過,雖然不知道具體有多少個,但用一群一伙一批來計數,那是沒錯的。這些留守在鄉村的老人們有的聚在一起打牌聊天,有的就拄個拐杖從東走到西,再從西走到東,有的哪兒也不去,守在自家門前呆呆癡癡地看著天空,或者遠處。這些從未有過城市生活經驗的老人,按他們的思維邏輯想像著遙遠城市里的兒孫。
寧代英不喜歡打牌,一打牌他就愛打瞌睡,而且總是輸。沱巴老人打牌從不賭錢,只求一個樂。但是不賭博并不意味著不認真,老人們對于輸贏非常計較。寧代英受不了老是輸的場面,輸了牌不光是沒面子,而要被人譏笑。這些年寧代英養成了游走沱巴村的習慣,由于走動,他就得到許多信息。付小清搞泥塑,就是寧代英在走讀沱巴村時發現的。
有意思,很有意思。寧代英在付小清家門前坐下來,眼睛望著正忙碌的付小清。付小清旁若無人地進行他的藝術創作,對寧代英不打招呼不讓座,更沒有沏茶敬煙。
你塑的是誰?
付小清手上的作品接近尾聲,他現在在作進一步的打磨。對寧代英的提問,付小清非常不屑。你塑的到底是誰?寧代英執著地再問。付小清停下,仔細打量手中的作品。他塑的是自己的父親,寧代英沒認出來,說明塑得一點不像。付小清站起來從不同角度檢查塑像,分析不像的原因。
付小清默默地坐下來,仔細回憶父親端坐時的神情。付小清是想塑一個坐著的父親來著。他想把這個坐著的父親放在堂屋,讓他深邃的目光永遠看著自己。當他找到泥塑不像父親的原因后,就把這件作品放在了一邊。這件作品再無修改價值。付小清弄來上好泥巴,第二次制作父親。
第二件作品不多久完成,但是寧代英還是以“你塑的是誰呢”表示否定。付小清一連做了五件作品,沒有一件得到寧代英的肯定。五件作品被他擺在堂屋里,看上去,他的堂屋就像一個工作室了。寧代英把付小清搞泥塑的事告訴了村里人,老人們就成群結隊地上家來參觀。
制作泥人干嗎呢?老人們小聲地議論著,生怕聲音大了嚇跑付小清的創作靈感。老人們有的是時間和耐心,他們坐在付小清家里一天天地見證著這項村里史無前例的藝術創作活動。
第八件作品出來后,寧代英驚訝地叫起來,你塑的是付冬才,你塑的是你父親!
付小清擦一把汗,滿意地笑了。第六、七件作品不能說不像父親,可是它沒有父親的神韻,讓人看不到一個活生生的父親。
成功地塑造父親之后,付小清信心大增。他接下來塑造母親、哥哥、爺爺奶奶。

顧錚作品·臺北“藍調”酒巴
又一個冬天來臨時,付小清完成了所有親人的塑像。他把這些塑像擺放在收拾干凈的西廂房里,他的家人或坐著或站著,見到它們付小清就像見到了活生生的親人,付小清因此不再寂寞。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在城里時,曾看過一則電視新聞,某一個地方把人塑成蠟像,那是一種除了不會說話,什么都像人的塑像。付小清想,如果能把親人們的膚色毛發也塑出來,就更理想了。
付小清去到縣城,買來顏料和有關調色書籍。如果有人點撥,或者有機會進行學習深造,付小清也許能成為一個優秀畫家,至少也會成為優秀畫匠。有關調色書籍付小清一看就懂,實際操作也基本沒走彎路。
深冬到來時,他完成了對親人的上色工作。那些來參觀的老人們一個個發出贊嘆:他們又活過來了!
接近年關,外出打工的陸續回來。與往年不同,有一位打工者開回一輛藍色豐田小轎車。主人是寧土坡。本來就很有凝聚力的寧土坡這下凝聚力更大了。寧土坡比所有沱巴人都有能耐,人家干不到工頭時,他干上了,人家干不上包工頭時,他干上了,人家開不了公司時,他開上了。今年年初他就在桂城開了一家裝修公司,成員一半以上是沱巴人,業務開展得非常大,許多寫字樓都上門來找他們裝修。寧土坡家里就天天聚集著前來祝賀和拍馬屁的人。酒香菜香時時從他家里散向沱巴四周。許多人去寧土坡家就不可避免地經過付小清家,見到了,免不了打個招呼,順便進屋去看看。還有人聽說付小清搞了一組親人塑像,他們也好奇地去參觀。這些人在寧土坡家喝酒時就談到了付小清,談到付小清制作的塑像。
寧土坡說,以前我對付小清是很器重的,他腦子靈人勤快聽使喚,但自從他吃自己父親的肉,我就徹底看不起他了。不管他有多能干,我都決不再用他!寧土坡這么一說,大家都不做聲了。他們不想因為付小清而丟了城里的工作。外出打工的沱巴人只要在桂城,都與寧土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要么是他公司的職工,要么是工程下的成員,要么是朋友的關系。總之,在桂城,寧土坡就是沱巴人的領袖。自然,回到沱巴,寧土坡仍然是領袖。別說在沱巴,就是在方圓十公里提起寧土坡,沒人不豎起大拇指的。付小清也會把大拇指豎起來。
沱巴的節日氣氛十分濃烈,而付小清家卻冷冷清清。打工的年輕人不愛上他家來,小孩們在大人的打罵下也不上他家來。有小孩偷著來參觀后回去說,他家有塑像。大人說,那是人嗎,那是鬼,見多了要倒霉的!而且他連父親都敢吃,小心把你們也吃掉!小孩就被嚇住了。
付小清想,幸好有活生生的故去的親人們作伴。有了親人們,他日子過得還算正常。他不跟村里任何一個人說話,他把所有的話語都用在了與塑像親人精神對接上。
村上人不敢在寧土坡家議論付小清以及塑像,但在自己家里卻悄悄地議論著。在該不該吃父親肉的問題上,他們不便作出結論。歷史上有過吃人肉的事件,可是他們吃的是別人的肉,非親人的肉。有人說,親人的肉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吃的。人如果為了活命吃親人的肉,已經失掉了人性,即使活下來也是野獸。話是這么說,倘若自己也處在那種危機時刻,會不會做出非人之舉?他們同樣也無法把握。因為他們會看著眼前的親人在心里反問自己,這一反問,心里就害怕。希望這樣的事件世世代代也不要有人碰上。那么,付小清搞親人塑像呢?他們也不好評說。在更多人看來這是毫無意義的。所謂壞事傳千里,好事不出門,付小清吃父親肉的事件已經傳遍了沱巴河流域。大多數人都對付小清的舉動表示出譏笑和痛恨。塑像呢?他們說,吃人的罪過,豈是搞幾個塑像就能洗清的!這種人該抓去槍斃,死后下地獄。

顧錚作品·理發時上海還算牌子?
“臭名遠揚”的付小清聽到議論,很多時候在半夜醒來,他希望再發生一次地陷,讓自己真正地餓死。
好在春節時間不太長,青壯年們在元宵后又陸續離開。沒了他們的議論,他的耳根這才清靜下來。
塑像工作開了頭,付小清就不想再停下來。他沒見過曾祖父曾祖母,但他想把他們塑造出來。他根據爺爺的樣子結合自己的推測,花二十天時間把曾祖父塑了出來。完工那天,他把塑像搬到屋外。這天天氣要陰不陽的,村道上很少有人走動。寧代英呢?他會出現嗎?付小清蹲在地上,靜靜期待寧代英的出現。一小時后,伴隨著一陣咳嗽,寧代英出現了。寧代英認為看付小清塑像是一種特別的享受,比看他們打牌強幾十倍。沒有特別事情時,寧代英總會如期到來的。
付尿桶,你塑了付尿桶。那是你的曾祖父啊!寧代英驚嘆不已。
付小清用懷疑的眼光看著寧代英。是你曾祖父,沒錯的!好幾十年了,你還記得!對了,那時候還沒有你呢!付小清終于認定寧代英說的是真話。因為付小清并沒有告訴寧代英塑的就是曾祖父,寧代英想說假話也無從說起。

顧錚作品·買書也這么急?
接下來,就該塑造曾祖母了。付小清花了許多時間去構思曾祖母。對于這個他從未謀面的祖輩,他在心中畫了許多草圖,當他最后確定時,竟然淚流滿面。二十天后曾祖母又塑成了。他仍然把塑像擺放在屋外接受寧代英的檢驗。
像,太像了!你曾祖母去世時就這個年齡。寧代英給予充分肯定。
村里的老人們聞訊,紛紛來參觀,他們對付小清的成果贊嘆不已。
付小清便沒日沒夜地進行大規模的塑像工作。他塑出了曾祖父的父親、爺爺,以及消失在歷史長河里的祖先。現在寧代英對付小清絲毫不懷疑,通過付小清的藝術創造,寧代英看到一個個活生生的祖先。
8月里的一天,一個陌生男人走進付小清的家里。陌生男人自稱老宋。付小清看不出老宋是什么身份,像農民又像鄉里干部,又像寧土坡那種不農不工不商的人。老宋對付小清的作品百般贊許。付小清心靜如水,他認為一個陌生人贊嘆自己的作品那是沒有道理的。他的作品不需要外人的贊嘆。
老宋給付小清敬煙,付小清不接,問話,付小清不答。老宋并沒有感到無趣,他自己在一張落滿泥土的板凳上坐下來。
老宋說,我是水晶礦的礦長助理,我們有大事需要你幫忙。礦上出大事了,鄭猛子被炸得面目全非。出了安全事故我們有責任,可鄭猛子沒按安全操作規程去做啊。上面來了人,賠償事宜雙方都談好了,可就是鄭家非得見到猛子的全尸,否則所有的條件他們不能接受。我們又不是孫悟空,到哪里去弄猛子的全尸去!這不,找你幫忙來了。
付小清走出屋子,他一言不發地去修補柴房。老宋跟在身后,說,價錢好商量,我們老板不是個小氣人。鄭家十幾個人住在礦上不吃不喝,以死威脅,嚴重影響了礦上的正常工作……你說句話呀,真急死我了。
老宋磨了一個多小時,說了一大堆好話。最后,他說,我忙得焦頭爛額,請你行行好,一定要幫這個忙。猛子的照片和我的聯系號碼我給你留下了,我再給你留下一筆定金,塑好猛子的尸體后,給我打電話。拜托啊!
定金和紙片被壓在凳子上,風吹過來,風想把這定金和紙片帶走。老宋那石頭壓得重,風沒奈何。接著出現的寧代英的目光隨風在定金上游走,他嘴巴咂巴咂巴響。那人是誰?這錢是他送來的?喔,對了,你是“啞巴”,問了也白問。付小清這才轉身細細打量那定金,好幾張呢,一不小心就是十來張。風撩起紙片時,露出了照片。寧代英忍不住湊近去,最后把照片拿在手上,說是個小伙子,不是姑娘,那人送小伙子和錢來干什么呢?如果是姑娘就有可能給你介紹對象。
付小清從柴房回到堂屋,繼續擺弄他的塑像。寧代英像往常一樣摸出煙袋,一邊自言自語地說,寧土坡給我買回許多香煙,那煙太淡,根本不是煙。我曾經戒過煙,戒成功了。但是看到你搞塑像我又來煙癮了。寧代英一邊說一邊吸,還一邊咳嗽。聽著寧代英時高時低沒有節奏的咳嗽聲,付小清喉嚨也癢癢了,緊跟著咳起來。
三天過后,老宋再次來到沱巴。這回有人看到了老宋開來的白色面包車,車廂是空的。隨老宋來的還有一個健壯的年輕人。老宋在付小清的家中轉了一圈后,臉色變得蒼白,嘴角的肌肉輕輕抽搐。當他看到壓在板凳上原封未動的錢、照片和紙片,暴跳起來,說你怎么沒塑像呢!付小清眼睛盯著老宋,老宋覺得付小清的眼中有一股火,盯在哪里,哪里就會燃的人即使躺著,在你手下也是活著的。你有一雙靈巧的手。

顧錚作品·街頭一景
老宋走后,再沒回頭。付小清盼望老宋快快出現,并把猛子拉走。一連等了一個月,初秋來到沱巴時,老宋也沒有來。老宋是不會再來了,他想。付小清將猛子轉移了地方。躺著的猛子和付小清的親人們呆在一起。
空下來的時候,付小清總是沒日沒夜地制作泥人。現在,他的屋子每個房間都堆滿了泥人。他塑了李逵李鬼,塑了曹操諸葛亮,深入人們骨髓的歷史人物正一個個地走進付小清的心靈,走進沱巴。
快要忘記老宋時,老宋卻來了。他惡狠狠地對付小清說,猛子的父母親還在我們礦上鬧著,我們雖然開了工,可是工作受到嚴重干擾。我還要告訴你的是,猛子的母親因為見不著猛子的尸體,已經瘋掉。
付小清倒吸一口涼氣。他把老宋帶到房間。老宋眼睛就亮起來,因為他看到了安然躺著的猛子。老宋激動地說,你都造好了,為什么不給我打電話?
老宋說,我本來是來興師問罪的,沒想到,你讓我喜出望外了。付小清配合著老宋把猛子抬到面包車上。一路上,老宋都在激動地說話,最后說,你怎么就不說一句話呢?你是啞巴嗎?老宋轉臉問寧代英,他是啞巴嗎?寧代英說,你才是啞巴。老宋說,那他就是個大怪人。
十來天后,老宋再次來到沱巴。他買來了雞和鴨,還有產自城郊的一大筐蔬菜。村里的老人跟隨老宋進入付小清的家。老宋說,你收下,一定要收下。猛子的事徹底解決了。猛子母親見到猛子的“全尸”后,不瘋了;父親平靜了。猛子所有的親戚都返回了家鄉。礦上為猛子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謝謝,太謝謝了!燒。老宋態度緩和下來,說,猛子的像你塑了嗎?塑一個躺著的猛子,三天前你默認了的。
付小清彎腰拾起定金照片和紙片,揮動手。他的意思是你們走吧。付小清揮動得非常堅決。老宋和年輕人后退了幾步,說,我知道你恨我們,我知道你認為我們草菅人命,可是事實完全不是你想像的那樣。我們的安全知識做得最普及最深入。是,猛子被炸死了,可是他怎么能吸著煙去檢查那插在炸藥里的雷管呢!我們多不容易,要錢,要多少,我們可以賠,可是要賠一具猛子的完尸,我們哪有辦法啊!你就幫個忙吧。看到我們開來的面包車了嗎?我們特意把車廂里的座位撬開,為的就是拉猛子的泥尸。我們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付小清再次揮動手臂。
老宋帶走了定金卻在匆忙中漏掉了照片。付小清拾起認真打量。這是個英俊的小伙子。他一下子就想起了付小盆。付小盆本來是可以不死的,可是他死了,因為固執。猛子本不應該死的,可是也死了,因為粗心大意。猛子一下子就牽住了他的心。
猛子的身高體重,付小清通過猛子的照片估量出來。這張全身照猛子可能在家鄉照的,因為他的身后有鄉村的風景。付小清開始為猛子塑像。
塑造猛子泥身的過程中,寧代英一直坐在一邊觀看,當十數天后猛子被完全塑好,寧代英止不住地咳嗽,然后煙桿指著泥人說,此人我好面熟,一定在哪里見過。付小清得意地笑了一下,從口袋里摸出照片。寧代英猛然醒悟,說是他,是這個小伙子!你怎么把他塑成睡像?
為猛子描色之后,猛子好像活著躺在木板上。
寧代英說,小伙子死了?小伙子一定死了。死了老宋緊握付小清的手。付小清心靜如水。

顧錚作品·從信義路看去的臺北101大樓
你有這么好的手藝,進入城市一定能賺大錢!你要愿意,我,我們全礦人都可以為你出主意!
付小清不置可否。老宋把一把鈔票塞到付小清手中時,付小清仍然像一根木頭立在原地。
秋雨綿綿,沱巴山區白天也有些涼。寧代英早已套上了外套。他身上的外套很時尚,在全沱巴也找不出第二件。寧土坡有錢,他在父親身上舍得花錢。而且在沱巴,寧代英是惟一在村里實現電器化的。寧代英仍舊吸旱煙,他寧可把寧土坡買給他的高級香煙送給村里別的老頭,自己也不抽。他拿起煙袋就會說,我抽不慣那無滋無味的東西。人們知道寧代英并不是作秀,寧代英一輩子都在做實在的人。
寧代英灑下一路咳嗽聲來到付小清家。
你還記得老六奶奶嗎?寧代英說。
老六奶奶是寧代英的老婆。
老六奶奶去世才5年,你一定還記得的。寧代英說。我要你幫我塑老六奶奶的像。老宋他們開礦,有錢,我是一個老山民,給不起你多少錢。但是你不要因為不能給你多少錢,就不幫我塑老六奶奶。
付小清低頭做他的事。
你成天不說話不吭氣的,到底是同意還是不同意?今天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我賴上你了!我沒有照片,沒有定金,也沒有電話號碼。我會天天蹲在你面前,守著你塑造老六奶奶。
說是這么說,剛開始寧代英并沒有蹲在付小清面前。在接下來的兩天時間里,寧代英都沒出現在付小清的家。其實這兩天的寧代英心里比沱巴河水都還要急。他一直在付小清家外轉圈,聆聽里面的動靜。他對村里的老人們說,付小清已經不是從前的付小清了,自從吃了父親的肉,就變了一個人,連聲音都沒有了。現在在錢少甚至無錢的情況下,付小清會答應制作老六奶奶嗎?
到了第三天,寧代英沒能控制住自己,他一頭沖進付小清的“工作室”。付小清正在制作一個胚子。
你做的是誰?寧代英說。他的心竟然咚咚直跳。
付小清轉動身子,擋住寧代英的視線。寧代英前進一步,說,你做的是誰?
寧代英就在凳子上坐下了。慢慢地,寧代英就笑了。
二十幾天后,老六奶奶制作完畢。老六奶奶溫柔地坐在板凳上,她手里正在做女工。上過色,老六奶奶就真的活過來了。寧代英滿心歡喜,要求付小清立即幫他扛回家。付小清將老六奶奶擱在廳堂里,寧代英對她動手動腳,嬉皮笑臉。
有了老六奶奶的陪伴,一連半個月寧代英都沒有離開家。老人們得知,成群結隊來參觀欣賞。
老六奶奶,你答應幫我做酒曲的,五年都沒做呢!
老六奶奶,再給我們講三婆娘的故事呀!
老六奶奶,下回趕圩我和你去,就你最有耐心。
老六奶奶,……
老六奶奶,……
…………
寧代英家充滿了歡聲笑語。
寧代英在第十六天上付小清家。
你老六奶奶好逗,她說竹籃可以打水,空麻袋可裝米。我說,你打水給我看呀,你裝米給我看啊。她笑呵呵地照做了。她居然能用竹籃打水,也能用空麻袋裝米。邪了門了!

顧錚作品·臺北“藍調”酒巴
你老六奶奶好兇,她要我戒煙。她說,你不戒煙我就不理你,我就離開你!我怕她離開我,我把煙戒了。也怪,煙戒了,我不咳嗽了,一餐能吃一大碗了!
你老六奶奶也真是的,說人都七老八十了,還睡在一起,讓后輩們見了笑話。你說這老婆子。你聽聽這些話,老六奶奶還是不是我老婆?!
付小清一下子領會了寧代英的意思,他丟下手頭的工作,著手制躺著的老六奶奶。這個工作付小清是背著寧代英做的。天冷了,他在身邊燒一盆炭火,手僵時,便在火上烘一烘。手烘軟了,接著又做。二十幾個日夜之后,付小清將風情萬種的老六奶奶送到寧代英的床邊。付小清用了最好的泥,這泥摸上去柔軟無比,像人的皮膚。寧代英喜出望外,他輕輕地摸了老六奶奶的臉,笑了笑,說,我說過你是我老婆,你會陪在我枕頭邊的。然后,寧代英就在老六奶奶身邊躺下了。
七爺走進付小清“工作室”那天,天空比較干凈,一群群候鳥飛過沱巴的上空。他坐在付小清的對面,手上拿著一支未點燃的香煙。七爺其實并不吸煙,年輕的時候就不吸。他現在手上拿著的香煙是寧代英散的。你知道,寧代英有許多香煙。七爺也不打撲克,能下地的日子他就下地勞動,不能下地時,更多的時候去到三公里外的竹海水庫。
七爺,你又去修水庫啊?
嗯呢。
七爺,你為什么老往水庫跑呢?
無語。
竹海水庫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修好了,沱巴地區那些無法享受到沱巴河恩澤的田地,就由竹海水庫來澆灌。為什么人們就愛說七爺“又去修水庫”?稍年輕以前,七爺是愛扛著鋤頭或鐵鍬去水庫的,到了水庫他會挖一挖土,壘一壘大壩。現在老了,他不帶鋤頭帶鐮刀,他用鐮刀修理大壩上的雜草。人們無法準確來定義及理解七爺的行為,就用“修水庫”來代替。
一縷陽光打在七爺臉上,他吸了吸陽光,說,我今年78歲,比寧代英大兩歲。本來老六奶奶是介紹給我的,我沒要,給寧代英撿了個便宜。老六奶奶是多么漂亮善良能干的一個女人!村上人以及介紹人對我十分不理解,老六奶奶更是不理解,她記恨了我一輩子。當我對介紹人說,我沒看上老六奶奶時,她就哭了,哭過之后賭氣地對介紹人說,那我就嫁給寧代英吧。就這樣,餡餅掉到寧代英腦袋上。寧代英臉上有許多麻子,又是個酒糟鼻,形象很不怎么樣。好在,人還算老實,也蠻勤快。寧代英知道是我把老六奶奶讓出來時,對我非常感激,他請我喝過三回酒,說,我們不愧是好兄弟。我和寧代英的確是好兄弟,我們一起長大,一起躲日本鬼子,一起參加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一起修竹海水庫。很多的“一起”,使我倆成為好朋友。
男人都搶著要老六奶奶,我為什么沒要呢?那時我心里有人了。她叫香麥。這是一個你從來沒聽過的名字。香麥是白寶公社的,她和許許多多人一樣響應上面的號召,前來沱巴修建竹海水庫。香麥像她的名字一樣全身散發著麥香。那年前來修水庫的人真多啊,大概有五萬吧。形勢浩大,到處彩旗飄飄。一師與二師,一團跟二團,青年突擊隊,鐵姑娘班,等等,師與師之間團與團之間,班與班之間展開勞動競賽,場面總是熱火朝天。
在近五萬人當中,我遇上了香麥。這就是緣分。那天有人在后面說話,從后面飄來的一股麥香味震住了我。
香麥。有人說。
我回過頭。我就傻了。
哦,香麥!
香麥停下腳步,她那雙月亮般的大眼柔柔地落在我身上,她一邊淺笑著,甜甜的,酥酥的,脆脆的。香麥從我身邊過去十幾分鐘后我才能邁動步子。
香麥所在的班組我并不知道,連她所在的師團營連都不知道。但是我一定要知道。有一天我想問寧代英,你知道香麥嗎?話剛到嘴邊我就止住了。寧代英怎么可能知道呢?再說,我不能讓香麥的名字從他的嘴里說出來。他的形象不好,暫時不配說香麥的名字。有一次我碰上一個操外地口音的姑娘,我問她,香麥在哪個連隊?她想了想,笑著搖頭。
近五萬人的隊伍分散在竹海的各個山頭,山水相隔,要找到香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時常去到與香麥相遇的地方分析香麥的駐地。可是,經過日日夜夜的思念,我把她的形象想沒了,只留下她麥香一般的味道。趁一個稍空的時間我滿山遍野去找香麥。我越過一兩道小溪,翻過兩座小山(這兩道小溪兩座小山后來被移掉成了蓄水的一部分),來到五團八連。好家伙,我一眼就看到了香麥。
香麥!我在心中大喊一聲。
聽到腳步聲,香麥轉過身子,對我笑了笑。而我低下頭,心狂奔亂跳。香麥走近我,說,你是哪個連的?我支支吾吾沒有說出來。她說,你來有事嗎?我搖頭。她說,我們見過,幾天前,在香水溝。
天啦,只一次,只一眼,香麥就記住了我!
呆了幾分鐘,我緊張地吐出幾個字,我在六團第五連。我叫盆書仙。
以后的日子,我時時盼望香麥到連隊來,可是她沒來。既然她不來,我就去。我利用別人休息的時間去到八連。香麥正與她的姐妹們打鬧,見到我,她臉紅了,羞澀地低下頭。可是她卻說,你來干什么?
她的姐妹也注意到了我。因為勞動,我頭上留著一小塊泥巴。香麥和她的姐妹們笑得滿地打滾。我不知道她們笑什么,就立在那里傻笑。最后,香麥對我說,過來洗個頭吧,洗了頭下午就更有精神,比賽絕對拿第一。我很聽話地走到茅棚邊的山泉水龍頭處,我摸自己的頭時才發現我“中標”了。香麥給我拿來香皂。我感覺香皂也是麥香味的。
可是,沒想到三個月后,香麥卻永遠離我而去。在沱巴修水庫,也像打仗,隨時都有危險。香麥就是被炸松的土方壓死的。為了趕進度,為了不落后于任何連隊任何人,炮響之后,他們就奔向土方……
得到香麥死亡的消息是在第三天。前兩天有關方面封鎖了消息。這三天時間內,我還準備去看望香麥的。第二天有一場文藝慰問演出,地點就在我們連,我要告訴香麥我為她占好了座位。這天中午革命的廣播如期響了。革命歌曲、政治口號、大好形勢之后,播出了香麥犧牲的消息。與香麥一起犧牲的還有三個青年小伙子,兩個姑娘。一共六人,能把六人同時埋掉,那是多大一個土方啊。
我眼前一黑,昏死過去。
香麥的死和別人的死亡一樣,人們談過幾天后就不再談論。人們看到的是未來,看到的是招展的紅旗熱火朝天的勞動競賽。有道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這有什么呢?只有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幾十年了,香麥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講述到這里,七爺停下來。因為激動,他的身子抖個不停。

顧錚作品·臺北228紀念公園
我想吸煙。七爺說。
付小清一動不動。在聽七爺講述時,付小清已停止了手中的工作。雖然看上去他的手在動在摸,其實心被七爺深深牽住了。最終七爺沒有得到火,香煙也沒有點成。
香麥一死,我就發誓,終生不娶。除非有一個一模一樣的香麥出現。后來的歲月里,人們給我介紹的不止老六奶奶一個,還有大豆、稻米、冬瓜等姑娘。可是,我心里裝的全是香麥,我非香麥不娶。我拒絕一個個介紹人介紹來的姑娘,身后就有了許多猜測甚至流言蜚語。有人說我心里有病,有人說我下面的東西不行。是的,為了對得起香麥,為了避免哪天我意志不堅定,我確實對我的下面下過毒手。也許它真的壞了。
香麥雖然在另一個世界,但我相信她是知道我對她的思念的。為了紀念香麥,天天能看到香麥,我用泥巴給她塑像。可是我不是那塊料,幾十年來,從沒有塑成過。香麥的眼睛像杏仁,眉毛彎彎的濃濃的;鼻梁很挺很直,略為有些鷹勾;嘴巴稍大了點,可是嘴唇薄薄的,左下巴有顆黑痣……
講述完畢,靜默十幾分鐘后,七爺起身離開。付小清見他步子比來時更輕松了。
那個半躺著的香麥在多日后一個雨天的正午全部完工。村里老人們結伴前來參觀。
七爺,你終生不討老婆,就是為了這個女人?七爺點著頭,老淚嘩嘩啦啦往下流。他用顫抖的手去撫摸香麥的臉,用滿是老人斑的臉緊貼香麥富有彈性的臉。
深秋過后是初冬,初冬過后,沱巴就冷了。村里老人好久沒見七爺的身影了。自從有了香麥,七爺總是深居簡出。人們發出善意的嘲笑,然后無限感嘆。見不到七爺沒什么奇怪,平時他就不愛與人玩。可是連續十天見不到七爺,問題可能就嚴重了。寧代英帶著幾個人弄開七爺的大門。
七爺死了。七爺緊摟著香麥,同在一床被子下。
七爺臉上有笑容。寧代英說。人們細看了,都點頭。七爺摟得香麥太緊,手掰都掰不開。寧代英說,分不開就不分了,就這樣讓他們一起進棺材。后在付小清幫助下,七爺摟香麥的姿勢有所改變。七爺仰躺著,香麥與七爺面對面嘴對嘴地壓躺在棺材里。
這下,七爺徹底滿意了。人們說。
七爺平靜地故去,給了寧代英一定的打擊。年輕的時候兩人關系很好,是發小。以后結婚生子,又同在一個沱巴大村,雖然接觸少了,但心里總有七爺的存在。七爺走了,寧代英更覺得七爺活著的重要性。因為七爺也占據了寧代英心靈的一角。七爺走了,那一角就空了。為七爺送葬,寧代英是惟一一個流了淚的老人。
因此,寧代英更珍惜自己活著的日子,更在乎老六奶奶的存在。在他心中,老六奶奶已經活過來了。老六奶奶能說話能干活,還能講故事。從七爺墳地回來,寧代英便在老六奶奶面前連呆了三個小時,又一次完成了與她心靈的對話。
我想看看我死后躺在棺材板上的樣子。有一天,寧代英對付小清說。
付小清在泥巴上畫了寧代英的去世像。
我不要這個,我要泥人。寧代英說。
付小清搖頭。

顧錚作品·臺北“巫云”酒巴掌柜老五
我死后,我也要老六奶奶躺在我身上,我要享受和七爺一樣的待遇。寧代英說。
付小清沒有為寧代英塑死后躺在棺材板上的像。這是他第一次拒絕寧代英的請求。
年關逼近,外出務工的沱巴人陸續返回。有一些人沒有回來。在外過年的沱巴人每年都有一些。他們有的是因為工作太忙,單位春節加班,有的因為害怕擁擠和不安全,總之都有充分的理由。這些因故不能回家的青年或壯年人,會給家里寄回一筆錢,還會給老人打一個電話。老人們理解子女,但內心總有那么一些遺憾和不滿足。
寧土坡的小車停在沱巴村頭,村頭就熱鬧起來。先期回到家的外出打工人員前來迎接寧土坡,有人為寧土坡開車門,這個開車門的人學著城里人的樣子,一只手護著寧土坡的頭。有人為寧土坡拿行李。寧土坡的老婆和一對兒女還有兒子的女朋友把車塞滿了。行李和年貨太多,他就叫人開回了公司的那輛面包車。村頭有些亂,剛開始人們沒有注意到這輛不起眼的面包車。寧土坡手指向面包車時,人們立即明白,那也是他此次返鄉的一部分。有人就朝面包車走去,開了門取行李和年貨。人們都對寧土坡一家問寒問暖,他們尤其關注寧土坡未來的兒媳婦。兒媳婦長得太漂亮打扮太入時,與沱巴格格不入,見到她,老人甚至在外打工的人員都感到暈眩。
在眾人的護衛下,寧土坡就停下來。他看到了父親寧代英。
爸。寧代英給寧代英鞠了一躬,然后深情地望著父親。
在場的人非常感動。在沱巴來說,寧土坡也算是一成功人士,大老板了。他很孝順。
寧土坡的兒女叫了爺爺,寧代英激動地答應著。
爸,你精神很不錯。是寧代英的兒媳。進城十幾年以后,兒媳一舉一動儼然一個城里人。寧土坡接過話,說,爸你越活越年輕了。寧代英說,說得沒錯,我的精神這么好,我自己也想不到。七爺去世后,我精神差過一段時間,但不久我又恢復了。
七爺去世了?寧土坡說。
是的。
得了什么病?
什么病也沒得,就去世了,走得干凈利落。寧代英說。
唉,說走就走了。寧土坡感嘆說。他一輩子真不容易,去世了也沒個送終的。
爸,你得好好活著。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什么要求你提出來,我們一定會滿足。現在我們家不像十年前了,我們有錢。兒媳說。
寧代英說,嗯。你們這么孝順,我不多活幾年,實在對不起故去的親人們。我要替他們多活,把兒孫們對他們的孝心全享用了。
人群中就發出了笑聲。
顯然,寧代英注意到了未來的孫子媳婦。孫媳主動地叫道:爺爺!寧代英說,好,好,好,時代畢竟不同了!
寧代英的話,人們不能完全理解。但人們并沒有深究他的話,大家的步子在寧土坡的帶動下啟動。
老六奶奶的坐像仍舊擱在廳堂里,這讓寧土坡大吃一驚。他捏一把臉上的肉,再咂巴眼睛,眼前的確是母親啊。
媽!寧土坡情不自禁地叫了一聲,然后“撲通”跪下。寧土坡除了孝順,還是一個感情非常豐富的男人。一跪下,就哭訴起來。

媽,想死我了,你離開家都六年了啊……
寧土坡的老婆兒女跟著跪下。看得出,沒多少文化的寧土坡家教還挺嚴。
現場不知情的人心里七上八下的。老六奶奶去世好些年了呀,這是怎么回事?知情的寧代英卻由著兒孫們。每年春節,少不了為列祖列宗供飯供菜進香,儀式都是跪著進行的。但面對的除了一個靈牌,并沒有實際的人物。現在老六奶奶的實物在這兒,內容就豐富而真實了。
哭訴一陣,寧土坡跪上前,他摸了摸老六奶奶的臉,發現是冷涼的,再一細看和連問幾句,才發現原來是塑像。
雖然是塑像,我們的跪拜也該也值。寧土坡對老婆以及兒女們說。
這個也太像了。我還以為媽又活過來了呢。寧土坡的老婆笑著擦拭眼角的淚水。
得意洋洋的寧代英一直賣關子,一家人酒過三巡時,他才揭了謎底。
是付小清的杰作。寧代英說。對了,我還沒付他錢呢。付小清為猛子塑像人家給了一大把,少說有五千。我們是一個村的,錢可以不給那么多,二千總得給的。所以還欠他四千。
四千?那還有一個呢?
寧代英說,是還有一個,你問這么多干什么。反正我們一共欠付小清四千。
寧土坡心里就不是個滋味了。他臉色當場變化,說,爸,好好的你塑什么像嘛。要塑也不能找付小清去塑啊!付小清是什么人?不,不是人,是一頭連父親的肉都敢吃的野獸!寧土坡當即丟了酒杯,氣呼呼地坐到一邊吸煙。
不就四千?我給,我賣了家具給!寧代英也來了脾氣,說付小清吃父親是吃父親,塑像是塑像,你不能扯到一起。
讓付小清給媽塑像,我們全家的臉讓你丟盡了!寧土坡不依不饒。還想讓我給付小清工錢?門都沒有!
這一夜大家過得都無滋無味。因為父子的爭吵,寧土坡老婆和兒女都感到空氣里彌漫著硝煙,氣氛十分壓抑。未來兒媳在一個角落對兒子說,你們家人怎么能這樣?我第一次上你們老家,就碰上吵架,心中很不爽。真后悔跟你來,我想明天就回去。
兒媳的話寧土坡聽到了,他大聲地說,爸你聽到了嗎,你看你干的什么事?沒有你做的這件蠢事,小碧對我們家印象會這么差?你不僅對不起全家,就連還沒過門的孫媳也對不起!
寧土坡一夜無眠,覺得父親做的這個事讓他吃了活青蛙一樣難受。第二天一早他就起了床。戶外,兒子兒媳在輕輕吵架,兩人的手碰來碰去的。寧土坡喝道,寧光輝,你是男人就要讓著小碧!小碧你也別生氣,有什么話對我說。都是爺爺不好,爺爺快80歲的人了,還干蠢事。
我沒怪爺爺。我覺得爺爺其實沒什么大錯,甚至是對的。我是說,你為什么對爺爺那樣?小碧說。爺爺老了,像小孩一樣,你不讓著點,反而氣他。
寧土坡欲言又止。然后灰溜溜地離開。我有錯嗎?我有什么錯?明明是父親有錯。寧土坡自言自語地說。看看他干的蠢事。他干的這件蠢事真的太蠢了。我從來沒有對父親大發雷霆,可是這回,父親干的事也太蠢了,蠢得到了我傷心欲絕的地步。

顧錚作品·臺北的一場民間音樂會
走著走著,就到了付小清家門前。付小清正在制作孫悟空,昨晚干到很晚,現在還沒起床。通過門縫,寧土坡往里瞧了瞧。里面光線太暗,什么也看不見。寧土坡拍拍門,里面也沒有反應。
寧總,早啊!有一個人經過。這個人在寧土坡的公司里干,按照輩份,這個人還是寧土坡的叔叔。可是他已習慣了叫寧土坡寧總。他生怕直呼寧土坡的名字甚至小名狗扒屎而丟了工作。
寧土坡心安理得地應了一聲,說,里面是什么?
來人說,聽說付小清成雕塑家了。
我呸!雕塑家,我看是敗家子!為了圖痛快,田里的泥都被他搞光了!
來人說,聽說付小清塑誰像誰。還把七爺幾十年前的女朋友都塑活了呢。
得到塑像,七爺就死了?
是的,七爺滿意而歸。
那是害了七爺的性命!
來人說,寧總說的也有道理。幾十年了,七爺沒死,偏偏得到女朋友塑像不久就死了。這塑像就像是毒藥!
對,總結得非常正確,塑像是毒藥!
付小清是殺害七爺的兇手。來人說。
說得好,去,告訴沱巴所有的人。付小清是兇手。寧土坡說。
吱啞一聲,大門開了。付小清打著大大的哈欠,他那一口煙牙明顯地暴露在寧土坡的眼前。
你讓人惡心!
看清門外站著的是寧土坡后,付小清欲將大門關上。寧土坡一腳插進門,付小清的門就無法關上了。
你能耐大長了,你居然塑我的母親,你居然塑七爺的女朋友并且害死了七爺!你從吃父親的肉開始就變成了禽獸變成了妖怪!你想從我這里要工錢?寧土坡揚起拳頭,說你看看,這是什么?看到了嗎?
氣憤中的寧土坡打了付小清一拳。清早血脈還沒有流通,而且又是冷天,遭擊打是最痛的。付小清痛得倒吸涼氣。
還手啊,有種的你還手啊!
寧土坡的聲音很大,一下就刺破了沱巴清晨的寧靜。許多人聞訊趕過來。此時付小清已經蹲在地上,嘴角在流血。
你怎么能惹寧總生氣呢?還不向寧總道歉!人們好心相勸。
付小清把嘴角流出的血吞回去,然后起身操起一把斧頭。見勢不妙,有人護住寧土坡。寧土坡也有些害怕了,他匆匆忙忙地罵著,但聲音小了許多,力度也弱了許多。
別跟他一般見識,犯不著跟他生氣。他是什么樣的人,沱巴人誰不清楚?他們把寧土坡架走了。寧土坡受了驚嚇。自從他有了錢后,口氣越來越大,膽子卻越來越小。想當初剛進城時,誰敢惹他,哪怕前面是公安局長,他也敢上前踢上一腳。有了錢,就覺得自己命值錢了,和人拼,很不值。但是不管怎么樣,你區區一個付小清也該低頭啊!
回到家,見到廳堂里老六奶奶的塑像,氣更不打一處來。多股怒氣集中在一起,足讓他歇斯底里。他順勢操了一根鐵棍,將塑像打得稀巴爛。
畜生,你是在打你母親啊!寧代英失聲痛哭。
寧土坡瘋了似的,打碎廳堂那具塑像不算,還滿屋子尋找另外一具。最終他在父親的床上找到了。寧土坡力大無比,他把這具塑像舉過頭頂,然后砸在地上,把塑像摔成幾瓣。

顧錚作品·臺北故宮正在舉辦大英博物館展覽
這個春節沒有過出一點歡樂氣氛。寧土坡早早地帶著全家離開了沱巴。父親說得對,我痛打的確實是母親。寧土坡時常在黑夜里回想那天的情景,一想就有針扎心。有幾回他夢見遍體鱗傷的母親向他求饒,嚇得他個半死。他認為那天自己太沖動了,他就是砸碎家里所有的東西,哪怕打兒女也不能打母親。他承認付小清塑得太好了,那舉止那神態活脫脫一個母親。
打碎了母親,還有臉留在沱巴嗎?
車子發動那一刻,他回過頭朝著村里,咬著牙說,付小清你給我記住,總有一天我要把你撕成碎片!
當時來為寧土坡送行的有許多人。他們除了祝他全家一路平安,完全沒有了迎接他回家時那么好的心情。所有人都知道寧土坡與父親關系搞得特別僵,也知道寧土坡心情低落到了最低點。
寧土坡一走,許多人也跟著離鄉。與往年相比,沱巴過早地進入安靜期。關于這個春節沱巴發生的事情,付小清一點不知道。他從來不串門,不和任何人說話交流。當聽到別人轉述說寧土坡要把他撕成碎片后,他在心里笑了,是一種陰冷的諷刺的甚至是勇敢的笑。
現在,泥塑像堆滿了付小清的幾個房間,并且數量在進一步增加。有一天他正在塑著時,看到七爺了。七爺手里還是拿著那根香煙。七爺說,你塑了一尊又一尊,塑來干什么呢?你不間斷地塑像,是你內心很孤獨嗎?付小清抬起頭來,可是什么也沒看見。可能是自己的幻覺,也可能七爺剛才真的來過。
按照固定時間給父親、哥哥上完墳,點完香,磕過頭,他來到七爺的墳地。七爺被埋在幾里外的山坡上,山腳下就是竹海水庫,就是香麥犧牲的地方。關于死后埋在哪里的問題,七爺沒有明確交待過,但他在不經意間向村里老人透露過。他說,我要永遠去修水庫。再結合他講的香麥的故事,寧代英就做主說把七爺埋在竹海水庫的山上。通向七爺墳地的山路已經被雜草覆蓋。當初本也沒有路,是埋葬七爺時,送葬隊伍踏出來的。
看得出,自從七爺埋葬在這里,就再沒人來過。七爺是五保戶,沒有兒女,只有遠方的親戚。遠方親戚確都顧不上自己的祖墳,就把七爺給忽略了。七爺孤獨地站在山的高處,守望著突然故去的香麥和瀅瀅的水庫。也許現在七爺是最不孤獨的,因為他身邊有香麥的塑像,山腳下有香麥的靈魂。他和香麥早已融為一體。
付小清跪拜在七爺墳前,上了香,他還放了一掛鞭炮。
寧土坡說我是殺害你的兇手,是嗎?付小清心里問七爺。如果是你就讓墳頭的草點一下頭,如果不是,你就讓它們搖一下頭。可是七爺墳頭的野草,一會兒點頭一會兒搖頭。付小清無法做出判斷。他仔細想了想,兩方面都有道理。他長嘆一陣,收拾貢品下山。
回到沱巴,付小清進入七爺的屋子。這么多年來,付小清首次進入七爺家。門是關著的,但沒上鎖。人們從這里把七爺抬走,就再沒人進來過。推開門,幾只老鼠向外竄出來,里面陰森森的,令人背皮發麻。付小清摸索半天,找到了開關,一拉,燈還是亮的。燈光下所有擺設如舊,仍像一個完整的家,可是,已沒有了人味。
從七爺家出來,他忽然有了為七爺塑像的欲望。他丟下手中別的塑像,趕塑七爺。他以最快的速度把七爺塑好。但是他仔細打量七爺時,總發覺少了些什么。后來意識到,少了香麥。他接下來又塑香麥。塑好香麥,他把它們搬進七爺的家。他似乎想讓人們永遠記住,這是七爺家,這個家里有過女主人的身影。是的,這個家一直有女主人的。這個女主人一直跟隨在七爺的身邊,活動在七爺的眼前。
完成這一切,付小清淚流滿面。
經過寧代英的控訴,付小清終于知道老六奶奶的塑像已毀于一旦。過去不久的這個春節,付小清朦朦朧朧地感覺到寧代英家發生了什么事。
寧土坡太狠心了,那是他母親啊!寧代英流著眼淚,激動地講述那天發生的事。當年破四舊,我們都沒這么狠啊!
付小清平靜地聽著,一刻不停地干著他手中的活。
你說句話呀,我都兩年多沒聽到你說話了!你干嗎不說話呢?
付小清搖頭。
寧土坡說,我病了。自從那不孝之子砸了你老六奶奶,我就病了。病得很重。我可能離開你們離開沱巴的時間不長了。昨晚七爺托夢給我說,快來吧,這邊比那邊好玩多啦!我當時答應了七爺。答應了,天收我的日子就快到了。
我真想看到我死亡的樣子。我知道誰也不可能看到自己死亡的樣子。只有你能幫人實現這個愿望。
十幾天后,付小清沒有給寧代英塑造死亡像,卻給自己塑了一個。寧代英說,這也不錯,你的死亡我本來是看不到了的,這下我看到了。死者為大,我向你鞠三躬吧。寧代英給付小清的死亡塑像鞠了三躬,燒了紙錢。但是付小清卻把自己的死亡塑像砸爛了。


顧錚作品·臺北捷運中
寧代英病得不輕,付小清想告訴寧土坡。但是付小清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思,他不能說話,他發過誓,為父親守孝的三年對誰也不可以說一句話。這是對自己嘴巴最大的懲罰。付小清希望寧代英自己給寧土坡打電話,讓兒孫們回家照料。但寧代英說話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會告訴寧土坡的!
寧代英給自己制作死亡塑像。寧代英笨手笨腳,塑像在他手下三不像。當他想重新塑造時,昏倒在地。付小清將寧代英扶起來。
我不行了。寧代英說。
這天正好有別的人在場,他們和付小清一起弄寧代英回家。寧代英全身涼冷,但他拒絕人送他上醫院。他說,我死后,想和老六奶奶在一起。
有人給寧土坡打了電話。寧土坡說他正在遙遠的西北出差,他說他馬上趕回來。就在給寧土坡打電話的那一刻,寧代英就去世了。付小清一直站在寧代英身邊,他又一次見到了一個生命的退場。那天,也就是困在地洞的第三天,受傷的父親在缺食缺水少藥的情況下,在付小清的眼皮底下離開人間。臨終前父親臉色蒼白,嘴唇焦黃,像死人一樣。父親是想說什么的,但他已失去說話能力。父親指指付小清兄弟,然后這只指頭收回來,橫擱在另一只的動脈上,來回拉鋸。因為三天來未進食物和水,付小盆付小清已是頭昏眼花,體力不支。兄弟倆并不明白父親的意思。父親再次艱難地重復了那個動作。兄弟倆仍然不能理解。父親臉上顯出更加痛苦的表情。父親準備做第三次時,昏過去了。付小盆付小清分別躺在父親的左右,父親昏過去后,兄弟倆就哭上了。他們以為父親已經死亡,所以以最大的力氣痛哭。但不多久,父親蘇醒過來。
父親精神意外地好,臉上有了紅潤,話也能從喉嚨里傳出來了。
這里離村莊太遠,這里平時根本沒人出現。我們父子只有死路一條了。我老了,但你們還年輕,你們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活下去。現在惟一的出路是你們把我殺死,喝我的血,吃我的肉。
付小盆,聽到了嗎?
不!付小盆說。我們一定能活著出去的。
付小清,你聽到了嗎?
我沒聽到。
我的傻兒子,快動手吧!父親大吼。但是父親這一大吼,耗盡了最后一點力氣,緊接著去世。
付小清兄弟無聲地哭著,然后都昏死過去。不知過了多久,付小清醒來了。緊挨著的父親已經冰涼。迷糊中他看到了一盤肉,一瓶水。我要吃肉!他對自己說。清醒后,他才發現又一回出現了幻覺。在城里打工時,他曾多次見過那個侯姓雕塑家面前放著一盤肉一瓶水。
此時,付小清聞到了那肉的香味。而且他想起了系在腰上的小刀。付小清艱難地打開小刀,又艱難而有耐心地劃向父親的大腿。父親的肉結構緊密,付小清費了很大勁才割下一小塊。付小清把這小塊肉送進嘴里……
付小清越吃越有癮,越吃越精神。
付小盆的身子動了一下,但他仍閉著眼睛。付小盆輕聲地說,我好像聽到你在吃東西。付小清說,沒有。

顧錚作品·臺北花博會上的表演
付小盆相信付小清沒東西可吃。可是隔不久,他又聽到了付小清嘴巴的咂巴聲。付小盆說,你是在吃東西嗎?付小清說,沒有。付小盆說,沒有就不要咂嘴巴,一定要保存體力,等待救援。
又一塊肉塞進嘴里時,付小盆終于肯定付小清在吃東西了。盡管腦袋缺氧,付小盆還是明白過來,他說,你在吃肉,吃父親的肉!
是的,我在吃父親的肉。哥,你也吃吧。我現在有些力氣了,我幫你割肉。
不!你這個禽獸!付小盆用力喊。因為激動和大喊,付小盆昏死過去。付小清爬起來,他感覺想尿尿。他掏出東西對準付小盆的嘴。
喝過尿液,付小盆體力有所恢復。他說,你這個畜生!你竟然吃父親的肉,天理不容,一定要遭天打雷劈。
我們只有吃肉才能活下去,才有機會獲救。
不!
付小清不顧付小盆的反對,將一塊肉塞進付小盆的嘴里,但是付小盆并不配合,相反極力反抗。
嘴巴是付小盆的,付小清怎么努力也未能讓付小盆吃上一塊肉。好吧,你不吃,我繼續吃,我能活著,你就能活。
又一天過去,十幾米高的地面上寂靜無聲。
有人嗎?救命啊!付小清用力喊。他每隔十分鐘就大喊幾聲。
這個地陷是突然發生的。地陷發生前,沱巴下了十幾天暴雨。地陷是否與暴雨有關,不得而知。當時父子三人進山采草藥,采著采著就走進了深山老林。父子三人草藥采得比較順利,他們坐在一塊石板上吸煙。一開始地陷是慢慢進行的,認真吸煙聊天的父子先前并沒發現地在往下陷。當他們發現后,下陷速度就越來越快。怎么回事?父親說。但是他們來不及了,幾秒后就被帶到離地面十幾米的地洞。伴隨著地陷,不斷有石頭泥土從洞口掉落。父子三人驚恐地抱成一團。地陷穩定,洞口不再掉落石頭泥土后,父親心也安定下來。關于地陷,沱巴以前發生過,但陷的并沒有這么深。我們要爬上去。父親說。父子三人仰頭,他們只看到高高的藍天,洞口的野草雜木在太陽背景下顯得模糊不清。父子三人分別往上爬。可是他們找不到支撐點。付小盆好不容易爬上了兩米高,突然又滑落而下。父子三人弄得筋疲力盡。看來是爬不上去了。父親說。我們喊救命吧。于是大喊。喊了一陣,除了聽到洞口上方不時傳來的鳥叫聲,沒有一點人的回音。父親說,我們不要一起喊,輪流喊。他們隔不了多久就輪流喊一次。但是這個季節進入深山的人太少,父子三人一次又一次的呼救都被密林吞噬。半夜時,地陷的次生災害又來了。不時有泥塊石頭從洞口跌落。父親就是被一塊石頭砸中頭部的……
時間一天天后移,父親身上的肉也一塊塊地少下去。付小盆仍然拒絕吃肉,他說我就是餓死也不會吃父親的一塊肉!付小清,不,你不配姓付,你是狗雜種,不是我們付家的人。
付小清說,父親的肉越來越腐爛,味道越來越不好,再沒人救,我們都得死去。你不要說話。你不要責怪我。你喝了我的尿,尿里面也有父親的肉。我們都是吃父親肉的人。
付小清堅持吃父親的肉,堅持對外呼救。他終于等來了救援。他的聲音與寧土坡他們的聲音相撞。順著付小清的聲音,寧土坡他們朝洞口奔來……
現在,付小清盯著眼前死后也不見平靜、甚至對死亡十分不服氣的寧代英(像父親一樣)。付小清下意識地摸到身上的小刀。這是他割父親肉的兇器。兩年來他一直帶在身上。一兩個小時后,寧代英的尸體完全退出熱量。付小清取下刀子,刀子在空中劃了幾個圈,然后就停在了寧代英的大腿上。多年后,付小清仍然對寧代英的尸體記憶猶新,慶幸的是手里的刀子沒有真的劃向寧代英的大腿。
寧土坡第三天才趕回家中。雖然是春天,但寧代英的尸體開始腐爛,難聞的味道飄在沱巴上空,令人窒息。有人告訴寧土坡,寧代英需要老六奶奶的陪伴。為了盡最后的孝心,寧土坡來到付小清家。
你聽到我父親臨終前那句話了嗎?寧土坡說。
付小清點頭。
聽到了你就照做吧!寧土坡以命令的口氣說。
付小清進到廚房。他從涼水里拿出一塊肉。付小清將它切成小片,配上辣椒老蒜炒成一盤菜。
寧土坡說,你太客氣了。我已兩天沒進食,現在看到這盤菜,聞到香味,便胃口大開。謝謝你。寧土坡還向付小清討了一盅酒。他坐下來,不緊不慢地享用起來。
付小清開始為老六奶奶塑像。事實上自從寧代英提出要老六奶奶陪伴,他就在為老六奶奶塑像了。付小清加班加點地塑造老六奶奶。
寧代英的尸體腐爛在加劇,不能再等了。盡管老六奶奶的塑像不是那么完美,但也只能將就。
三年守孝時間在不覺間過去。付小清最后給父親和哥哥付小盆上墳。上完墳,他將所有塑像擦拭一遍,然后關上家里大門。坐在村頭的老人們默默地望著準備出發的付小清。三年來,偌大一個沱巴村只有付小清這么一個年輕人。因為年輕人的缺席,沱巴就不再是從前的沱巴。
你也要外出打工嗎?老人說。
付小清不置可否。
都走吧,你們都不要沱巴就不要吧。我們都是快要進土的人了,我們什么也管不著了。老人說。沱巴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付小清的身影在老人們眼中變得模糊起來。后來,他們才發現,不經意間,他們都流了淚。
付小清來到桂城,這個他曾經多年打工的城市,三年后變了許多。但是,他還是很容易地找到了寧土坡。
見到付小清,寧土坡吃驚而憤怒地說,你來干什么?我說過,我從骨子里看不起你!我最敬佩付小盆!我一輩子也不想見到你,你滾吧!
付小清離開沱巴時就說話了。三年未說話,要恢復說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付小清做了很大的努力才學會像從前一樣說話。為了能順利地說話,他一路上都找人說話。
我是要滾的。付小清說。
你小子居然說話了,你這張吃了父親肉的嘴巴永遠也沒有資格說話!寧土坡湊近來。這是在他的公司,身邊全是他的人,所以他并不怕付小清動武。
你還記得那盤肉嗎?付小清腦中突然閃出一個惡作劇。
記得,怎么了?寧土坡說。那肉真是好吃。我一直沒猜出來是一種什么野味。在沱巴生活了幾十年,我什么野味沒吃過?可就是辨不出那個肉的味道。你要給我送那種肉嗎?我告訴你,你送來我照收,但我仍然看不起你,仍然要讓你滾蛋!
那不是野味,是你父親大腿的肉。付小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