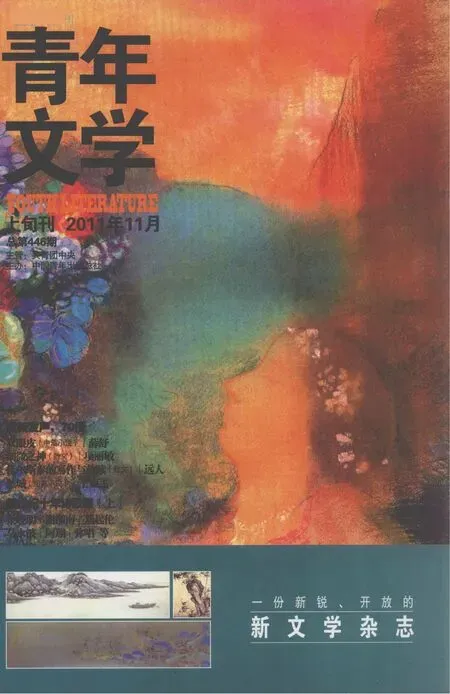尋找一只叫魯亢的紙老虎①
文/安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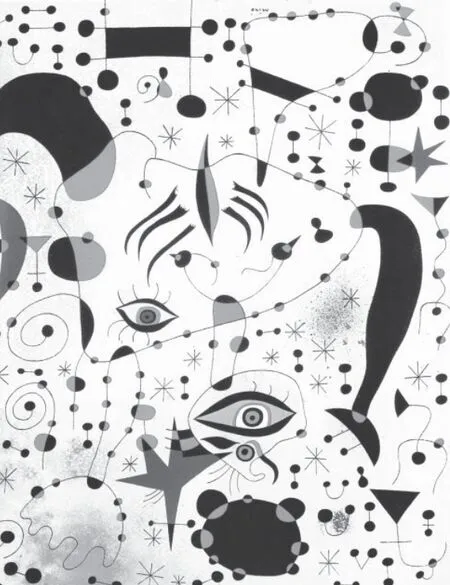
■美術作品:胡安·米羅
這是一個別開生面的另類文本,由三百零七則小對答構成,每則小對答包含有作者本人設置的標題、導語、提問與魯亢的回答四部分,簡短卻寓意深刻。
——題記
1)為脆弱的存在所傷。
此山并未逝世,你依然活在此山中,有逝世感的是你脆弱的心,它如此脆弱以至于經不起一段蹩腳存在的打擊。
——“請問魯亢,如何克服嫉妒?”
——“跑步和睡覺,即出汗和夢自戀,可解。天陰,將雨,慌。急跑。抱歉,無法多答了。”
2)情不情,不情之情。
哪一個角落都不足以承納你的悲涼,你把歡樂建筑在他人的空間里,一旦他轉身而去或允許另外一個又一個的人來此空間,建筑他們的歡樂,你的歡樂瞬間會變成股票暴跌后的深度套牢。
——“請問魯亢,無情麻木、有情卻苦,該有情還是無情?”
——“雨已歇,將進飯,暫答一二。先觀察敵情,再伺機而動。給有情一群哨兵,讓無情一路挺進。都行。”
4)吾生也有涯,而書也無涯,奈何?
昨日,聽從魯亢跑步解憂之計,帶孩子們漫步至書店。六層樓的書不禁讓人觸目驚心:一驚,自赴京后,因屢次搬遷貨物遺失嚴重,已不敢購書,因此也就很少讀書了;二驚,如此多的書窮盡幾生都無法讀完,不免凄涼之心頓起。
——“請問魯亢,人到中年,時日無多,閱讀和寫作,以何為主?”
——“以寫為母,讀乃腹中之孕,可懷經年而不生。受之,懷之,欲罷不能。安師,下若有題,黃昏共答。愉快之一天。”
5)不患冷熱,患忽冷忽熱。
連續一周不說話,對我這貌似愛說話的人來說,似乎是奇跡;但確實如此。我真的經常連續一周不說話,不是不想說,而是無人可訴。結果漸漸變成:心中波濤洶涌,口卻出不了一言。那種絕望異常平靜,也異常無奈。
——“請問魯亢,有人時嘈雜,無人時孤寂,如何是好?”
——“以好為好,以糟為糟,可棒喝凌亂內心。有人時逢迎,無人時吃它零食一片驚。人有病,多少給點兒沒來由的瞎關心。雖近黃昏,還在顛兒顛兒忙。天天‘請問’,雙目由亮轉灰,安師,不怕人嗤,只管玩得透腳才心甘。”
9)誰指使艾略特動了中國古代的黃昏?
黃昏的惆悵是中國古代留下的凝固畫面,直到艾略特用一句“正當黃昏像一個病人被麻醉在手術臺上”,黃昏的現代性才呈現出來。當今天艾氏的黃昏意象遭遇中國古代黃昏的同樣境遇時,我產生了返回去詢問的好奇。
——“請問魯亢,黃昏的麻醉感與艾略特有何關系?”
——“一日三碗,似昨日有約,吾已近似武二郎,且讓我過岡讓人睡。至于艾氏,彼時居療養院苦吟《荒原》,不光黃昏麻,全天皆麻。只取黃昏,恐為詩者之通識。‘讓夜來吧,讓鐘聲響起,時已逝,我還在這里。’”
18)恐懼有一副安的軀體。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所憂者眾,恐懼其一。對恐懼,海子有一個非常形象的表達詞匯:“動物般的恐懼”。你在閱讀到這個詞匯的第一瞬間就愛上了它,因為你也是動物的一種。
——“請問魯亢,如何解除對恐懼的恐懼?”
——“走神良久。無法消除。恐懼如影隨形,對它的態度只有‘戒審恐懼’。恐懼形同血液,入洞鉆坑,還是你自己。和它打成一片,若能左擁右抱,則還命運以青眼。與之是‘那樣的須臾不可分離’。快樂你今天。”
21)魯亢其人,說真是真,說假亦假。
小學生回家跟爸爸說:“爸爸,今天老師出了個題目:三乘以七等于幾?”“你怎么回答?”爸爸問。“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回答說是二十四。”現在,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交代如下:本“請問魯亢”系列中,魯亢其人,是真是假,有如《紅樓夢》中之賈寶玉、林黛玉,說真是真,說假亦假。
——“請問魯亢,你信仰什么?”
——“不驚動樓上獨居人終日的動靜,‘我不在,你盡興’。從傾倒的廢墟中探出頭,摸摸鼻子,嗅覺依舊。說信仰太沉重。今兒有啥好吃的嗎?不要放棄。哈哈。”
23)如果你復活了愛,就連恨一起復活吧。
海子《神秘故事六篇》之《初戀》里說到,有一個青年帶著他父親救活的一條蛇,去尋找殺父仇敵。他四處漂泊還是沒有找到,但他的蛇此時卻痛苦地愛上了千里之外的一條竹編蛇。它在把強烈的愛注入那條竹編蛇的同時,也把對殺死主人的仇敵的恨注了進去。竹編蛇活了。它爬出主人的木箱要去與給了它生命的蛇會合,臨出發前,它帶著被注入的恨咬死了它的主人。它的主人正是那條給它生命的蛇的主人的仇敵。兩條相愛的蛇注定了青年一輩子必須漂泊。
——“請問魯亢,倘若愛復活了,恨也隨之復活,那么,該復活愛嗎?”
——“愛復活為鬼?恨復活難道還望成圣賢?萬物復活咸因前生有罪有疵,既如此,當然選愛,來場人鬼情未了。”
24)一個唯心主義者對命運的左思右想。
據我所見,一般人在得意處總是遺忘命運,只在失意處才恍然慨嘆造化弄人。我們閩南有句老語叫做“吃命贏過吃硬”,意為:命好勝過好強爭勝、累死累活打拼。作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唯心主義者,我自然相信命運的存在,但在處理世事的具體問題上,卻又總是暗懷著謀事在人的自信。
——“請問魯亢,如何看待命運?”
——“迄今未疑‘天注定’,俗而踏實。附送兩句西北民謠,看命只看那人能否‘在甜處安身,在苦處化錢’。”
33)一篇關于詩歌標準探討的約稿,已經變成一條水淋淋的草繩。
整整一個月,我一直在構想陳仲義先生關于詩歌標準探討的約稿,其情就像一條一斤重的草繩每天浸一斤重的水一樣,越來越沉地壓在心里。毫無疑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詩歌標準,但如何把這個標準表達出來而且表達得準確,真難。
——“請問魯亢,你的詩歌標準是什么?”
——“迷思于語言的妙構、氣質的雅、對反智的糾正、干擾虛無和惰性的強電波,像黑暗騎士,可能,說的是一部電影。不過已經在盡力說清楚了,即:自由的身份,不屈不撓的博學。”
36)快下雨了,魯亢的腳比我的問題還焦慮。
閩籍第三代詩人黃燦然若干年前在《讀書》雜志撰文《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中,直指“本世紀以來,整個漢語寫作都處在兩大傳統(即中國古典傳統和西方現代傳統)的陰影下”。結合此前學界、知識界傳讀的布羅姆的《影響的焦慮》,確乎“陰影、影響”已成為中國當代寫作者揮之不去的情結。
——“請問魯亢,如何化解影響的焦慮?”
——“介入。在場。這幾乎算是偽命題,好適合次發達國家的顆顆想獎腦袋。快下雨了,我要疾步。啥焦慮的,影響實太少。近期終審又被斃,這影響就發不出去。”
45)所謂同題,其實就是企鵝在南北極扎成一堆。
古之文人雅集時,好把酒臨風、對月抒情,然后或現場或各自回家就著當情當景寫寫同題。這個習慣成為血液流注到今日文人身上,同題遂不絕種。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同題當是《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同題作家:朱自清、俞平伯。
——“請問魯亢,如何看待由古至今的同題詩文?”
——“劣詩一籮筐。酒酣耳熱,氣味相投,也屬節能減碳之舉,但試無妨。友人說不缺寫詩的,缺的是讀者。用艾略特一言回他:虛偽的讀者,空心人。于是有同題詩,正如企鵝愛扎堆。玩吧,南北極也沒幾年冰了。”
48)“光”一定本來就在那里,它只是經由上帝的口說出。
在我看來,上帝說“要有光,就有光”,其意并不表明上帝的存在之威力,而在于印證語言的力量,具體說,就是“命名”的力量。“光”一定本來就在那里,它只是經由上帝之口說出才具有了自己的表述指稱,才為世人所認識。每一個事物都相應對照著一個名稱,沒有無名的事物。
——“請問魯亢,你認為命名是必須還是無須?”
——“盡量靠近必須。給午餐命名:赤裸的混蛋(破了)。給失眠也來一個命名:愛弟弟的玫瑰,等等。你要命名啥?找上帝,他一流!”
54)錢鍾書用一部《圍城》來為《紅樓夢》一副對聯作注。
重讀《圍城》,我感覺《圍城》尚未到達中國現代文學的頂峰,雖然夏志清教授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我內心還是這樣認為。錢鍾書這位大才子對中國市民階層、知識分子階層的認識實在是太通透了,簡直通透得可怕,可怕得毫無同情之心、悲憫之情。錢鍾書真的是一個看破世事的人,更是一個深悟人生之虛無、之荒誕的大家,也只有這種人,才能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才能徹底拒絕一切繁華喧囂于門外。
《紅樓夢》里有一聯:“世事洞察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圍城》一書可視為對《紅樓夢》此句的注解。
——“請問魯亢,‘圍城心態’說到底是人類喜新厭舊心理的一種表征,有解決良方嗎?”
——“老方:尊重與包容。先有儀式,后入血液,可過百年。喜新厭舊亦平常,重修舊好待運氣。大中午,熱煞人,回這類事,顯呆氣。古之齊人之福,也不失為方,莫破產,別壞身。只是,哪有圍城?全因心魔。”
60)寫作中的三種人稱指向。
與學弟吳子林博士QQ聊天,在理性與感性的語境下,突然想到寫作中的三種人稱指向。三種人稱很難說哪種更優秀、哪種更拙劣。轉天在車上便想,《伊利亞特》該是第三人稱寫作,《哈姆雷特》該是第二人稱寫作,《紅樓夢》該是第一人稱寫作。三部巨著的三種人稱寫作同為經典。由此對照自己,該屬于第一人稱寫作。
——“請問魯亢,你屬于第幾人稱寫作?”
——“心儀于第二人稱,如新小說《慢》;震動于第三人稱的《鐵皮鼓》;羨慕第一人稱的《一個人的好天氣》。各個人稱互串寫作,對撞、爆炸,碎片自組于空曠,時間威逼智力,永遠是實驗。炫技、干預、曖昧、迷失、憤怒,此五菜還加一湯:清醒。”
74)如何趕走如人肉窺探器的樓上住客?
“讓蒙面人說話”,第一次讀到這個句子是在西川出版的一本隨筆集上,該句是此書書名。搜索時發現,四川作家麥家也用這個書名出了本小說集。內心覺得這句話應有典故或出處,也許在西方某部經典上?我自己倒很想讓魯亢這個蒙面人說話,說出一個具體的、形而下的魯亢:他的出生、教育背景、成長經歷、生活現狀……
——“請問魯亢,如何讓蒙面人說話?”
——“也蒙面,疑似同類。戰勝的方法之一是攪局。大家都是蒙面人,過去有疑懼,現在當行為。近在構思一文:如何趕走樓上的住客。他與我同息同眠,時時發聲暗示,如人肉窺探器。是將之想成《魔界》里的‘咕嚕’,或安吉麗娜·朱莉?給個建議。風騷好動的蒙面人還是少說為妙。”
82)張清華教授的天才詩人生命體驗論。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九日,在首都師范大學的一場詩歌會議上,又一次聆聽了張清華教授關于“天才詩人的生命體驗”的講述。在我看來,這同時也是張教授對自己的內心定位和所欲達成的目標。在張教授看來,天才詩人是些極其偉大的另類詩人,他們富有慷慨的犧牲精神,用生命的代價換取藝術的價值,他們是一些現實的盲視者。荷爾德林認為那就是“詩人的使命”;雅斯貝爾斯的說法更直接,詩人就是屬于甘愿進入深淵的、擁有“深淵性格”的人;尼采則說他注定要去“危險地生活”,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存在的最大享受”。
——“請問魯亢,如何理解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詩人的深淵性格’?”
——“他通過考察思想家的特殊性和歷史性格的殊異,對詩人的從眾和叛離給出了一個‘存在’的解釋。我愿意為此埋單:如果有助于自我解脫,有助于培養純正的氣質,乃至臆想的拯救。”
84)那現代詩究竟生出了幾個龐德爸爸?
在中國,龐德影響了許多詩人包括我,以致我在《龐德,或詩的肋骨》的第一句即寫下“那現代詩究竟生出了幾個龐德爸爸”。此句來源于一個哲學命題:“是兒子生出了父親而不是父親生出了兒子”。
——“請問魯亢,你受過龐德的影響嗎?如何評價龐德?”
——“早期《地鐵》:這是古詩十九首之類的移形幻影,不安靜的眼,有趣;中期《詩章》及刪改《荒原》,一個卓越匠人,望塵莫及。與其說學,太過了,還是致敬吧;后來,他的‘有罪期’讓人想起同罪之海德格爾,人探視,其妻擋,說:他在思考。詩人不妨思考,可他們亂了。他對我的影響很世俗,有等于無。”
88)理想的創作期應該像乞丐一樣低頭能吃,靠地打鼾。
批評家陳仲義、向衛國、趙思運、張德明等在關于我的批評文章中,都注意到了我的游歷詩。每次外出回來后,我總有一段時間處于茫然無措狀態。有一種離開正常軌道的外來沖擊感,使我身心恍惚。往往這時候就是我的創作噴薄期,《任性》《九寨溝》《紙空氣》《張家界》等諸多長詩就是這樣完成的。得悉某詩人剛不遠萬里從某國回來,我短信詢問他是否有創作感,其回到:“只有疲憊感”。
——“請問魯亢,外出旅游回來后,會是你創作的勃發期嗎?”
——“我沒,困覺。你有,勃發?借龐德的一句詩來解釋此事:旅游,‘有一個畫好的天堂在其盡頭’;歸來,誰能確定是否踏實、有心情呢。‘沒有一個畫好的天堂在其盡頭’。創作期,還是學乞丐似的,低頭就能吃,靠地就打鼾。秋老虎來了,你要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