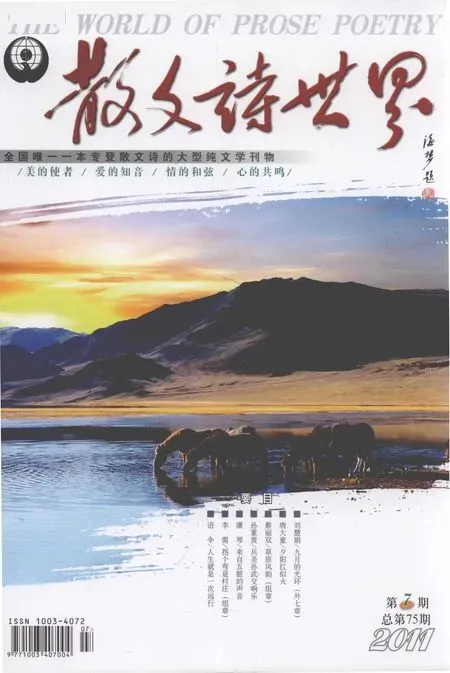礦 工
云南 亢恒學

一
礦工。一個古老的命名,太耐人尋味。
在許多詞典里,所有的注腳,都蒼白無力。
我領悟了三十年,得出一個沉重的結論。
它是一個個鮮活的人,一道道悲壯的風景。在艱辛的汗水背后,更多的是血和淚。
二
多年來,無論春夏秋冬,一早一晚,或陰或晴,遙望礦山,或粗或細,或直或曲,或經或緯的路上,或特立獨行,或三三兩兩,或成群結伴,他們騎著摩托,由遠而近,像蚊子、蒼蠅和小蜜蜂,在耳畔嗡鳴;似夏天雨后的飛螞蟻,在眼前忽隱忽現。夜晚,在來去礦山的路上,他們是許多難以入夢的螢火蟲;而在我的仰視里,他們是點燃夜空的星斗。可惜,每次一剎而過的印象,又太繚草。
在充燈房,把燈盞遞給我的那位老工人,他的門牙已關不住風。世界在他的腳下傾斜。他說十六歲就在井下挖煤,去年出了點意外,礦長是咱舅子的舅子的堂舅子,沾了點便宜。
在穿越地層深處,三三兩兩的礦工,如直立巖壁的黑山羊,覓食遠古的植物。那些蔥郁的綠意,已被時光褪盡,肉眼所及,盡是如鐵的堅硬。
在他們不遺余力的面壁斧鑿鎬掀中:
一架架鋼筋鐵骨,似股肱肌隆起;
一條條浸透汗水的軌道,步步延伸;
一臺臺雙風機,把萎縮的風筒吹得鼓脹,直達巷道末梢。
煤礦,一座地下工廠。
支護,森林般茂密,只是一些曾經天籟般悠揚婉轉的鳥啼蟲鳴,早已成為遠古。偶然遇見的零星動物足跡,也僵為化石。巖縫中滲透出來的小溪,卻沒有魚。
一排排電纜線,裹著黑色的外衣,一路向前;
一臺臺電機成群結隊的糾結,猶如虔誠的禱告者;
一條條浮離地面的皮帶,托負著煤的心愿,通向時光之隧;
一臺臺不言而喻的報警儀,閃爍著各種險情;
一位返祖的工人,酷似把脈號病的醫生,在盲廢巷、冒頂處、工作面上隅角,檢測各種聚積的有毒有害氣體。
一位鏟煤的工人,雙眼如電,如洞察萬物的山鷹,或收緊翅膀、獨守漆黑蒼茫、或展翅翱翔,讓不規矩的煤塊,順理成章。
掘進迎頭,一群群堯舜精英,沿著煤層的走向,冒著肆意傾瀉的淋棚水、險象環生的頂板,沒有凱歌與戰鼓,絕路開拓。風鎬是他們沖關奪礙的見證;汗水在鏗鏹聲中滑落,巖層在吶喊的進攻中,撕心裂肺的一層層剝落。
在百余米、千余米的攔腰包抄中,熱浪翻滾的工作面,藏在巖層中億萬年的煤,如初夏時節的麥子。收割的季節,長夜漫漫……喂養工業的煤,不是米勒畫中那群割麥的農婦,小試鐮刀的鋒芒。煤的堅韌,除了瓦斯的氣貫如虹,只有炸藥、風鎬、割煤機和礦工的爆發力,才能掀開它袒露的一角。
割煤的場面,勝似搶抓收割節令。地殼的運動,偏偏不守規矩,起起伏伏的煤層、高低不等,千萬噸的頂板斷裂又破碎,鋼鐵意志的單體液壓支架,也要拼命苦撐。從來沒有粉絲追隨的礦工群體,或立或蹲,或貓著身子偏著腰,雪亮的鎬子和鋤器發出串串刺耳的撞擊,任血性的汗水和迸裂的煤浪,肆無忌憚地翻騰;兩排柱子間的鎦子,如暴漲的小河,載著凸起的烏金,不停地嘩啦嘩啦流淌。
這樣的場景,讓我常常情不自禁:要是羅丹再世,他的傳世、佳作,定是咱礦工壯懷激昂的一瞬。
三
這世界精彩紛呈,唯有挖煤的礦工黑白不分。
蒼天未降大任于斯。礦工們卻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傷其體膚……
為了生存,為了求財。
他們前仆后繼,一張張老面孔才被巷道熟悉,一張張新面孔又接連出現。
礦工,一道遠離陽光的風景。
在礦井深處,常常見到一些支護斷梁折柱,災害盡是些防不勝防的豺狼虎豹。
透過礦工背影,我心深處彌漫的,不是掌聲與笑容、鮮花和美酒,而是難以克制的悲憫!
眺望迷蒙的遠方,唯愿潛在大山深處的村子,少點愁纏,多些歡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