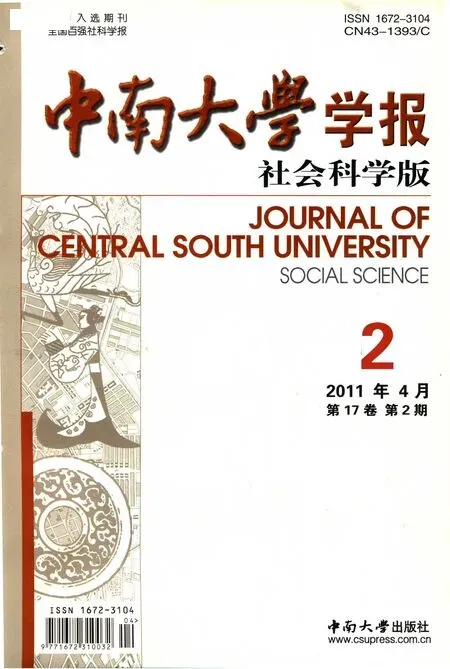論共同犯罪性質的認定
——以整體犯罪構成為視角
劉斯凡
(武漢科技大學文法與經濟學院,湖北武漢,430072)
論共同犯罪性質的認定
——以整體犯罪構成為視角
劉斯凡
(武漢科技大學文法與經濟學院,湖北武漢,430072)
整體犯罪構成是指兩人以上的共同行為所符合的犯罪構成。不管是否采納修正的犯罪構成概念,整體犯罪構成都是認定共同犯罪的基礎;整體犯罪構成要和共犯的成立條件相區分,作為整體犯罪構成評價對象的事實行為要結合單獨犯罪來確立;在共同犯罪中,只要有利用身份的情況出現,就可以認為構成相應的身份犯,如果同時滿足非身份犯的犯罪構成,就形成了非常特殊的想象競合關系。
整體犯罪構成;共犯;想象競合;刑法理論;身份犯
在共同犯罪中,犯罪的性質是一個不難認定的內容,但一旦涉及到存在身份犯時共同犯罪的性質,問題就變得復雜無比。現行的刑法理論忽視了整體犯罪構成的存在,更未對身份在整體犯罪構成中的地位進行分析。本文擬從整體犯罪構成概念出發,結合身份在整體犯罪構成中的地位,對共同犯罪的性質認定進行探討。
一、德日刑法理論關于共犯構成要件的不同解讀
在構成要件①的基本分類上,日本刑法存在基本構成要件和修正構成要件的分類。基本構成要件是在刑法分則或各種刑罰法規中單個規定的構成要件。所謂修正的構成要件,是以基本的構成要件的存在為前提,將其進行修正之后所設計的犯罪類型。從數人參與的角度來看,規定有兩個以上的人共同實行犯罪的就是共同正犯,教唆他人實行犯罪的是教唆犯,幫助他人實行犯罪的是幫助犯等各種類型。[1](103)然而,拋開行為上的差別不論,如果仔細分析,正犯和狹義共犯所符合的犯罪構成仍存在質的差異。持上述分類的學者認為殺人罪的共同正犯的構成要件是“二人以上共同殺人”。[1](103)很明顯,這個修正的構成要件將主體為一人的構成要件修正成了二人以上,也就是說,該修正的構成要件是兩人以上共同滿足的構成要件。而教唆犯和幫助犯則不同,他們根據總則所得到的修正的構成要件只是針對教唆犯或者幫助犯本人。②
這種差異在日本理論界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導致在共同犯罪的定罪和正犯與共犯的區分問題上一直含混不明,造成了共同犯罪定性的困難,正犯和共犯區分的失當。所以,在確立共同犯罪整體的性質上,日本學者之間并沒有從修正構成要件的角度展開討論,而是從共犯的本質的角度,提出了行為共同說和犯罪共同說,即將本屬于構成要件解決的問題由共犯的本質來處理。這種處理模式以犯罪的共同或行為的共同作為認定共同犯罪的基點,顛倒了整體犯罪構成和個別犯罪構成的關系,將共犯的成立條件和犯罪構成剝離。
與此相對,德國并沒有基本構成要件和修正構成要件的分類,只是存在基本構成要件(Grundtatbestand)和變體構成要件(abgewandter Tatbestand)的區分。基本構成要件是對犯罪類型基本形式的規定,它包含類刑事可罰性的最起碼的條件;變體構成要件(加重性質和減輕性質的變體)就基本構成要件在其特別的特征上做了擴展。(如關于時間或者空間的狀況,關于實施的方式,關于使用一定的行為手段的規定,對于行為人與受害者之間關系的規定,等等。)[2]可見,變體構成要件并非修正的構成要件。所以,這種分類方式根本不涉及到共同犯罪的定性。但德國刑法學者大都認為共犯理論是不法構成要件理論的一部分,并認為正犯是自己實施構成要件行為或者通過他人實施構成要件行為或者作為共同正犯參與此等構成要件行為,教唆犯和幫助犯則處于構成要件之外。[3](651)
德國學者將共犯理論都視為構成要件理論可謂恰當,但只是從確立正犯的角度來論證正犯和構成要件的關系,并沒有從構成要件和構成要件事實的關系上闡述共同犯罪的構成要件,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構成要件和構成要件事實的關系是確定共同犯罪性質的基礎,是討論正犯的前提。所以,雖然可以沒有修正構成要件的概念,但是對共同犯罪的構成要件符合性的探討是必需的,這一點無法以正犯符合構成要件這一簡單結論取代。
二、我國整體犯罪構成理論的確立
我國刑法通說關于犯罪構成的分類與日本關于構成要件的分類是一致的,共同犯罪所涉及的犯罪構成就可以稱為修正的犯罪構成。而我國刑法并不存在共同正犯的規定,在探討修正的犯罪構成時,更加會忽視正犯和共犯在犯罪構成上的差異。如我國刑法通說認為,數人共同實施搶劫行為的犯罪構成,要結合我國刑法分則第263條搶劫罪和總則第26~29條,根據各共同犯罪人的具體情況綜合加以認定。[4]既然是結合各共同犯罪人的具體情況綜合加以認定,這個綜合認定得出的犯罪構成是以單個的共犯人為基準的,從而忽略了共犯中的修正的犯罪構成的特殊性。共同犯罪是兩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即兩人以上共同實現一個犯罪構成。共同行為要構成犯罪,必須有兩人以上的共同行為符合一個犯罪構成,這個犯罪構成就叫做整體犯罪構成。這個整體犯罪構成應該先于我國通說所說的修正的犯罪構成(可稱為個別犯罪構成)而存在。③
共同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應該由整體犯罪構成決定。共同犯罪中的實行行為和單獨犯罪中的實行行為不能等而視之,除非是共犯中的一人獨立實現了所有的構成要件。共同犯罪中的實行行為和單獨犯罪才是一致的,這時候依靠正犯才可以界定犯罪的性質。在相當一部分情況下,每個共犯人只是部分地實現了構成要件。比如搶劫罪,甲實施暴力脅迫行為,乙實施獲取財物的行為,不論是甲還是乙,單獨都不符合完整的搶劫罪的構成要件。如果只是從甲的行為來認定犯罪的性質,故意傷害罪可能更合適;如果僅僅依據乙的行為來認定犯罪的性質,盜竊罪是更好的選擇;只有將甲和乙的行為合并來看,才能定性為搶劫罪。如果從共同犯罪構成和單獨的修正犯罪構成的角度來理解,可以更清楚地發現通說的問題。共同犯罪是數人共同實現一個犯罪構成,應該從整體犯罪構成的角度來理解其的性質。也就是說,共同犯罪性質的確定,是將共同犯罪人的行為當做一個整體,來確定到底和刑法分則的哪一個犯罪構成相符。修正的個別犯罪構成在整體犯罪構成成立的前提下才能存在,不考慮整體的犯罪構成,而只從修正的犯罪構成來決定共同犯罪的性質,在邏輯上存在問題。
我國存在共同犯罪的立法規定和成立條件的理論,它和整體犯罪構成的關系便值得探討。我國刑法通說認為共犯的成立條件有三個,分別是兩人以上、共同故意和共同行為,并認為共同犯罪行為表現為四種方式:第一,實行行為,即實施符合犯罪構成客觀方面要件的行為;第二,組織行為,即組織、領導、策劃、指揮共同犯罪的行為;第三,教唆行為,即故意勸說、收買、威脅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唆使他人故意實施犯罪的行為;第四,幫助行為,即故意提供信息、工具或者排除障礙協助他人故意實施犯罪的行為。[5]顯然,這樣的共犯成立條件不是從犯罪構成的基礎上把握的,因而必然存在漏洞。我們知道,共同犯罪的成立條件,是為了說明在何種情況下共同犯罪可以成立。而犯罪的成立之重要判斷標準是有沒有實施刑法分則規定的構成要件行為,在單獨犯罪中如此,在共同犯罪中亦然。所以,實施了構成要件行為的正犯和沒有實施構成要件的教唆犯和幫助犯應該進行區分,以實施了構成要件行為的正犯來認定犯罪是否成立就足夠了,教唆犯和幫助犯在確立共同犯罪這個整體是否成立上是沒有作用的。糅合了教唆行為和幫助行為的共同犯罪行為到底是什么樣的行為,是否可以糅合在一起,都成問題。而且,將所有的共犯人的行為結合在一起,捆綁成共同犯罪行為,也就肯定了每個共犯人也成立犯罪。在犯罪的成立都成問題時,如何能夠確定實施了非構成要件行為的教唆行為和幫助行為一定就構成犯罪? 這樣的做法一方面使得共同犯罪的成立條件越俎代庖,取代了認定教唆犯和幫助犯是否成立的修正犯罪構成,另一方面很容易恣意擴大犯罪的成立范圍。實際上,我國刑法理論中的犯罪成立條件在認定犯罪成立上的作用是十分微小的。在整體犯罪是否成立的問題上,我國刑法理論跟隨日本刑法理論,以犯罪共同說或者行為共同說來說明。在教唆犯是否成立的問題上,是根據教唆犯的修正的犯罪構成來判斷。這其實從根本上否定了犯罪成立條件在認定犯罪時的指導意義。
整體犯罪構成的認定,需要考慮不同的情況。在共同犯罪中,可能是一個人實現犯罪構成,也可能是兩人以上實現一個犯罪構成。對于后者,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任何單個人的行為單獨看都不符合某一個犯罪構成,另一種是單個人也符合某個犯罪構成,該犯罪構成也許和兩人以上所符合的犯罪構成相同(如兩人以上共同傷害的情況),也許不同(如搶劫中有人使用暴力,有人獲取財物)。到底是一人還是數人實現犯罪構成的根據就是客觀行為,該客觀行為判斷的前提是作為評價對象的事實行為。而在共同犯罪中,對事實行為的認定和單獨犯罪會有所區別。以故意殺人罪為例,在共同犯罪中,一人抱住被害人,另一人用刀刺殺,一般認為,刺殺者實施的是構成要件行為,而將被害人抱住的人實施的并非構成要件行為。又比如在一人實施投毒行為,而另一人借談話轉移被害人視線時,會認為投毒人實施的是構成要件行為,而轉移被害人視線的人實施的是非構成要件行為。這樣的認定貌似合理,而如果與單獨犯來對比,就會發現問題所在。刺殺者必須先有對被害人的控制行為才能實施刺殺,這種控制不一定是抱住被害人,但必定將被害人置于可刺殺的范圍之內,否則刺殺行為不能完成。投毒人要投毒成功同樣要趁被害人不注意或者轉移被害人的視線。這些所謂的構成要件行為之外的行為在單獨犯罪中是很少被單獨考慮的。在單獨犯罪中,我們必定認為控制被害人的行為和刺殺行為結合起來才可稱為殺人行為,我們總是主張之前轉移視線的行為和后面的投毒行為構成了刑法上可以評價的投毒行為的整體。在單獨犯罪中作為一個整體的行為,在共同犯罪中因為分別由不同的人實施,就很容易被分離成數個行為,這種做法的合理性要結合作為評價對象的行為來把握。
對于作為評價對象的行為,可以以競合理論中的行為概念作為參考。德國的判例和主流的理論在界定競合理論中的行為概念時,往往以自然的生活觀念(natürliche Lebensausffassung)作為基礎。如果不同的行為部分是基于統一的意志決定,且時間和空間又有緊密的聯系,以至于他被一個與之無關的觀察者認為是一個行為的,那么,一個事件過程的外在上可分離的數個組成部分應當被視為一個單一的行為。[3](710)這種行為概念應該是前構成要件的,而遺憾的是德國學者忽視了這一點,而從構成要件的角度進一步認為“自然的生活觀念”的公式不再適用,它掩蓋了將行為的存在視為判斷的對象的事實上的根據。由于不存在法學觀察所能直接追溯的享有優先權的社會行為單數,行為人計劃的單一性又不可能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為數個具體的行為可能來源于一個單一的行為決意,而這些具體的行為基于公正性又不得復合為一罪(例如,盜竊用于謀殺的武器,殺死被害人,為逃脫搶劫機動車)。因此,對于確定是行為單數還是行為復數起決定作用的,可能是各自破壞的法定構成要件的意義。[3](711)這種混淆作為判斷對象的事實行為和作為已經評價過了的構成要件行為的思路是不足取的。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斷是看社會生活中的具體事實是否和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構成要件的行為相符。作為評價對象的行為應在先于構成要件而存在,而不是依靠構成要件來確定行為的單數和復數,靠構成要件所確定的行為,已經是構成要件行為了,已經是評價過了的對象。至于盜竊用于謀殺的武器,殺死被害人,為逃脫搶劫機動車的一系列行為,到底被認定為一個構成要件行為還是數個構成要件行為,則是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問題。
所以,在確定作為共同犯罪評價對象的行為的時候,恐怕仍需要采取類似自然的生活觀念的做法,以單獨犯的事實行為為參照,對共同犯罪中的事實行為加以判斷。所以,抱住被害人和刺殺行為的整體、轉移視線和投毒行為的結合是需要納入刑法評價的事實行為。④這樣的認定結果可能和將單純的刺殺行為或者投毒行為作為事實行為得出的結論一致,但將單純的刺殺行為或者投毒行為作為事實行為就會與行為理論相悖,偏離了整體構成要件的初衷,在理論方向上是錯誤的。同時,如果和復行為犯的整體構成要件認定模式相比較,理論的一致性的維持也成為問題。
在整體犯罪構成的判斷上,若在共同犯罪中只有一個人實現犯罪構成,該犯罪構成就是整體犯罪構成。若兩人以上實現一個犯罪構成,而單個人實施的行為都不符合某一個犯罪構成,那么兩個以上實現的這個犯罪構成就是整體犯罪構成。如果單個人實施的行為和兩人以上行為所符合的犯罪構成相同,依照高度行為吸收低度行為的原則,整體犯罪構成是兩人以上共同符合的犯罪構成;同理,如果單個人實施的行為和兩人以上行為所符合的犯罪構成不同,更應該以兩人以上共同符合的犯罪構成作為整體犯罪構成。
進一步言之,在主觀方面,每個人的故意的內容都包含了單獨犯罪中的故意,并同時具備了單獨犯罪的所不具備的意識聯絡等內容。⑤其次,在客觀方面,可能是兩個以上的人共同實現了一個實行行為,可能是一個人實施了實行行為,可能是每個人都實施了實行行為。而不論如何,整體犯罪構成所關注的是整體的實行行為,到底是一人還是數人實施了實行行為,究竟是實施了一個實行行為還是數個實行行為,都不影響整體犯罪構成的符合性,只是當存在數個實行行為時,可以依想象競合的理論來確立整體犯罪構成的符合性。
整體犯罪構成基本上是以刑法分則的構成要件行為為基礎;也就是說,認定整體犯罪構成只涉及到構成要件行為,沒有實施構成要件行為的教唆犯和幫助犯,對整體犯罪構成的認定并沒有影響。⑥確立了整體犯罪構成之后,就可以確立共同犯罪的性質。以共同犯罪的性質為基礎,可以確立教唆犯和幫助犯的犯罪性質。雖然根據各國對共犯從屬性的接納程度,教唆犯和幫助犯的性質會有所差異,但他們性質的認定是以整體犯罪構成的確立為基礎,卻是不難得出的推論。在整體犯罪構成中,犯罪構成的符合性需要重新認定。
三、整體犯罪構成與涉及身份犯的共同犯罪的定性
在我國,當無身份者和有身份者共同實施犯罪時,根據什么來確定所共同實施犯罪的性質到現在仍眾說紛紜,尚無定論。如非國有公司的工作人員與國有公司委派到非國有公司從事公務的國家工作人員共同竊取該公司的財產時,應當如何定性,就存在諸多觀點。第一種學說是主犯認定說,該說認為內外勾結或兩種以上身份者勾結實施的共同犯罪的性質,應由主犯實施的行為的性質確定。[6]這一見解和司法解釋是一致的。第二種學說是正犯行為性質決定說,即以正犯行為的犯罪性質確定共同犯罪的性質。[7]第三種學說是主職權行為決定說。該說主張,在一般情況下,應根據為主的職權行為認定共同犯罪的性質;在兩種職權行為分不清主次的情況下,應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原則來認定共同犯罪的性質。[8]第四種學說是區別對待說。該說認為,具體應分不同情況加以討論:①甲身份者與乙身份者只是各自利用本人的身份,且沒有利用對方身份的,宜認定構成共同犯罪,但應分別定罪處罰;②甲身份者與乙身份者不僅利用了本人的身份,而且還相互利用了對方的身份的,宜按刑法重點保護的身份客體即重點打擊的純正身份犯來確定共同犯罪的性質,對各行為人按統一的罪名定罪處罰;③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分別利用各自的身份,其中,國家工作人員又同時利用了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而非國家工作人員沒有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的,應認定構成共同犯罪,但應分別定罪,即對國家工作人員定貪污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定職務侵占罪;④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分別利用各自的身份,其中,非國家工作人員又同時利用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而國家工作人員沒有利用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的,應對他們統一按貪污罪論處。[9]第五種學說是整體考察說。該說是指從整體上考察混合主體共同犯罪,只要各共同犯罪人具有共同的犯意,且他們之間有意思聯絡,其共同犯罪行為符合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純正身份犯的犯罪構成,各共同犯罪人統一定罪,均以該純正身份犯論處;否則以常人犯論處。[10]
以上觀點各有特色,但都存在一定不足。首先,對于只利用了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或者只利用了公司、企業和其他單位人員身份的,分別按照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來處理,需要討論的是如果同時利用了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和公司、企業和其他單位人員身份的如何定性。按照主犯定性,實際上是按照主犯所具有的身份定性,而當存在兩個以上的主犯,而主犯的身份不一致時,主犯認定說就發揮不了作用。其次,正犯行為性質決定說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當存在兩個以上的實行犯⑦,且實行犯具有不同的身份時,仍然無法確定共同犯罪的性質。而如果認為依照有身份者的實行犯的實行行為來定罪,那么按照相同的邏輯,回歸到主犯作用說,是不是可以認為,可以按照有身份的主犯來認定共同犯罪的性質?而不論按照也許只是實施了部分構成要件行為的有身份的行為人來界定犯罪的性質,還是按照起到主要作用的有身份的共犯人來界定共犯的性質,都存在問題。部分行為、或者部分作用怎么可能決定整體犯罪行為的性質? 正是因為如此,實行行為說將單個行為人的部分行為來決定整體犯罪的性質,會存在難以確立實行行為的疑問,也會出現當一般主體的犯罪重于有身份要求的犯罪時,難以保證罪刑相適應的難題。實際上,按照主犯的性質來認定共同犯罪的性質與按照實行犯的性質都存在同樣的缺陷。不論是主從犯還是正犯、教唆犯和幫助犯都是在符合整體犯罪構成的前提下,也就是犯罪性質已經確立的情況下,所做的進一步探討。如果認為根據主犯或者正犯可以認定共同犯罪的性質,就顛倒了邏輯關系。再次,主職權行為決定說以職權的高低來決定共犯的性質,其本質觀點就是認為職權高的起到了主要作用,而當職權相當時,或者說作用相當時,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則,確實避免了主犯決定說在存在兩個以上的主犯時,難以說明共犯性質的疑難。但是,僅僅因為認定上的困難,就采取有利被告的原則來處理,似乎不太妥當。復次,分別考察說所列舉的四種情況可以歸結為一點,只要存在對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利用,不論是有身份者利用,還是無身份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統統成立貪污罪。而對于非國家工作人員,只有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的時候,才構成貪污罪,否則構成職務侵占罪。這種學說看似比較合理,但是以單個行為人是否利用了有身份人的身份來決定共犯的性質,忽視了共同犯罪部分行為全部責任的基本原理。從共同犯罪的角度思考,在兩人以上共同實現一個犯罪構成的時候,只有其中一人利用了身份犯的身份就可以構成共同犯罪,或者說只要其中一人具備身份就構成相應的共同犯罪。國家工作人員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各自利用自己的身份,與國家工作人員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對方的身份,或者兩者既利用自己身份又利用對方身份,實際上沒有差別。但是,認為只有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時才可以構成貪污罪,已經否定了共同犯罪本身。而且,非國家工作人員即使利用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但他仍然不具備該身份。如果將分別考察說貫徹到底,真正分開考察的話,應該是永遠都不可能構成貪污罪。最后,整體考察說注意到了共犯犯罪的認定應該區分整體犯罪構成和修正的犯罪構成,其理論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仍不夠完整,主要是沒有考慮到即使是整體犯罪構成,在整體的行為可能構成多個犯罪的時候,依然存在想象競合的情況。而不是簡單地認定為純正身份犯就足夠。而且,當教唆犯或者幫助犯具有特定身份,正犯不具備相應身份時,難以成立相應的共同犯罪,當然也無法確立犯罪的性質了。
在涉及身份犯時,以整體犯罪構成認定犯罪的性質是合理的方法。我國刑法通說認為身份犯分為真正身份犯和不真正身份犯。對于不真正身份犯,身份只影響到量刑而不影響定罪,身份并不影響整體犯罪構成的成立。對于真正身份犯,只有具有該身份才可能構成相應的犯罪。在共同犯罪中,整體犯罪構成的符合到底是只需要一個人具有相應的身份還是所有的人都具有身份。如果只需要一個人具有身份,何種性質的行為人具有身份才滿足整體犯罪構成的要求,都是在整體犯罪構成下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如果每個人都具有身份,很容易就可以確立整體犯罪構成。如果只有一個人具有特定的身份,同樣也不會影響到整體犯罪構成的存在。以受賄罪為例,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非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是典型的受賄罪的共犯模式。若認為只有兩人以上同時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才可成立整體犯罪構成,那么非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的共同犯罪的范圍就急劇縮小。即僅限于國家工作人員實施了完整的構成要件行為的情況下,一旦國家工作人員只是實施了部分構成要件行為,就無法確立整體犯罪構成,共同犯罪無法構成,而這過度縮小了處罰范圍。此外,從整體犯罪構成的確立模式來看,只有一個人具有身份,就可以滿足所有的構成要件要素,當然可以構成相應的犯罪。如果兩人以上都具有身份,則會對相應的行為人是否構成正犯發揮影響,而對犯罪性質的認定不會產生影響。所以,在整體犯罪構成中,只要其中一人具備相應的身份,相應的犯罪就可以成立。但結合前述分析,具有身份的人至少是實現了部分構成要件的人,僅僅是教唆犯或者幫助犯具有相應的身份,還不足以成立相應的犯罪。
因此,在存在身份犯的情況下,只要有利用身份的情況出現,就可以認為構成相應的身份犯,與此同時,如果同時滿足非身份犯的犯罪構成,同樣可以構成非身份犯,這兩個罪屬于想象競合的關系。然后可以確立相應的單個行為人的修正的犯罪構成,采取從一重處斷的原則,確立不同犯罪人所應當成立的罪名。原則上按照兩罪中的重罪論處,如果輕罪對無身份者的處罰較重時,可以認為成立輕罪。
注釋:
① 雖然因為犯罪論體系的原因,我國的犯罪構成和大陸法系的構成要件存在重大差別,但這種差異對犯罪構成分類的影響并不明顯,故在本文可以忽視這種差別,但在論述上,涉及德日刑法時,稱構成要件,涉及我國刑法時,稱犯罪構成。
② 通說對修正犯罪構成的認識存在諸多缺陷。比如通說認為,修正的犯罪構成僅限于對基本的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的修正。這種理解是極其片面的,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幫助犯的犯罪故意都和單獨犯罪存在巨大區別,若是認為主觀要件沒有被修正,那么,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在修正的犯罪構成中的故意根本無法界定。所謂的教唆犯和幫助犯的雙重故意根本不可能在修正的犯罪構成中體現,修正的犯罪構成作為確立犯罪成立標準的基本功能就完全喪失。
③ 鄭逸哲教授在《構成要件理論與構成要件適用》一書中對此有精當敘述,他指出:迄今在適用所謂“共同殺人(既遂)構成要件”時,是一直混淆不清的,有時指“全體成員(既遂)構成要件”,有時又用來指“個別成員(既遂)構成要件”……以B和C為例,他們根本不可能犯“共同殺人(既遂)罪”,雖然刑法上是存在“共同殺人(既遂)構成要件”,但那是就“共同正犯”——即“參與者全體”——所規定的構成要件,而不是就“參與人”個別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在“個人責任主義”的情況下,B應該就其個人的“參與共同殺人(既遂)構成要件該當性”,而犯“參與共同殺人(既遂罪)”。鄭逸哲.構成要件理論與構成要件適用. 臺北:瑞興圖書.2004: 124?125. 由于全體構成要件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所有參與犯罪的人所符合的構成要件,而將教唆犯和幫助犯納入,而且,全體構成要件僅限于共同正犯構成要件,故本文采取整體犯罪構成的說法。
④ 當然,這只是針對共同犯罪的事實行為的最終判斷結果,對于作為評價對象的事實行為的判斷過程并沒有這樣簡單,需要對事實行為做層層遞進的逐步分析。具體可參見鄭逸哲.構成要件理論與構成要件適用.臺北:瑞興圖書. 2004: 4?94.
⑤ 在目的犯的場合,如果每個人都具有犯罪目的,當然滿足目的犯的主觀要件,但只有部分人具有犯罪目的時,所涉及的問題和身份犯相同,故大致可以參考下文中對身份犯的探討。
⑥ 但并不代表著整體犯罪構成之外僅僅存在教唆犯和幫助犯,從整體犯罪構成和正犯的關系來看,在整體犯罪構成中,至少是實現了部分構成要件行為的人,如果不考慮身份犯的情況,他們必然是正犯,而在整體犯罪構成之外,仍然存在構成正犯的可能。因為整體犯罪構成是確定犯罪性質的標準,并非正犯和共犯區別的標尺。
⑦ 按照本文的觀點,在共同犯罪中,非身份犯也可以構成身份犯的實行犯。
[1] 大谷實. 刑法講義總論[M]. 黎宏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
[2] Wessels/Beulke.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Die straftat und ihr Aufbau [M]. Heidelberg: C.F.Müller Verlag, 2008: 38.
[3] Jescheck/Weigend.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M].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6.
[4] 馬克昌. 犯罪通論[M].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9: 93?94.
[5] 高銘暄, 馬克昌. 刑法學[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179.
[6] 樊鳳林, 宋濤. 職務犯罪的法律對策及治理[M]. 北京: 公安大學出版社, 1994: 245.
[7] 張明楷. 刑法學[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350?351.
[8] 趙秉志. 共犯與身份問題研究——以職務犯罪為視角[J]. 中國法學, 2004, (1): 120?129.
[9] 狄世深. 行為人身份對共同犯罪定罪的影響評析[J]. 法商研究, 2004, (6): 47?57.
[10] 徐留成. 混合主體共同犯罪定罪問題研究[J]. 人民檢察, 2001,(9): 54?57.
Abstract:The overall constitution of crime is the constitution which is comprised of joint act which two or more people implementing. Regardless of adopting the conception of amendatory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e overall constitution of crime is the basis of definiting crime, and the overall constitution of crime differs from the component conditions.Factual behavior, as the appraisal object of the overall constitution of crime, needs to definite with singular crime. In a joint offence, status crime can be confirmed when someone takes advantage of it,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constitution of non-status crime can be confirmed, thus a special relationship of imaginative superposition will come into being.
Key Words:the overall constitution of crime; accomplice; imaginative jointer
On identification of the quality of joint offence: Based on the overall constitution of crime
LIU Sifan
(School of Humanities, Law and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2, China)
D924.11
A
1672-3104(2011)02?0077?06
2010?06?21;
2010?09?16
劉斯凡(1977?), 男, 湖北天門人, 法學博士, 武漢科技大學文法與經濟學院法律系講師, 主要研究方向: 刑法學.
[編輯: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