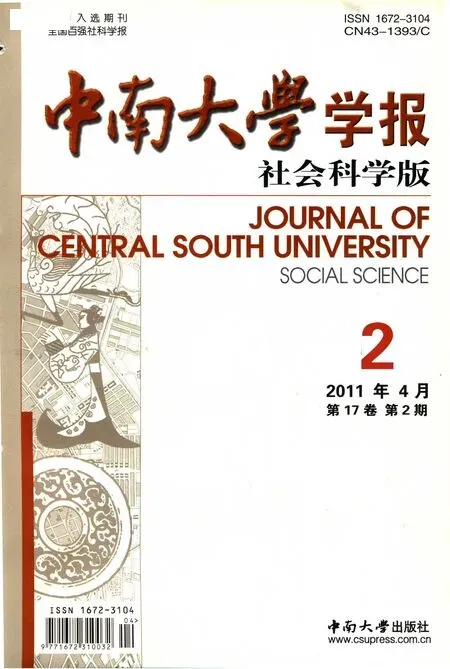晚唐小品作家文學思想探源
李秀敏
(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山西臨汾,041004)
晚唐小品作家文學思想探源
李秀敏
(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山西臨汾,041004)
晚唐小品作家在諸多篇章中明確闡明了自己的文學思想。而這些文學思想均源自于中唐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韓愈、柳宗元,是在繼承韓柳所倡導的“文以明道”“不平則鳴”等理論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它們充實豐富了中唐古文運動的理論內涵,并對后世,尤其是北宋古文運動產生了一定影響,在文學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
晚唐小品;中唐古文運動;文學思想
晚唐小品以其斐然的成就,于唐之季世形成一個創作高峰。而綜觀以孫樵、羅隱、皮日休、陸龜蒙等為代表的小品作家,由于他們身逢江河日下之世,面對晚唐日蹇的國運、民不聊生的慘境,文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促使他們自覺以儒家思想為指歸,擔當起道濟天下之溺的重任,充當社會批判者與拯危救世者角色,并以飽蘸憤激之情的筆墨,對晚唐的重重積弊一一加以譏刺。因而中唐古文作家韓愈、柳宗元所倡導的“文以明道”“不平則鳴”等文學思想激起他們的共鳴,他們不僅于文中徑言對韓愈的企慕,如皮日休在《請韓文公配享太學書》中云:“文公之文,蹴楊、墨于不毛之地,蹂釋、老于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繄公之力”[1](88)。而在實際創作中也自覺繼踵韓愈、柳宗元的文學思想,以“明道”作為自己為文宗尚,反對綺靡文風,以文針砭時弊,發揮文學裨補時政的功用。可以說晚唐小品作家的文學思想無論是站在扶樹儒道立場上的“上規時政,下達民病”[2](3695)“上剝遠非,下補近失”[1](2),還是反對綺靡文風的“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夸飾者也”[3](270),抑或是根據自身創作經驗的“古之士,窮達必形于歌詠,茍欲見乎志,非文不能宣也,于是為其詞”[1](236)、“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駭于俗”[4](264)之論,均能從韓愈、柳宗元的文學思想中探得源頭。晚唐小品作家的這些文學思想充實豐富了中唐古文運動的理論內涵,并對后世,尤其是北宋古文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文學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
一、“文以明道”
晚唐小品作家為文崇尚 “明道”,顯然是承繼中唐古文運動的傳統。
“文以明道”是中唐古文運動的核心理論,是韓愈、柳宗元在總結前人關于“文”“道”關系論述的基礎上確定的古文運動的指導思想。韓愈《爭臣論》云:“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5](65)清楚表明自己的創作宗旨就是“明道”,即以文章作為表現儒家思想的載體。與韓愈同為古文運動領袖的柳宗元,也強調“文”與“道”的關系。他在《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于世者,必由于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6](886)認為寫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讀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辭只是傳達“道”的手段、工具。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又說:“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茍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6](873)更明確地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則。
晚唐大多數小品作家在思想上繼踵韓愈、柳宗元,也將“明道”作為為文的宗尚。孫樵較早在創作中承繼韓柳“文以明道”傳統,重申文學經世致用的主張。他明確提出為文的目的應是“上規時政,下達民病”。(《罵僮志》)[2](3695)他本人的小品創作,也實踐了這一理論主張,以明道濟物為己任。年輩稍晚于孫樵的皮日休,也強調文學裨補時政的社會功能,認為文學應做到“上剝遠非,下補近失”[1](2),否則就失去其存在價值。他在《陸賈序》中云:“圣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1](17),明確表明自己為文旨在明圣賢之道,以求有用于世。他在《悼賈》篇中談及賈誼《新書》時也說:“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真命世王佐之才也。……則《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深……”[1](17)從文章經世致用角度贊頌《新書》的優長。在《桃花賦序》中更是鄭重地宣稱,自己為文是“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1](9),將文章視作諷刺、鞭撻丑惡社會現實的載體,強調文學作品干預現實的社會功用。他于《請孟子為學科書》一文中說:“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洪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 ”[1](89)又于《移成均博士書》中云:“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弊也……”[1](90)對無益于裨補教化之文進行嚴厲指斥。羅隱在《〈讒書〉重序》中同樣聲稱:“君子有其位,則執大柄以定是非;無其位,則著私書而疏善惡。斯所以警當世而誡將來也。”[3](241)他雖牢落不遇,對于文學仍抱有譏刺時弊、救濟時政的期待。劉蛻在其文集自序中也說:“蓋覃以九流之文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結珠璣,昧則將救之;云雷亢粢盛,干則將救之。予豈垂之空文哉!”[2](3661)顯示出自己為文的宗旨與抱負。黃滔在《與王雄書》中則更明確地說,自己為文雖是“出于窮愁”而有意識的創作,但宗旨則必定為“指陳時病俗弊”[2](3843)。陸龜蒙在《〈苔賦〉序》中批評江淹所作《青苔賦》缺乏懲勸之道,廢棄化下諷上之旨;在《〈蠶賦〉序》中又云“荀卿子有《蠶賦》,揚泉亦為之,皆言蠶有功于世,不斥其禍于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 詩人碩鼠之刺,于是乎在”[4](203),更鮮明地表明自己針砭時弊,發揮文學裨補時政功用的為文主張。
晚唐小品作家在將“文以明道”作為創作宗旨的同時,也不斷更新著這一理論。誠如葛曉音所言:“繼承和發展古文運動的關鍵在于正確理解韓柳變革古文的基本精神,不斷適應現實的需要更新‘道’的內容和文的形式,提高古文的思想和文學價值。曲解和模仿必然使散文走向衰落。”[7](207)這從側面道出小品于晚唐所以繁盛的一個重要原因:從社會現實出發,更新了“道”的內涵。如皮日休繼承古文運動傳統,強調儒學道統,以明道濟物為散文創作宗旨,這是他與韓愈、柳宗元相同之處;不過他更想以文為工具,明“經濟之道”。他不僅在《桃花賦序》中強調文章的實用性,在《鹿門隱書》中更以藥為喻,告誡人們應重視文學的實用性:“文學之于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為害。”[1](92)由于重視文學的實用價值,他更強調以“文”來“裨造化、補時政”,凡有所作,必須針對現實,具有強烈的批判鋒芒。綜觀皮日休一生中的優秀作品,特別是編入《皮子文藪》中的前期之作,確實貫徹了這一主張。正如他于《文藪序》中云:“賦者,古詩之流也。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慮民道難濟,作《橋賦》;念下情不達,作《霍山賦》;憫寒士道壅,作《桃花賦》。《離騷》者,文之菁英者,傷于宏奧,今不顯《離騷》,作《九諷》。文貴窮理,理貴原情,作《十原》。太樂既亡,至音不嗣,作《補周禮九夏歌》。兩漢庸儒,賤我左氏,作《春秋決疑》。其余碑、銘、贊、頌、論、議、書、序,皆上剝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1](2)與韓、柳相較,皮日休更強烈地強調文章現實針對性與批判的深廣度。可見,從“文以明道”的角度來看,皮日休的理論直契韓、柳,但就強調批判現實、有補政教而論,又勝過韓、柳。陸龜蒙也強調文章應具懲勸之道、化下風上之旨與美刺精神,與韓愈、柳宗元所倡導的“文以明道”“文以載道”理論相近。不過不同的是,“懲勸”“化下風上”“美刺”本是儒家傳統詩學理論,陸龜蒙不僅將之引入自己的散文創作理論,并以之指導自己的實際創作,令其諷刺小品成為鞭撻黑暗腐朽社會的銳器。
晚唐小品作家為文崇尚“明道”的同時,對浮靡文風有一種本能的排斥,這無疑亦是承繼韓愈、柳宗元的創作精神。
韓愈與柳宗元本著“文以明道”的觀點,對當時過分追求文采而無益于世的文風加以批判。柳宗元甚至在《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一文中言:“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后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阱也”[6](825),認為專務文采,崇尚藻飾,歪曲事實,以致于誣怪、闊誕的作品,對后世危害尤大。可見,柳宗元基于“文以明道”的原則,從文章內容本身出發,對過分追求文采,陷入虛浮藻飾的形式主義怪圈中的作品進行了強烈駁斥。
秉承韓愈、柳宗元創作精神的晚唐小品作家,居于風氣敗壞的晚唐文壇,也強烈排斥浮靡文風。羅隱在《河中辭令狐相公啟》中言“某聞歌者不系聲音,惟思中節;言者不期枝葉,所貴達情”[3](297),認為文章的優劣不在夸飾,乃在于準確表達作者的情感。他又在《理亂》中云:“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夸飾者也。”[3](270)確切表明寫作應重視文章內涵,亦即有德,而德之來源,則源自文人內心之誠,顯然,他認為創作應著重于文章所展現的內在精神,并非夸飾的外在形式。此文又云:“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恥且格。……有恥且格,則教化無不行。”[3](270)從文采與內容的關系角度,再次坦言自己重內容輕形式的觀念。孫樵在《乞巧對》中言:“彼巧在文,摘奇搴新,轄字束句,稽程合度,磨韻調聲,決濁流清,雕枝鏤英,花斗窠明。至于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于俳,觀者啟齒。下醨沈、謝,上殘《騷》、《雅》,取媚于時,古風不歸。”[2](3693)明確表明對追求華艷聲韻的便巧文風的強烈不滿,與柳宗元的觀點自有相侔之處,這些對于矯正晚唐的華靡文風,確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晚唐小品作家對“文以明道”這一理論的繼承與發展,于衰敗腐朽的晚唐,無疑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使他們的諷刺小品在批判現實方面表現得特別尖銳,顯示出引人注目的氣勢與鋒芒。
二、“不平則鳴”與“窮苦之言易好”
晚唐小品作家生逢垂垂末世,世衰俗弊,個人的沉淪不偶,激蕩著小品作家們的心靈,因而在創作理論上易與“不平則鳴”之說達成共識。
中唐古文家們在提出和實踐“文以明道”這一理論的同時,又提出另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這就是“不平則鳴”說。這一理論見于韓愈的《送孟東野序》,認為文章創作乃是主體由于外物激發而產生的思想感情的宣泄。序中指出,作者的感觸既與時代、國家的興亡盛衰有關,又與個人命運緊密相連。所謂“不平”,泛指心靈的感觸,并非專指郁悶、憤慨而言。誠如錢鐘書所言:“韓愈的‘不平’和‘牢騷不平’并不相等,他不但指憤郁,也包括歡樂在內。先秦以來的心理學一貫主張:人‘性’的原始狀態是平靜,‘情’是平靜遭到了騷擾,性‘不得其平’而為情。……不論什么情感都是‘性’暫時失去本來的平靜……”[8](107)韓愈的《送高閑上人序》,在言及情感與藝術創作的關系時,雖就書法而論,但卻進一步闡明了這一理論:認為情感是創作的動力,藝術是情感的表現,并且強調進行創作時作者須將濃烈的情感傾注其中;而情感既包括源自人生遭際的“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5](158),也包括觀賞外物而產生的審美感受,二者均是由外物激發而致。在這篇序中,韓愈還明確指出,作者須“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于中,利欲斗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5](158),作者只有內心時常激動不平,方能創作出生動感人的藝術作品。韓愈雖一再說明,“不平所鳴”的情感既可為歡樂愉悅之情,亦可為怨悱憤激之情,不過對他而言,則更偏于因怨憤不平而鳴的一面。他在《上宰相書》與《上兵部李侍郎書》中就明確表明自己常自覺以詩文宣泄心中的憂憤。和韓愈一樣,柳宗元也極力主張以詩文舒泄憤懣,其言論雖不及韓愈多,卻也說得明白透徹。他在《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中云:“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于世,而遁隱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于當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詠,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也。”[6](644)其中也明確表明自己以詩文釋憂抒憤之意。
晚唐小品作家居于窳敗之世,衰頹的世風,襟懷難展的個人遭際,時時在其內心深處掀起波瀾, 因而“不平則鳴”之說,極易引起他們的共鳴。皮日休在《松陵集序》中云“古之士,窮達必形于歌詠,茍欲見乎志,非文不能宣也,于是為其詞”[1](236),即是將創作看作宣泄心中情感的一種方式,這一觀點直接繼承了韓、柳所提出的“不平則鳴”說。與韓柳相比,皮日休則更重視作家抒寫個人失意不偶的情懷,這一點,在他的《九諷系述并序》里,有著比較詳盡、深入的闡述。序文開篇即直言屈原的作品源于放逐時抑郁難遣之懷:
在昔屈原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為《九歌》,辨窮愁而為《九章》。[1](11)
他充分肯定了屈原這些抒發自己失意牢騷和憤世嫉俗的作品,并指明漢代相應的仿效之作。他比較欣賞揚雄的《廣騷》、梁竦的《悼騷》,正是因為它們本身宣示出一種失意不偶、悲憤怨抑的情懷。而他對于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嘆》、王逸的《九思》等作品則進行了嚴厲的批判,認為他們雖為屈原作品的仿效之作,卻僅是“嗜其麗詞,撢其逸藻者也”[1](11),缺乏屈原作品中那種“騷怨”精神。最后,皮日休又進一步強調自己的這篇《九諷》,正是承繼屈原以創作抒寫失意不偶情懷的傳統,來發抒自己心中的怨抑:
昔者圣賢不偶命,必著書以見志,況斯文之怨抑歟? 噫!吾之道不為不明,吾之命未為未偶,而見志于斯文者,懼來世任臣之君因謗而去賢,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故復嗣數賢之作,以九為數,命之曰《九諷》焉。嗚呼!百世之下,復有修《離騷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不為乎《廣騷》、《悼騷》也。[1](11)
重視抒寫人生失意不偶的為文宗尚,由此可見一斑。他的《悼賈并序》一文也說:“(賈)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沅、湘,沉文以吊之。”[1](17)屈原的遭際,不僅令同樣沉淪不遇的賈誼嘆息不已,也激起皮日休心靈的共鳴,“余悲生哀平之見棄,又生不能自用其道”,并進一步說道:“吾之道也,廢與用,幸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后,得其文而存之者,復何人也。”[1](17)語辭委婉含蓄,不過字里行間不僅是對屈原、賈誼不幸遭遇的哀悼,也是對自己志不獲騁的喟嘆,更是自己意欲以文章抒寫人生失意情懷的隱曲表述,所闡明的正是與韓愈、柳宗元一脈相承的“不平則鳴”說。
陸龜蒙、羅隱均有與皮日休相近似的言論。陸龜蒙在《笠澤叢書序》中云“內抑郁則外揚為聲音,歌、詩、頌、賦,銘、記、傳、序,往往雜發”[4](228),表明自己藉創作來抒發內心的情感,從而宣泄胸中的憤懣。羅隱在《讒書·重序》中直言:“蓋君子有其位,則執大柄以定是非;無其位,則著私書以疏善惡”[3](241),既遙承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也與韓愈、柳宗元所主張的“不平則鳴”有著內在的統一性。
此外,陸龜蒙還自覺繼承并發展了韓愈的“窮苦之言易好”理論。“窮苦之言易好”理論,是韓愈在“不平則鳴”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發揮而成。他在《荊潭唱和詩序》中云:“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句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5](154)認為文章優劣與個人遭際息息相關,身罹不幸之境、困窘不堪之人,抑郁積胸,發而為文,必使文章臻于精工。不過韓愈僅是客觀地指出文學作品優劣與個人遭際的關系,而陸龜蒙除意識到這一聯系外,尚能挖掘造成“窮苦之言易好”這一文學現象的社會根源。他在《書李賀小傳后》中曾無限悲憤地慨嘆道:“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 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 長吉夭,東野窮,玉谿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4](270)李賀仕進不能過早夭亡,孟郊屢試不第困窮潦倒,李商隱扎掙于黨爭的漩渦中抑郁而終,不幸的遭逢確實令其創作出卓異不群的文學作品,不過他們終究因在不公平社會無法容身,在困窘與失意中離世而去。陸龜蒙將此歸咎于“暴天物”的封建統治者,見解深刻,同時也深化了韓愈“窮苦之言易好”說之理論內涵。
三、“尚奇”
孫憔、陸龜蒙為文宗尚奇崛、怪奇,其文學主張顯然與韓愈一脈相承。
韓愈為文尚奇,自稱“少小尚奇偉”(《縣齋有懷》),他在《答劉正夫書》云: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后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文,豈異于是乎? [5](121)
認為“怪奇”的文風,是自我風格的彰顯,藝術的獨創。他在《送窮文》中也曾言“不專一能,怪怪奇奇”[5](329),明確表明自己對怪奇文風的自覺追求。韓愈以此理論指導實際創作,自己的散文也呈現出奇崛的風格。
晚唐小品作家孫樵為文同樣主張“趨怪走奇”,他在《與王霖秀才書》中云:
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 日月五星是何等象? 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2](3690)
要求為文“趨怪走奇”,但必須歸結到奇正相生。他在《與友人論文書》中又云:“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后為奇,意必深然后為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2](3690)。他并不以形式上的“怪奇”為務,而是以一定的現實內容為基礎,包含有強調藝術的獨創性與藝術形式的特殊作用的合理內涵。
陸龜蒙為文也提倡“怪奇”。他在《怪松圖贊并序》中提出“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駭于俗”[4](264)的觀點,表明自己從文章社會效應的角度追求文風的“怪奇”。這顯然是對韓愈“尚奇”為文主張的借鑒。不過對陸龜蒙而言,他雖吸納了韓愈的“趨奇駭俗”理論,但對“奇”卻另有一番獨特見解:
天之賦才之盛者,早不得用于世,則伏而不舒,熏蒸沉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阨。號呼呶拏,發越赴訴,然后大奇出于文彩,天下指之為怪民。嗚呼!木病而后怪,不怪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駭于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4](264)
他認為文風的“怪”與“奇”同個人身罹的遭際和所處的社會環境緊密相連,是作者憤激之情的真實展現。他進而出人意料地將“怪”與“真”聯系在一起,提出“不怪不能圖其真”,認為“怪”是“真”在特定條件下的變形與異化,“真”是“怪”的內在本質與原形。換言之,即是主張為文應由情感內容上的“真”與“實”,向形式上的“怪”與“奇”進行開拓,從而令文章兼具真實的情感內容與奇崛怪怒的形式。此種理論顯然是進一步發展了韓愈的“尚奇”理論。
由此可見,晚唐小品作家的文學思想源自于中唐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韓愈、柳宗元,是在繼承韓柳文學思想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這些文學思想不僅充實豐富了中唐古文運動的理論內涵,而且也成為溝通中唐古文運動與北宋古文運動文學思想的一座橋梁。
[1] 皮日休. 皮子文藪[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2] 董誥. 全唐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3] 羅隱. 羅隱集[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3.
[4] 陸龜蒙. 甫里先生文集[M]. 鄭州: 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6.
[5] 馬伯通. 韓昌黎文集校注[M]. 北京: 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6] 柳宗元. 柳宗元集[M]. 北京: 中華書局, 1979.
[7] 葛曉音. 漢唐文學的嬗變[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0.
[8] 錢鐘書. 七綴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Abstract:Essayists elucidated their literature thoughts in a lot of creations definitely in late Tang Dynasty, which derived from Han Yu and Liu Zongyuan who wer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ancien-stale prose movement in middle Tang Dynasty. These essayists in late Tang Dynasty developed theorises such as “expressing Dao by literature” and“injustice proveks outcrys” that Han Yu and Liu Zongyuan advocating further basing on inheritance. These theories enriched and afflunced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ancient-stale prose movement in middle Tang Dynasty, and had an important effect on later generation, especially on ancient-stale prose movement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won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inking.
Key Words:essays of late Tang Dynasty; Ancient-Style Prose Movement in middle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thought
On source of essayists’ literature thought in late Tang Dynasty
LI Xiumin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China)
I206.2
A
1672-3104(2011)02?0156?05
2010?08?25;
2010?11?24
山西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YS08019)
李秀敏(1973?),女,吉林長春人,文學博士,山西師范大學講師,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學.
[編輯: 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