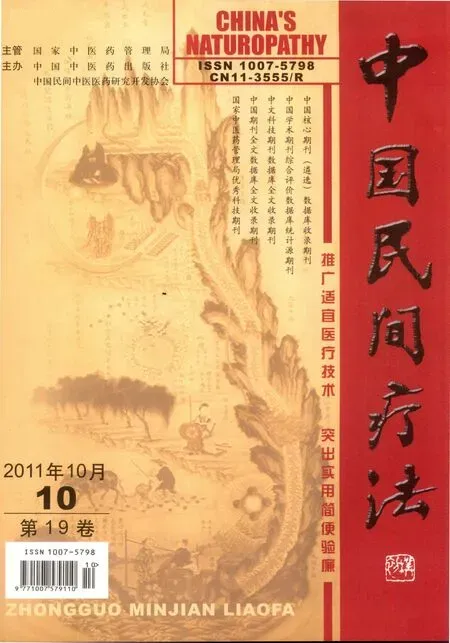治療婦科病經驗
國醫大師 班秀文
治婦必治血,治血不忘瘀
婦科病盡管虛實夾雜,但主要是經、帶、胎、產之變,其致病因素有外感六淫、內傷七情、多產房勞之分,其病情亦有寒熱虛實的不同。但婦女以血為主,以血為用,其生理活動與血的盛衰、盈虧、寒熱、通閉息息相關。如血熱則迫血妄行,可出現月經先期、量多,甚至暴崩漏下;血寒則沖任凝澀,氣血不通,可致痛經、閉經、不孕、胎萎不長。故治療婦科病,班老強調不論溫、清、補、消均要考慮到婦女以血為本,陰血難成而易虧、血分易虛易瘀的特點,選用既止血化瘀又不傷血之品,如三七、藕節、茜根、大小薊、蒲黃炭、炒山楂等,尤善用雞血藤,以其能入血分,以補為主,補中有化,久服亦無傷血耗陰之弊。如為出血的病證,班老常在止血的同時,不忘化瘀血,崇尚唐宗海“凡血證,總以祛瘀為要”之說。認為婦女瘀血的病因,在臨床上常見的有氣滯、氣虛、寒凝、熱郁、濕困、創傷以及出血處理不當等。根據瘀血的不同病因,采取不同的治則。常用有理氣化瘀、益氣化瘀、溫經化瘀、涼血化瘀、養陰化瘀、補血化瘀、燥濕化瘀等法。
根據婦女“有余于氣,不足于血”的生理特點,在治血的同時,班老著眼于疏肝理氣。由于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血隨氣而行,氣賴血以載,氣行則血行,血到則氣到,氣滯則血凝。氣分的寒熱升降均與血分密切相關。故在治療婦科血分病證時,除養血外,還要注意處理好氣與血的關系。由于肝藏血而主疏泄,主升發,喜條達而惡抑郁,體陰而用陽,為沖任二脈所系。肝氣是否舒暢條達,與婦科疾病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班老在理血的同時,常配用合歡花、素馨花、柴胡、香附、郁金等疏肝開郁之藥,以為順氣、理氣、調血之用,使氣順則血順,氣行則血行,以防止瘀血之形成。
治帶先治濕,治濕不忘瘀
帶下病為婦科常見病,其病因復雜,雖有六淫之侵、七情之擾、房勞多產、飲食勞逸等因,但均與濕有關。濕的輕重多少,關系到病情的深淺程度。班老主張治帶要先治濕,只有祛除濕邪,帶脈才能約束。治濕之法有溫化與清化之分。蓋濕為陰邪,其性重濁黏滯。只有通過溫化,才能使脾得健運,腎得溫煦,激活先天之生機,使水谷精微清者輸布全身,濁者從膀胱排出體外,升清降濁,帶脈得以維系。又濕邪為陰邪,最易阻遏陽氣,且濕邪蘊久易化熱,通過清化之法,能使濕熱分離,濕熱去帶自止。溫化之法代表方如《傷寒論》附子湯和《傅青主女科》之完帶湯;清化之法常用班氏自擬方清宮解毒飲。
治帶固然先治濕,但帶脈失約,除六淫、七情致病外,還與產后、人流術后、房事損傷諸多因素有關。通過數十年的探隱索微,班老發現帶下與瘀血關系密切。因濕為陰邪,最易阻遏陽氣,不僅使帶脈失約,更能使臟腑氣機升降失常,氣滯則血瘀;房勞產傷或久病入絡,瘀血阻塞脈絡經隧,氣機不暢,水不化氣則生濕,濕能致瘀,瘀能致濕,濕瘀膠結,病情纏綿難愈。治療中班老提出治濕不離化瘀的觀點。有兩層含義,即根據濕可致瘀、瘀可致濕的特點,首先在治療上要預防帶下病的濕與瘀合,防患于未然;其次,在收澀止帶之時要注意先用既能收澀又能化瘀之品,如澤蘭、馬鞭草、救必應等。
經者血也,帶者濕也,經帶同為胞宮陰戶所出,經帶關系密切。因為濕熱熏蒸,壅滯胞宮,既可導致水精不化,濕濁下注的綿綿帶下,又可損傷沖、任、帶諸脈,致經行失常。治療時,班老強調既要治經,又要治帶;經帶并病者,要經帶并治,在濕濁帶下嚴重之時,通過治帶可達治經的目的。一般而言,實證以治帶為主,從帶治經,虛證以治經為主,從經治帶,班老在國內率先提出了經帶并病、經帶并治之說。
藥貴沖和,善用花類
根據婦女有余于氣,不足于血的生理特點,班老主張用藥以沖和為貴,寒溫相宜。如偏于補陽則易動火而耗血傷陰,若偏于養陰則滋膩礙脾,故藥宜取甘潤沖和,掌握補而不膩,利而不伐,溫而不燥,涼而不寒,補陽配陰,補陰配陽,補中有化,化中有補的用藥原則。在病情需要用偏寒偏熱之品時,則講究配伍法度,注意柔中有剛,剛中有柔,剛柔相濟。對于寒熱虛實夾雜病證,臨床上又有攻補兼施、寒熱并用、補中寓清、化中有補之分。
藥物除寒熱溫涼之性外,尚有升降浮沉之勢,而花者,華也,集天地之靈氣,凝本草之精華,性味平和,質輕芳香,有升發陽氣、醒脾悅肝之力,可調達氣血,尤適合體質嬌嫩、不堪藥性之偏頗之婦女使用。用之得當,可使肝之怫郁得解,脾之運化能行,氣血調達,經帶如常。班老常用的花類藥有:偏于上焦者有金銀花、菊花、玉蘭花、合歡花、密蒙花等;用于中焦者有密蒙花、佛手花、素馨花;用于下焦者有凌霄花、雞冠花;兼有化瘀行血作用的有田七花、玫瑰花等。在辨證的基礎上,在大隊的補益劑中,酌加一二味花類藥,能使之補而不滯,健運脾胃,而達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