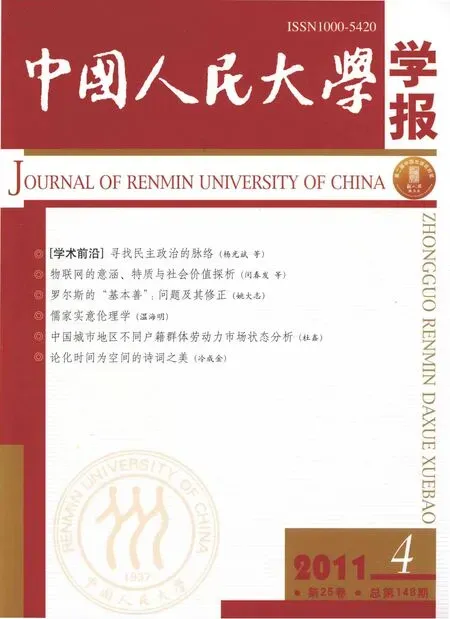日本近代“道德”、“倫理”概念的變遷
李 萍
本文所說的日本“近代”,指幕末至昭和初年,大體時間約為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30年代。日本在這一時期受到西學的影響,經歷了重大的思想激蕩,完成了一系列的社會變革。本文擬以“道德”、“倫理”兩個概念的變遷為例,分析日本社會自身原有的倫理思想如何應對西方觀念的沖擊并進行了怎樣的適應性調整。
一、近代初期譯介西學過程中“道德”、“倫理”的變形
西方的“倫理”和“道德”概念分別產生于古代的希臘時期和羅馬階段,據說是亞里士多德最先將ēthos改造為ethic,并留下了人類第一部倫理學著作《尼科馬可倫理學》,而西塞羅則將拉丁文的mores發展為moralis。“倫理”、“道德”的古義均為“風俗”、“慣例”,經思想家們提煉后開始指普遍、共有的行為規范。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西方古典時期倫理學的核心是探討如何使一個人的生活變得有意義或幸福。這一問題通常又被歸結為道德與幸福的關系問題。在哲學領域,“道德”、“倫理”的起源義均為“風俗”、“習慣”,所以“道德”、“倫理”并未被嚴格區分,只是個別思想家因關注點不同而偏重“道德”(如斯密、康德)或“倫理”(如黑格爾)。在西方倫理思想中,“道德”或“倫理”的最終根據大多訴諸永恒的信念或人類理性,這樣的信念和理性可以為“道德”、“倫理”提供終極意義上的支撐。雖然在藝術審美、社會批判、文化構建等方面,近代西方都有徹底世俗化的轉向,但在倫理思想領域,西方社會則或多或少保持了對信仰的敬重。在哲學上,這樣的信念被不同的哲學家分別以“理性”、“知識”、“良心”、“自由意志”等概念加以表達。
在日本,大規模地接受西學(最早稱蘭學,后稱洋學)始于享保元年(1716)德川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所進行的“享保改革”。佐久間象山(1811—1864)雖然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儒學家,但也十分關心蘭學,并鉆研了西方的自然科學、兵書、醫書和制炮術。他以朱子學的“格物窮理”思想為基礎來理解近代西方的科學,提出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重要命題,將西方近代成就限制在技術這一范圍。在他看來,雖然西學比傳統“格物”更精致、更實用,但無非屬于“藝術”或“技藝”之列,“道德”則只存在于東洋思想中。他所說的“道德”即儒家的道德規范、社會秩序觀念,或者說未經改變的、恒常不變的傳統價值觀念,這樣的綱常名教自然只能在傳統的儒學體系中尋找。佐久間象山篤信只有“東洋道德”才能保證承認差別的身份秩序的存在(東洋社會結構的合理性),斷定它優越于西方類似的東西,所以,完全不必學習或引入西方此方面的內容。可見,佐久間象山所說的“道德”并沒有超出傳統儒學的范疇。
1868年發生的明治維新改寫了日本的歷史,日本自此開始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等資本主義化過程。明治時代也是日本近代思想激蕩、黨派紛爭的時期,在各種勢力的綜合作用下,日本近代社會的轉型不僅是漸進的,也是幾經反復和充滿血腥的,思想界進步與復古、革新與保守的斗爭始終沒有停止,在“道德”、“倫理”問題上也不例外。
譯介西方哲學最為熱心者當推西周(1829—1897)。他曾進入幕府為翻譯歐美科技方面的書籍而設立的“蕃書調所”學習。1862年。他為了完成購買軍艦的手續和掌握軍艦操縱技術,以海軍留學生的名義被派到荷蘭留學。西周利用這個機會,廣泛涉獵了當時歐洲的社會科學及哲學研究成果,特別是當時十分盛行的密爾的功利主義和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他最初把“philosophy”稱為“西方的性理之學”,并認為“西方的性理之學”(類似于程朱理學)與經濟學(類似于王政學)一樣都是實學。他于回國后的第二年(1866)撰寫了《百一新論》,這是一本試圖把西方各種學問加以綜合統一論述的書,也被認為是日本第一部哲學知識啟蒙書。該書明確地把“philosophy”翻譯成“哲學”,并認為哲學就是“通過參考物理、探明心理,確立用于揭示天道和人道的教之方法的學問”,它是統一“百教”的根本學問。“哲學”又被細分為致知學(logic)、性理學(psychology)、理體學(ontology)、名教學(ethics)、政理家之哲學(political philosophy)、佳趣學(aesthetics)、哲學歷史(histo ry of philosophy)和實理上哲學(positive philosophy)。[1](P21-23)他還指出,儒學的一大弊端是“對政(政治學、法學)、教(道德學)的思考的確混亂”[2](P106),必須把外部的政治、法律的世界與內部的道德、價值的世界截然分開。需要指出的是,他對ethics的翻譯并不一致,有時是“道德學”,有時是“名教學”。不過,他確實對“道德”與“倫理”做了不同的解釋,認為“道德”(moral)與內在價值相關,“倫理”(ethics)則是關于道德的系統理論。這一解釋對后世理解、使用“道德”、“倫理”概念產生了重要影響。①至今,在中國,為數不少的人認為“道德是關于善惡的觀點”,“倫理是道德的系統理論”,又被稱為“道德哲學”。
與西周把哲學看做是實學、是統一個別科學的方法論(實學式哲學觀)不同,中江兆民(1847—1901)把哲學理解為探究更高級的(或者說次元的)形而上學諸問題的學問(理學式哲學觀)。他于1886年撰寫了《理學鉤玄》,其中所設定的哲學體系包括“性理”(psychology)、“論理”(logic)、“法式”(mothod)、“原理學”(metaphysic)、“世界的害惡”(multi-monde)、“道德”(mo ral)。中江兆民也將mo ral翻譯成“道德”,但認為“道德是以正當不正當的觀念和這種自知的能力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3](P110)不同于西周將哲學的各個分支并列,中江兆民把“道德”看做哲學的最高階段,是其他哲學內容如性理、法式、原理學等的運用。這種理解具有西方學問條分理析的特點。
新渡戶稻造(1862—1933)曾游學歐洲多國,最后定居美國。他用英文著述來介紹自己祖國日本的思想文化,尤其注意到了日本人的道德與西方人的道德的差異。在歐美游歷時,他經常被那些知道日本學校不進行宗教教育的歐美人問這樣一個問題:不進行宗教教育又怎樣實施道德教育呢?常常被這樣的問題所困惑,總是不能馬上作出回答,這促使他對此進行了長期的思考。后來他發現,自己被灌輸的道德觀念正是“武士道”,于是,他萌發了讓自己的美籍妻子和更多的歐美人理解日本人道德的念頭,從而用英文寫下了《武士道:日本的精神》一書,通過對武士道的描述來說明日本傳統道德的根基及特點。他在書中所理解的“道德”已經帶有強烈的西方色彩,即生活方式、習俗、慣例,而非傳統儒學的禮教內容。
進一步撇清“道德”的傳統內容,為其加入近代元素的是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4—1901)。他將“道德”與“富足”聯系起來,認為道德與富足兼具才是“文明”的狀態。他說:“所謂文明是指人的身體安樂、道德高尚,或者指衣食富足、品質高貴。”[4](P30)這里反映出與傳統思想的重要區別:傳統思想主張道德就是人生價值所在,也是評價、解釋意義的根據,是目的本身;但福澤諭吉卻將“道德”作為“文明”的一個構成要素,而且是體現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這樣,“道德”就被工具化了。此外,他不僅承認西方科學、技術的先進性,也肯定了西方道德的合理性,甚至指出西方道德的合理之處在于注重公德、興公德。他明確且富有創意地將統一的道德一分為二,劃分出私德和公德兩個部分:“凡屬于內心活動的,如篤實、純潔、謙遜、嚴肅等叫做私德”;“與外界接觸而表現于社交行為的,如廉恥、公平、正直、勇敢等叫做公德”。[5](P73-74)在文明社會,公德比私德重要,智慧比道德重要。日本傳統道德“是專指個人的私德而言的”,只有將私德轉化為公德,傳統的“君子”才能轉化為文明社會的“國民”。正是在福澤的大力傳播下,“公德”以及“社會道德”的概念自明治中期以后在日本知識界普遍流傳開來。其實,在西方倫理學中,并沒有公德和私德的概念,也從未出現關于公德與私德的討論,但福澤諭吉卻把當時西方社會達到的社會道德狀態理解為“公德”,這樣,既可以為傳統東方道德留下生存空間(作為個人心性修養),也提出了后起國家在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加強社會道德普及和提升全民道德共識的問題。公德與私德的劃分盡管在學理上仍存在不少問題,但現實意義非常重大,它甚至也影響了許多中國近代思想家如梁啟超、孫中山、魯迅等人。
二、明治中后期融合傾向的出現
明治10年代后半期至2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開始致力于確立近代國家和培育國民道德。1879年頒布的《修訂教育令》把“修身科”首次提到所有教科的前列,成為“日本國民教育的核心”,日本的近代教育也由此從主知主義轉為德育主義。中日戰爭的勝利(1895)進一步增強了日本人和日本政府的自信,以致出現了狂熱的民族主義浪潮。在哲學領域,出現了與啟蒙思想相對立的、以引導國民思想為目的而復活儒教思想的傾向。
元田永孚(1818—1891)于明治12年(1879)稟天皇之意撰寫了《教學大旨》,明確提出:“自今之后,基于祖宗之訓典,專以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人人尚誠實之品行。然此,各科之學隨其才器,日益長進,道德才藝,本末具備。”[6](P137)他將道德、才藝分別置于本末的對陣之中,將接受西學的范圍限定在技術領域,用儒教的“仁義忠孝”作為日本人精神的核心。因為儒家所強調的忠誠和孝的觀念非常適合建立統一的君主立憲國家,在這樣中必須保持一元意識形態的絕對統治。在他的倡導下,以教化為主的道德教育逐漸取代了明治初年建立在西方啟蒙觀念基礎上的自主教育模式,以便減少西方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思想的負面影響;道德教育開始被看成強化國家的工具,道德的禮教內容及其教化功能等都受到推崇。元田永孚又從傳統儒學德目中選出了20個作為《幼學綱要》(1882)的核心,認為這些德目是建立穩固的帝國而必須對國民進行的道德教育內容。這20個德目是孝行、忠節、和順、友愛、信義、勤學、立志、誠實、仁慈、禮讓、儉素、忍耐、貞操、廉潔、敏智、剛勇、公平、度量、識斷、勉職。他的思想成為《教育敕語》(1890)的理論基礎。但元田永孚畢竟是受到了近代思想洗禮的學者,他的復古仍然為西學的合理內容留下了少許空間,例如,在20個德目中,公平、勉職都是具有時代精神的,而且對一些傳統德目也賦予了部分新的詮釋,如信義、立志、儉素、識斷等。
如果說元田永孚是復活舊道德的急先鋒,那么,西村茂樹(1828—1902)則溫和同時也精巧了許多,他主張在折中東、西道德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道德體系。西村茂樹用“道德立國論”來批判西周的政教分離的觀點,并于1887年出版了《日本道德論》一書。他認為依托國民道德實現了國內統一的日本,也可以憑借國民道德確保國際上和外交上的自立目標。但西村并沒有簡單地照搬傳統儒教,而是增添了新內容。他把“道德之教”分成“世教”和“世外教”,前者包括東方的儒教和西方的哲學,后者包括佛教和基督教。他把后者作為“下等社會民眾”的信仰而加以排斥,將前者作為“上等社會人物”的道德而奉為國民精神的支柱,換句話說,他力圖將儒教和西方哲學加以綜合,構成“日本道德的基礎”。不過,他所說的西方哲學主要指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為此,他舍棄了西方哲學的一般世界觀和形而上學立場以及其他主流的哲學體系,而保留了在理論的精密性和方法論的有效性上具有明顯優勢的實證主義哲學流派。
井上哲次郎(1855—1944)最熱衷融合東西方道德,他的思想以承認皇權、國體為前提,被稱為國家主義的東洋道德之集大成者,但他的融合說表現出“命題之作”的局限性。他一生的學術目標就是融合東西方思想,將東方傳統思想與西方哲學進行嫁接,用西方哲學的方法來挖掘、整理東方思想的內容。井上哲次郎與蟹江義丸編輯、校訂了十卷本的《日本倫理匯編》,卷一至卷三為陽明學派,卷四至卷六為古學派,卷七、卷八為朱子學派,卷九為折中學派,卷十為獨立學派和老莊學派。這套書在解釋日本傳統倫理思想資源時,力圖將東西方的道德理論融為一體,例如,他們從日本古學派的思想中發現了類似于西方的“自由研究的精神”,認為日本朱子學所倡導的道德學說與德國觀念主義倫理學說有異曲同工之處,等等。
即便在軍國主義政治高壓下,一些學者也受到西方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的鼓舞,堅持對“道德”、“倫理”的獨立思考,反對單純的復古或一味迎合政府教化的意圖。大西祝(1864—1900)曾經尖銳地批判官方的《教育敕語》不是倫理學研究者自由討論、學術交鋒的產物,而是專制政治、君主意志的體現,它雖然部分反映了政府對國民特定道德德性的關注,但完全忽視了倫理學的理論爭辯。大西祝表現出的自由主義精神在當時還有一些追隨者,如桑木嚴翼、中島德藏。相比于“國民道德論”的喧囂,這種理性的、批判的聲音卻明顯曲高和寡、應聲了了。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思想潛流一直存在于部分學院派學者身上,它日后成為日本知識界構建獨立的倫理學體系的核心力量。
明治末年至大正的二十多年間,日本思想界出現了一個活躍期,教養主義、人格主義、觀念主義、文化主義、日本主義等各種思潮或運動風起云涌。在1898—1901年間,日本學界主要圍繞道德的作用問題展開了大討論,起因是:當時的很多調查結果和民間的反映是,明治維新以來,法律侵入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缺乏道德補充的法律并不能充分保證社會秩序和民眾的凝聚力。人們開始懷念道德制約法律、引導法律的前現代社會環境,這進一步推動了強化德育主義的傾向。但學術界并未簡單地拋棄法律,轉向人倫道德,而是引入了一個西方概念“人格”(personality)。“道德”之所以優越于法律,沒有道德的社會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為道德是建構人格的重要力量,道德能夠為人格提供內在支撐。中島力造(1857—1918)是第一個翻譯“人格”概念的人。人格概念的引入使日本近代的倫理學與心理學、法理學等現代學科之間建立起緊密的聯系。由于人格概念對道德主體特征的揭示,有利于強調道德的精神性、內在性因素,這也使得道德可以擺脫傳統的輿論、他人眼目、相互規勸式的外在作業或他律模式,使道德在世俗化世界中獲得了有力支撐。
如果說福澤諭吉最先注意到道德的社會調節功能,涉澤榮一(1840—1931)則將道德的社會調節功能直接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因。作為日本近代企業之父的涉澤榮一提出了著名的“《論語》和算盤一致論”。他說:“道德和經濟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缺一不可,換言之,《論語》和算盤并不是對立之物,可以右手拿《論語》講之,左手拿算盤計之,退則可利家和富國,進則可理天下之經濟。”[7](P379)涉澤在經濟界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他將營利與求道、經濟與道德相融合的做法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的風潮,即力圖用具有儒家色彩的道義來融合近代西方的功利意識、權利觀念。
三、“道德”、“倫理”概念的確立
自19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就沒有停止過對外的侵略、征服,但日本國內相對穩定,資本主義經濟得到發展,資本主義政治目標也得以部分實現,因此,在思想界并沒有完全關閉學習西方的大門,也沒有停止對自身傳統的思考。“日本知識分子當時如醉如癡地探討的是在一個現代國家中道德的基礎,以及道德與宗教、法律、科學理性的各種關系。”[8](P428)在此期間,日本出版了大量西方關于道德的撰述,并進行了初步的反思和綜合的理論建構工作。例如:蟹江義丸和桑木嚴翼共同主編了《倫理學書解說》叢書(富山房出版),共12冊,分別評述了杜威、斯蒂文等人的倫理學。阿部次郎(1883—1959)出版了專著《倫理學的根本問題》(巖波書店),這是一部系統探討倫理學理論的著作,其中的問題意識和論證方式都借鑒了西方的思想。
在文學界和一般社會思潮中也體現了道德觀念的變遷。有關“教養”、“理想”等問題的討論、自然主義的盛行及對其的反思等都對當時日本人的道德觀產生了深遠影響。自然主義對當時的日本來說具有反叛性,因為它背離了集團主義的獻身倫理和民族主義的團結道德,主張對自我本性的回溯,用自然而然的情緒、利益、感性來反對充滿高壓和一體化要求的社會道德氛圍。評論家石川啄木在《時代閉塞的現狀》一文中表達了對當時苦悶、憂郁的精神生活的感受,指出“自然主義”與其說是文藝上的一種思潮,毋寧說是在明治30年代中形成的新自我意識的根本支柱,年輕人的“私我主義”是社會“閉塞”的折射。在石川啄木的論述中,“道德”已經不再是傳統的修身范疇,而是與現實生活相關的思慮。他曾這樣追問:“每年數百公立和私立大學的畢業生,卻有一半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借宿在貧民窟中……比他們要多幾十倍、幾百倍的年輕人卻在半途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失去財產的同時也失去了道德心的貧民和賣淫婦激增說明了什么?”但從哲學層面上說,自然主義掙扎于進化論的唯物論和新康德派的觀念論之間,是一種抱有理想主義卻又不得不屈服于現實的威權主義倫理。不過,在當時的日本思想界,占據主流地位的還是主張倫理理想主義的德國新康德派思想、提倡人格說的唯心論和主張自我實現說的英國新理想主義。
在近代日本思想史上,在哲學和倫理學領域建樹最為卓著的是西田幾多郎和和辻哲郎。西田幾多郎(1870—1945)的代表作《善的研究》(1911)確定了“西田哲學”,被認為是現代日本哲學的肇始。他將西方的“有”與東方的“無”作對比,“以回歸后者的軌跡為論說的首要著力點,既可以在復興東方文化的過程中,又可以在調和東西倫理的過程中,找到其各自的理論依據,所以西田的《善的研究》是明治日本的哲學、倫理學的歸結,也可以理解為走向大正、昭和時期的轉折點”。[9](P378)不過,構成西田哲學思維底色的仍然是東方的禪宗,貫穿西田眾多著述的主線可以說是東方倫理高于西方倫理的優越感。
從“人格”和“自我”的探求出發所進行的“人格本位的實踐主義”式倫理學探求,可以說是一種相對獨立的倫理學體系,主要體現在《作為人間之學的倫理學》和《風土》的和辻哲郎倫理學之中。和辻倫理學的主體不是西方文化的“人”或傳統儒學的“君子”,而是“人間”。“人間”是“人”的同時,也是“人世之中的人”,在此雙重結構中的“人間存在的根本理法”被理解成這樣一種辯證運動:它“通過個人(即對全體性的否定)進一步實現全體性(即否定之否定)”,即“絕對的全體性的自我實現的運動”。和辻深刻地指出,擁有各自歷史的國民,只有在其特殊性中追求自身全體性的形成,真正意義上的inter-national的關系才成為可能。“國民道德”的問題只能在倫理學的終篇得出結論。在日本現代哲學史上,西田哲學、和辻倫理學都被視為日本化的哲學成就之重要代表。
在現代日本,哲學界鮮有討論“日本人的道德”或“日本社會的倫理”之類的問題,與此相關的話題都被歸入“日本人論”或日本國民性的討論范圍。在專業書籍和學術詞典中,“道德”和“倫理”的解釋已經非常具有現代性了。例如,在《現代哲學事典》中,對“道德”的解釋是:“所謂道德,就是關于人應該像人一樣行動的要求之探討,一般認為它與倫理同義。”[10](P462)“倫理”則有兩個條目:“倫理I”是對英語ethics的解釋:“倫理與道德同義,都起源于風俗,倫理學或道德哲學在現代西方被分為規范倫理學和元倫理學兩支。”而“倫理II”是對人倫的解釋:“所謂倫理,就是關于人倫的理法,因為倫指人的小組和人的關系,理就是對這樣的人的小組和人的關系所作出的條理規定……倫理這樣的詞匯揭示了中國思想的特色。”[11](P466)日本著名學者河合隼雄、鶴見俊輔主編的《倫理與道德》一書對道德和倫理的定義分別是:道德“就是關于善的事物和惡的事物的社會性共識”;倫理“是不依據外部參照系、有時還與外部參照系對抗的決斷以及與個人選擇深刻相關的、構成了善惡標準的思考”。[12](P279)不難看出,在今天,日本學術界對“倫理”、“道德”的解釋幾乎與西方同仁是同步的。雖然存在差異性認識,如對“倫理”另一層含義的說明,但其作為概念強調了個體獨立意志的牽連,作為社會事項則主張通過說理、討論、訴諸思想史來澄清。
[1]宮川透、荒川幾男編:《日本近代哲學史》,東京,有斐閣,1976。
[2]日本名著全集刊行會編:《日本名著》,第34卷,東京,日本名著全集刊行會,1928。
[3]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續一年有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4][5]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6]《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0卷,《明治思想集》,東京,筑摩書房,1976。
[7]《涉澤榮一傳記資料》,第41卷,東京,青木書店,1961。
[8][9]中村哲夫:《梁啟超與“近代之超克”論》,載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10][11]山崎正一編:《現代哲學事典》,東京,講談社,2004。
[12]河合隼雄、鶴見俊輔主編:《倫理與道德》,東京,巖波書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