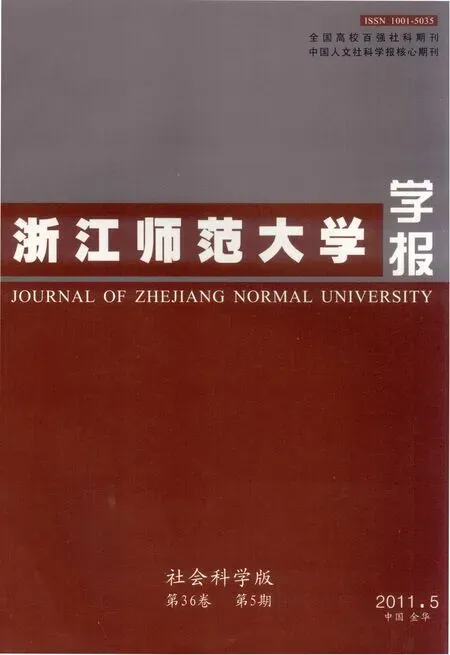辦刊實踐與品格凝練:以《文訊》雜志為中心的考察*
廖 斌
(武夷學(xué)院 人文學(xué)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優(yōu)秀雜志都有“文化身份”或“品格”,它們作為精神產(chǎn)品,肩負傳播、弘揚文化的重任,在實踐中因辦刊宗旨的逐步落實,慢慢凝練出特色和風格。資深編輯、文評家林建法說:“在做了這么多年的編輯以后,我想到了一個雜志的‘文化身份’問題。現(xiàn)在大家比較多關(guān)心作家的文化身份,其實一個雜志也有自己的文化身份,這個身份決定了雜志以什么樣的姿態(tài)置身于文學(xué)活動之中,以什么樣的學(xué)術(shù)理想?yún)⑴c學(xué)術(shù)生態(tài)的建設(shè),以什么樣的方式進行知識生產(chǎn),以及這個雜志作為中介如何來建立文學(xué)批評與文學(xué)寫作的關(guān)系等。……以此觀之,雜志應(yīng)當承擔的引領(lǐng)作用遠遠沒有能夠發(fā)揮好。”[1]縱觀文學(xué)期刊史,1930 年代“海派”期刊小報的市民文化;臺灣《中外文學(xué)》、《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同仁”、“學(xué)院”性質(zhì);“潛在寫作”而賦予的“民間”屬性;《收獲》等所標舉的“純文學(xué)”、“審美性”而獲得的高雅、精致文化的贊譽;新中國《文藝報》、《人民文學(xué)》居于文學(xué)場域頂層,統(tǒng)領(lǐng)全國文藝生產(chǎn)而獲得的政治權(quán)威屬性等,都是文化品格的表現(xiàn)。本質(zhì)說,期刊編輯過程即作者的文化創(chuàng)造、編者的文化選擇及讀者的文化認同的過程;作者、編者、讀者的關(guān)系即文化制約與文化互動的關(guān)系,面對全球化浪潮、市場利益驅(qū)動與大眾文化沖擊,只有傳承優(yōu)質(zhì)文化,打造良好品格,塑造獨特風格,才能吸引讀者文化視線,突顯中華傳統(tǒng)文化資源的魅力,這是期刊最根本的定位。
一
《文訊》由國民黨文工會創(chuàng)辦于1983年,是“近20年來臺灣文壇的重要存在”,對兩岸文學(xué)交流及臺灣文壇的良性發(fā)展有重要作用,期間歷經(jīng)威權(quán)體制到多元開放、合并到獨立、黨辦到民營的艱辛,忝為世界華文學(xué)界重鎮(zhèn)。它的發(fā)展?jié)饪s了臺灣文學(xué)傳媒的嬗遞和當代文學(xué)篳路藍縷的拼搏歷程。辦刊28年,型塑清新的形象,凝練出匡扶時弊、感時憂國、入世濟世、敬重人倫、重情信義、助人為樂、擔當?shù)懒x、勇挑責任、和諧為貴的文化品格;學(xué)術(shù)上兼容并包,體現(xiàn)出“老中青皆尊,各流派并重”,[2]重道德教化,重教育、文學(xué)的群治,倡文運,重視文學(xué)與整個社會的互動等多面向。作為臺灣文壇最重要的雜志之一,2003年國民黨宣布停止經(jīng)費挹注時,“文訊震撼”數(shù)見于報章,咸謂臺灣社會價值抉擇的一個課題,學(xué)者陳芳明指出:“《文訊》所放射出的意義,所代表的理想,不但屬于國民黨,也屬于整個社會,撐起了臺灣社會的文化象征,這樣說,絕無絲毫夸張。”[3]因此,《文訊》蔚為臺灣高文化品格的期刊。
期刊編輯學(xué)有“編者運作理論”(editor-operation theory),與“讀者接受理論”呈辯證關(guān)系。理論上說,雜志和市場的接受程度密切相關(guān),讀者接受程度越高,雜志越受歡迎,出版行銷越好,但這只是市場表相。深層看,還存在轉(zhuǎn)換者機制(transmitter mechanism)問題,亦即被動的讀者之所以接受某種期刊、某類作品,其實來自出版者(包括雜志及副刊編輯)的“鼓勵”。所以,《文訊》后面隱藏的“編輯群體”實際上賦予了刊物以活潑潑的生命力,期刊就是一個生命綜合體,融匯編輯和主事者的思想情感、光榮夢想、文化心理乃至世界觀、價值觀,這些要素,反之又對《文訊》的品牌鑄造、文化實力與品格塑造居功至偉。一句話,刊物的品格是編輯思想傳承、精神文化、個性理念、興趣愛好、人格意志的外化,編輯是活躍而穩(wěn)定的決定因素,他們在文學(xué)與文化建設(shè)上扮演啟蒙者、引領(lǐng)者、范導(dǎo)者、薪傳者,對臺灣文壇融入深厚的人文關(guān)懷。
首先,從編輯宗旨看,《文訊》確立文化品格的第一面向:為文學(xué)立命,為文學(xué)而文學(xué),拯救文學(xué)于困厄的深厚情懷。在文學(xué)邊緣化的今天,《文訊》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理念為文學(xué)掌燈,它的慘淡經(jīng)營、默默堅守、無怨無悔、永不回頭的執(zhí)著,自有悲壯動人的一面,更催生文學(xué)人發(fā)憤圖強的信念。封德屏總編輯說:“不可否認,經(jīng)營的辛苦,讓我們有時不免涌現(xiàn)一種心酸凄涼。在文學(xué)閱讀式微的今天,‘獨立自主’談何容易!為了這些可愛、可敬的作家,為了支持《文訊》屢渡險灘的眾多前輩、好友,我們許了諾、發(fā)了愿,也必將努力去實現(xiàn)。”[4]這段話正是艱苦創(chuàng)業(yè)歷程的真實寫照。臺灣是“全世界雜志競爭最激烈的地區(qū)”,[5]“有發(fā)展趨于成熟的雜志出版業(yè),每年超過40 000種新書上市,出版近5 000種雜志;加上進口的外文雜志,總品項超過9 000種,是一個活潑而熱鬧的雜志社會,更是一個競爭激烈且成熟擁擠的商業(yè)市場。……幾乎只要有一種社會興趣的存在,就有一種與之對應(yīng)的雜志類型”,[6]“到1997 年,臺灣注冊雜志有5 600 種”,[7]其數(shù)量十分驚人。在種類分布上,財經(jīng)類以超過第二位數(shù)百種的優(yōu)勢穩(wěn)居首位,其后是教育文化類、宗教類、社會類。政論類雜志影響下降,黨外雜志風光不再,純文藝類雜志數(shù)量驟減,副刊漸趨八卦娛樂化,博客、論壇及休閑雜志成為閱讀新寵,臺灣的雜志業(yè)進入白熱化競爭。向陽指出:“這十年來,文學(xué)雜志不增反縮,文學(xué)出版社更是備受市場打擊,大型連鎖書店每月提供的所謂‘文學(xué)類排行榜’成為對文學(xué)最無情的嘲諷和最可悲的笑話,‘純文學(xué)’已停,‘大地’不在,‘洪范’、‘爾雅’余音裊裊,‘九歌’易調(diào),七○年代的‘五小’盛景日薄。我們看到的,《聯(lián)合文學(xué)》、《中外文學(xué)》、《文學(xué)臺灣》等純文學(xué)雜志艱難苦撐,繼續(xù)前進,而歷史悠久的《臺灣文藝》最近又傳出面臨停刊的訊息,顯然,文學(xué)雜志并未因為副刊走向大眾化而開拓岀更大的純文學(xué)閱讀市場。”[8]但是《文訊》不管如何艱難,對文學(xué)永不放棄。陳昌明教授任職臺灣文學(xué)館期間曾想動支5千萬元新臺幣收購《文訊》典藏的圖書資料,以充實文學(xué)館。時值2003年,《文訊》處于最困苦時期,但封德屏婉拒這份請求。感佩之余文學(xué)館請《文訊》幫助實施文學(xué)專案,雖經(jīng)費不多,卻也有所助益,而《文訊》回報的是精彩豐富的產(chǎn)品,“如《臺灣現(xiàn)當代作家評論資料目錄》等文學(xué)史料,至今都是臺灣文學(xué)館引以為傲的成果,對臺灣文學(xué)研究有相當大的貢獻。”[9]《文訊》民營后,第一年的經(jīng)費百分之五十依賴募款,而后逐年降低外援比例。2006、2007年外緣只剩下百分之十,2008年開始做到百分百自負盈虧。盡管拮據(jù),緣于為文學(xué)立命,《文訊》“不放棄以往對文藝界的服務(wù),繼續(xù)舉辦一些能啟發(fā)文學(xué)心靈的有意義的活動。這些活動雖然與市場營利無關(guān),往往是覺得最重要非做不可的”。[10]因此,在經(jīng)營壓力與工作重負下,《文訊》同仁仍披荊斬棘,努力向前,在“藝術(shù)的道路時空”(巴赫金語)中,與臺灣文學(xué)同源同質(zhì),同步發(fā)展,在眾多雜志“屢撲屢起,旋起旋滅”的市場博弈中,以精進勇猛的進取精神、富于擔當?shù)呢熑我庾R、尊老愛幼的人倫情愫,超越黨派意識形態(tài),團結(jié)各方作家學(xué)者,凝聚文壇認同,贏得廣泛支持稱道,被譽為“臺灣最寶貴的文化資產(chǎn)”,[11]這是對它為文學(xué)寫史的褒揚,更是對其堅持為文學(xué)、文化立命的禮贊。
其次,從社會責任看,《文訊》展現(xiàn)了為人生而文學(xué),相信文學(xué)、文化的社會功用,闡揚文化教化,載道明德的面向,這體現(xiàn)了《文訊》的多元思考。臺灣社會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一波又一波的斗爭、論辯隨之而來,浮躁的浪潮一襲又一襲打來;功利主義彌漫于政壇、文壇,消費社會蠶食和改變著文學(xué)的性質(zhì),但“《文訊》卻仍能抱樸守一、堅持文學(xué)品質(zhì)、文化本位,堅持多元、包容的立場和寬闊的視野,……無疑是觀察臺灣社會的心性、定力、精神、氣質(zhì)的重要指標”。[12]夏志清指出,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主流乃從清末迄今的“感時憂國”,多流露道德使命感和民族意識,耽于社會譴責及人道關(guān)懷。《文訊》雖遲至1980年代面世,卻賡續(xù)“感時憂國”傳統(tǒng),強調(diào)文學(xué)、文化的社會參與和人道關(guān)懷,它在發(fā)刊詞和“編輯室報告”中屢屢自我期許:
我們希望能在文藝界與社會大眾之間,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梁,為推動文化建設(shè)的文藝界,包括作家和讀者盡一份棉薄。[13]
執(zhí)行這一份刊物的編輯,在歷史使命與社會責任上面,特別注意古今的接合以及中外的匯通,凡此種種努力,也無非是以和為尚,導(dǎo)偏于正。[14]
從“人文關(guān)懷”欄目也應(yīng)可具體明白我們的關(guān)懷。[15]
在跨世紀之際,我們有信心再起風云;在兩岸的變局中,堅守可大可久的人道與人文之關(guān)懷;在整個世紀有關(guān)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糾葛中,超越并走出一條康莊大道;在獨統(tǒng)的激辯中,維持一貫沉穩(wěn)、清明的唱音……[16]
更著重在文化現(xiàn)實的關(guān)切與探索上面,我們希望能掌握文化脈動,參與當前文化的創(chuàng)造與論述之活動,提供文化界一個好的對話空間,更重要的是,我們將不斷探索文化發(fā)展上的臺灣經(jīng)驗,提供創(chuàng)造完美“文化中國”理想的基礎(chǔ),更愿藉此呼吁國人增進文化素養(yǎng),培養(yǎng)藝術(shù)趣味,提升生活品質(zhì),穩(wěn)定社會秩序。[17]
28年來,《文訊》以天下為己任,以期刊為“文化公共論域”,從文學(xué)跨越到大文化層面,對公共文化服務(wù)、文化建設(shè)、文明建設(shè)的責任意識、批評鋒芒表現(xiàn)得特出而頑強,充分發(fā)揮組織、策劃和論域發(fā)聲功能,凝聚大批學(xué)者專家研析探究,透過專題策劃、文化短評、專題采訪、座談討論等多種方式,指摘社會積弊,痛批惡質(zhì)文化,建言文化建設(shè),反省文化體制,有效地將不同聲音集結(jié)為公共論域的智慧,向當局和文化機構(gòu)建言獻策。基于《文訊》的“親和力”,眾多的文壇人士、知識分子積極參與,諸如傅佩榮、張雙英、林谷芳、張錯、董崇選、南方朔、閻振瀛、呂正惠、鄭貞銘、龔鵬程、高柏園、蔣震、葉海煙、余玉照、陳慧樺、古蒙仁等都是學(xué)界一時之選。他們從不同面向,比如文化的形成與發(fā)展、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關(guān)系、社區(qū)文化與文化“生活化”、文化教育與薪傳、文化交流與移植、文學(xué)與文化建設(shè)等,對文化建設(shè)、復(fù)興開出了“良方”,在眾聲喧嘩的臺灣社會找到可資討論的空間,他們所擁有的“象征資本”增值了《文訊》的聲音,形塑了民間知識分子清新的形象,構(gòu)筑了文學(xué)雜志少有的參與社會批評、文明批評的公共論域,對當代臺灣貢獻頗多。蘇其康教授說:“‘人文關(guān)懷’絕不是一個空的口號,而是落實在《文訊》的各種文章和書寫中,……許多建議不是作壁上觀的書齋之見,而是務(wù)實性的針砭并能夠劍及履及,是有價值的文化評論。”[18]這種“位卑未敢忘憂國”、“敢為人先”、“鐵肩擔道義”的價值立場,淋漓盡致地表征了《文訊》及周遭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參與意識。臺灣傳播學(xué)者須文蔚指出,“在文藝刊物上鮮少見到文化政策的專題,文化公共論域的闕如,更顯得《文訊》雜志25年來進行過的20個文化政策專題,以及9個特別企劃,共計253篇文章,顯得異常珍貴。”[19]
再次,從服務(wù)作家學(xué)者看,《文訊》確立文化品格的第三面向:敬重人倫,構(gòu)建和諧有序的優(yōu)質(zhì)文藝倫理。李瑞騰總編較早提出“文藝倫理”的概念,意指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因文學(xué)活動在文學(xué)場域的延伸——諸如世代、文人集團、審美霸權(quán)之間的頏頡,報刊雜志、文學(xué)流派、社團之間的競爭,都可納入文藝倫理的框架考察。尊老敬老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但臺灣社會矛盾叢生,文藝倫理備受扭曲,文學(xué)論爭裹挾藍綠矛盾,世代演遞纏繞人際糾葛,文藝評論內(nèi)藏族群之爭,而文壇前輩逐漸被遺忘。在此觀照下,《文訊》始終甘當橋梁、人梯,傾力重構(gòu)文壇長幼有序、尊老愛幼、和諧有序、團結(jié)協(xié)作的人際倫理。首先是文壇里“扶危濟困”、“仁愛和諧”。多年來,《文訊》除了向讀者介紹資深作家、文壇新銳,還以實際行動關(guān)懷處于困頓處境的老作家、學(xué)者。在物質(zhì)、精神上予以力所能及的支持。鄭明娳教授說得好:“《文訊》一直具體而微地做著本來應(yīng)該由當局來主導(dǎo)的工作。就以照顧作家來說,長年來,《文訊》挖掘年輕作家、鼓勵成長作家、照撫年老作家,可是因為人力不足、資源匱乏,只能靠著機遇點擊式努力,無法大布局地計劃、主動且全面地放手去做。就結(jié)果而論,當局和《文訊》照顧的作家可能一樣多。……而《文訊》照顧的總是鰥寡孤獨或者窮愁潦倒的作家,不論人或者事,連新聞價值都沒有,所以一直默默無聞。”[20]早在黨營時代,《文訊》就形成傳統(tǒng):探訪老作家。“今年(1997年5月)五四文藝節(jié),特別舉辦了五四文藝節(jié)探望作家活動,表達我們對文藝的關(guān)懷,對作家的敬意,藉著探訪,致贈慰問金和禮物,對曾經(jīng)奉獻心力的文藝創(chuàng)作或文藝行政工作的前輩給予溫暖與關(guān)懷。……我們拜訪了梅遜、黃得時、聞見思、陳紀瀅、郭晉秀、李牧、陳火泉等作家,希望這個溫暖的行動,能夠年年持續(xù)下去。”[21]對于遠在南部的作家,則想方設(shè)法代為轉(zhuǎn)達,如委托《明道文藝》的陳憲仁去探訪。黎湘萍十分恰切地歸納了《文訊》的品格:“尊老愛幼”、“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所謂“尊老”,指《文訊》堅持為作家、學(xué)者服務(wù)。首推一年一度的品牌活動——重陽文藝雅集,這個公益的、純粹賠錢的活動迄今舉辦22屆。封德屏總編輯說:“我們在與時間賽跑,……讓許多遺漏的作家及作品重現(xiàn)光芒,關(guān)懷貧病、弱勢作家,努力地想為他們爭取一些資源。杜甫當年‘安得廣廈千萬間,盡庇天下寒士俱開顏’的恢弘理想不敢企及,但唯有此時,能深刻體會其中的焦慮與無奈。”[22]“像這樣一個年年以資深作家為主的活動,申請經(jīng)費的困難度越來越高,……但是我們這些享受果實的后生晚輩,理應(yīng)對他們表示敬意。”[23]雅集甚至衍生為辦刊外的重要內(nèi)容:間或性的慰問、探訪;轉(zhuǎn)達問候、查找聯(lián)絡(luò)、穿梭斡旋、看望文友、出版紀念專輯甚至接濟作家。比如:為女作家嚴友梅轉(zhuǎn)達書信給作家王書川夫婦、看望重病臥床的作家劉枋、為剛過世的作家尹雪曼播發(fā)新聞稿、組織紀念專輯等。第270期說:“我們得到許多作家的信任及協(xié)助,建立了編輯與作家良好的友誼。……我們接到於梨華女士從美國寄來的”一封寫給作者的信,“他們多年未聯(lián)絡(luò),特寫了一封問候老友的信,請我們轉(zhuǎn)交”。[23]“尊老”更見諸精耕細作的編輯作業(yè),它為海內(nèi)外文壇提供老一輩作家、學(xué)者的近況。如第266期打破刊期安排,集中報道幼兒詩拓荒者薛林,活躍于20世紀60年代、后隱逸多年的許希哲,中研院院士、著名人類學(xué)家李亦園,作家黃克全,學(xué)者周策縱等學(xué)人作家。2010年第8期專文追思剛辭世的作家商禽、韓國學(xué)者許世旭。“看到《文訊》仍堅持不懈地關(guān)愛著老作家的晚年,看到李瑞騰教授對琦君執(zhí)晚輩禮,真是感動。不獨如此,對于一般作家,《文訊》也是如此,2005年1月有‘李潼紀念特輯’,《文訊》對因癌癥去世的李潼(1953-2004)的懷念,從那些質(zhì)樸真誠的文章,到為李潼編寫作年表,真令人動容。”[12]所謂“愛幼”,即不遺余力獎掖青年,提攜文壇后進。學(xué)界聲名鵲起的須文蔚、楊佳嫻、陳建忠、胡衍南等60、70后學(xué)人,多受《文訊》培養(yǎng)。《文訊》的編輯團隊均是嶄露頭角的新世代;在專案執(zhí)行小組里,盡為學(xué)有所成的碩博生;青年文學(xué)會議殿堂里,更是“青春的盛會、文學(xué)的饗宴”。臺灣文學(xué)研究的新世代就在《文訊》的思想濡染和活動、工作里成長,薪傳了文學(xué)智慧,繼承了良好的文藝倫理。
最后,從文化傳承看,《文訊》品格濃縮了忠于理想、勇于擔當、堅持操守、奉獻社會、踐重然諾等儒家文化精髓。與大陸文藝期刊政策不明朗的生存樣態(tài)相比,臺灣完全是“市場化”運作,按照布迪厄“輸者為贏”的顛倒經(jīng)濟學(xué)邏輯,在“有限生產(chǎn)次場”“為生產(chǎn)者而生產(chǎn)”。因此,《文訊》脫離黨營后只能自力更生。老作家畢璞說:“《文訊》可說是一份先天不足,后天失調(diào)的刊物,財力、人力都極度欠缺,經(jīng)費相當困難,其中甘苦,我感同身受,……《文訊》的靈魂人物封德屏女士以她過人的毅力、驚人的熱忱,奉獻了她的青春,犧牲了家庭生活,無怨無悔地把全副心力灌注在這份刊物上,不辭勞苦,不畏艱辛,就像呵護自己的孩子般去養(yǎng)育、培植,使它在荒蕪的土地上慢慢成長、茁壯;終于25年有成,它開花結(jié)果,綠葉成蔭,以獨特的風格、豐富的內(nèi)涵,贏得了無數(shù)掌聲,受到海內(nèi)外關(guān)心與愛好文學(xué)或從事文字工作的讀者們的喝彩。”[24]《文訊》的慘淡經(jīng)營,和28 年的頑強執(zhí)守,正是儒家思想譜系中踐重然諾、恪守文學(xué)理想、為文化建設(shè)而入世濟世的奉獻精神。它的主事者李瑞騰、封德屏發(fā)揮了巨大的社會動員能量和打拼精神,使這份雜志在困難中生存,在轉(zhuǎn)型中發(fā)展,在拼搏中崛起,臺灣文壇對此有很高評價。蘇其康說:“《文訊》已成為臺灣文學(xué)界甚至文化界的聚焦,……而且早就是臺灣文學(xué)界最討人喜歡最盡心盡力的義工。”[25]28年來,《文訊》想有所作為的無外乎兩個關(guān)鍵詞:文化、文學(xué),但在政黨主宰下,經(jīng)費不足,差點數(shù)度停刊,因此藝文界總是擔心這個體質(zhì)蕤弱的“小孤女”半路夭折。它能取得這樣的成就,靠的就是克難攻艱和對事業(yè)的忠誠,對純文學(xué)辦刊的堅持。即使遭逢困頓,依然反對商業(yè)文化的趨附、逢迎、惡俗,永葆文學(xué)操守,對文學(xué)人的尊重、提攜,堅持超越黨派,兼容各派;即使面臨停刊,也不改其志,表現(xiàn)了九死未悔的擔當。封德屏說:“有些朋友建議改版,重生后的《文訊》是不是焦點放在暢銷作家、流行話題上,不要盡作一些‘不合時宜’的主題。但什么是合時宜的話題呢?歷史鋪陳、智慧薪傳是持續(xù)累積,是從過去到現(xiàn)在的。我們不可能把過去切斷或者遺忘。”[26]就這樣,《文訊》不屈不撓地守護著文學(xué)這方凈土。臺灣學(xué)者高柏園說:“《文訊》同仁堅守理想,從不拿理想宰制他人。……它耐心守候所有的飄逸與風華,在默默中享受最平凡的偉大。”[27]
總之,在文學(xué)的細節(jié)處、立身安命的大節(jié)處,《文訊》執(zhí)著表現(xiàn)出“仁愛”、“濟世”、“執(zhí)中”等精神氣質(zhì);在窮與達、常與變、創(chuàng)新與懷舊間自覺扛鼎,它兼濟文壇的胸懷未嘗懈怠。一份刊物品質(zhì)精良,乃在于專業(yè)的水準和高度;但既得到專業(yè)的贊譽,又得到文壇交相稱頌,由衷喜愛、尊敬,那一定是文化基因與品格在起作用。
二
臺灣新文學(xué)發(fā)展迄今60余年,賞鑒眾多文學(xué)期刊的品格,慣有為文學(xué)而文學(xué)者,如《純文學(xué)》。《純文學(xué)》由林海音于1967年元月創(chuàng)辦,它以文學(xué)創(chuàng)作、翻譯、名家作品選錄為主,內(nèi)容亦“兼容并蓄,不分黨派”,是臺灣早期、中期及新生代作家的重要發(fā)源地,自林海音、余光中、琦君到張系國、朱西寧、白先勇等,均有承前啟后之重。林海音在“聯(lián)副主編”時期,在“密不透風的文藝體制下,……大膽提拔新銳,什么稿子都敢登,在1963年刊出了一篇有問題的文字,遂鞠躬下臺”。[28]但是,無論《純文學(xué)》,還是其他刊物如《文壇》、《作品》,堅持辦刊理想,堅持純文學(xué)立場,更多是編輯的職業(yè)需要和本能,少了《文訊》的艱難轉(zhuǎn)型及屢次涉險的經(jīng)歷,和當今在大眾文化圍剿和市場白熱化競爭的特殊情境下的自覺意識與勇于擔當,從而也少了悲壯與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敢決絕;也有淑世情懷者,如《明道文藝》,它在總編陳憲仁的經(jīng)營下,大膽刊用新人、尊重前輩作家,企劃性高,又貼合社會脈動;通過舉辦學(xué)生文學(xué)獎、挖掘校園新人、積極參與社會、對作家學(xué)人的生老病死表現(xiàn)尊榮敬意、推動兩岸文學(xué)文化交流,30年來,“呈現(xiàn)了溫厚、深沉的溫度和厚度,……創(chuàng)出溫暖、深厚的文學(xué)環(huán)境,這是《明道文藝》一路走來,最動人的淑世理想,一種安靜地在晦暗中為文學(xué)種夢的文化角力。”[29]但與《文訊》相比,《明道文藝》有“明道學(xué)園”這樣全臺知名的私人教育集團的雄厚財力,加之“臺灣文壇影響深遠的文學(xué)推手”、明道中學(xué)創(chuàng)校校長、著名教育家汪廣平的支持,使得《明道文藝》被譽為“臺灣作家的搖籃、臺灣文壇的源頭活水”;[30]還有以“小眾擁抱大眾”者,如《聯(lián)合文學(xué)》,創(chuàng)辦27年來,被稱為“敏銳精準的時代風向標”,融典雅/前衛(wèi)于一體。它“橫跨到藝術(shù)領(lǐng)域或次文化,從音樂、流行歌曲到卡拉絲,從華文戲劇節(jié)到柏林影展……逐一網(wǎng)羅涵納”,它充滿活力,除雜志、叢書,且有小說新人獎、巡回文藝營、研討座談等接力舉辦,彰顯了動靜兼?zhèn)洹⒒ブダ男惺嘛L格,漸成“華文雜志的翹楚、1980年代以來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文學(xué)傳媒之一”。[31]然而,《聯(lián)合文學(xué)》的業(yè)績除了歷任編輯痖弦、高大鵬、丘彥明、馬森、鄭愁予、鄭樹森、初安民、許悔之等人的努力,企業(yè)化的行銷與對流行議題的介入也成就了它經(jīng)典/時尚的文化品格,而其身后龐大的聯(lián)合報系更是可資倚重的靠山。因此,《文訊》與上述同儕相比,各有千秋,卻更具精氣神與深厚的文化氣質(zhì)。它獨樹一幟的品格,是在時代的風云激蕩中,由黨營轉(zhuǎn)型民辦、電子媒介誕生、市場化沖擊、編輯群體的理想信仰、辦刊宗旨以及《文訊》獨特的身份、經(jīng)歷中打拼、孕育出來的,可以學(xué)習(xí),卻無法復(fù)制。
與大陸文學(xué)期刊相比,《文訊》也給予很好啟迪。最近,頗具知名度的《上海文學(xué)》遭遇困難,主編趙麗宏表示,《上海文學(xué)》的收益主要有三,一是刊物本身收益,二是政府提供一定資助,三是靠社會資金贊助。雖然《上海文學(xué)》有五位數(shù)的發(fā)行量,但成本遠高于支出,靠刊物的行銷根本養(yǎng)活不了編輯部。而為了堅持純文學(xué)刊物的品位和格調(diào),“我們不會改變對文學(xué)理想的追求,不會登廣告文學(xué),不會降低雜志的品質(zhì)。”[32]業(yè)內(nèi)人士認為,在純文學(xué)尚未從困境中擺脫的當今,由國家養(yǎng)幾份純文學(xué)雜志,保留幾塊文學(xué)的陣地非常必要,因為一旦全部放開,純文學(xué)蜂擁轉(zhuǎn)向商業(yè),到時覆水難收。但問題是,純文學(xué)雜志也應(yīng)像《文訊》,多想擺脫困境的辦法,多樹立幾個品牌,多涵養(yǎng)文化品格,坐等“被養(yǎng)”,只能給人留下抨擊的口實。
學(xué)者李海艦指出,“學(xué)術(shù)期刊要有‘文化’,一是企業(yè)文化,包括辦刊宗旨、辦刊使命、目標導(dǎo)向、理念定位、論文取向、編輯模式、編輯考評、運作思路;二是職業(yè)文化,即編者要有大局意識,要有學(xué)術(shù)大師視野,要有為人作嫁精神,要有注重細節(jié)習(xí)慣;三是產(chǎn)品文化,即期刊要打上雜志社的烙印。”[33]顯然,《文訊》早已構(gòu)筑了自己的文化,“為人民服務(wù)”(陳建忠)、“文學(xué)荷光者”(隱地)、“文壇小魔瓶”(白靈)、“文學(xué)信使”(李敏勇)、“重要視窗”(劉俊)、“文學(xué)界的寶”(林澄枝)、“人少志氣大”(宋雅姿)、“救風塵”(陳柏青)等等,都是對《文訊》品格的中肯評價。《文訊》前20年為黨營刊物,為何它能夠擺脫黨派色彩,辦出另類風格,它的突破憑借什么?作為臺灣文壇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和無形資產(chǎn),值得從中找尋鏡鑒。一是非營利的因素,無經(jīng)費短缺之掣肘。早期的《文訊》坦承:“基本上,這不是一個營利的刊物,它的非市場化取向,使我們在規(guī)劃設(shè)計的時候,能夠完全站在文學(xué)的立場,采取學(xué)術(shù)的方法統(tǒng)攝過去的文學(xué)現(xiàn)象與成就。”[34]可見,文化既要產(chǎn)業(yè)化,必要時又需不計投入加以扶持。二是黨營時代,早期主管的寬容、開明和后期國民黨不管不顧,少了政治干預(yù),可以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文訊》創(chuàng)辦人、原總編輯孫起明回憶說:“周應(yīng)龍主任包容年輕人的強悍無禮,信任年輕人的見解主張,放手讓我們?nèi)グl(fā)揮,從不過問編輯計劃,從不事先審稿,使我們幾個人……不考慮國民黨的政治文化,也不管黨的文藝政策,決心走文學(xué)的路。不做傳聲筒,不做指導(dǎo)者。……從創(chuàng)刊之處起,我就決心走一條堅持文化價值、尊重文人發(fā)聲的路,……我們不分黨派、地域、省籍、男女,來稿歡迎‘文以載道’,也歡迎‘文學(xué)的歸文學(xué)’。”因此,《文訊》走過的道路,為臺灣文學(xué)期刊史展示了跳脫政治文化,“深刻、誠實地與知識分子對話,甚至辯論,以學(xué)問服人,贏得尊敬”[35]的努力。三是主事者的視野和胸懷,決定了以文學(xué)為本位。《文訊》“能在臺灣這樣的政治掛帥社會中受到重視和信賴,原因甚多,但主要應(yīng)在于編輯群的努力,和主事者的高度自制,他們……不黨不私,忠實紀錄了每個年代的文壇脈動”,[36]而且“不為政黨、文學(xué)流派或單一的意識形態(tài)機器掌控,這是李瑞騰主編時就成形的模式,在封德屏主編后更加確定”。[37]四是民營后少了政治考量,堅定了它的超越與兼容。《文訊》在市場與文學(xué)間力求平衡,企業(yè)化、團隊化、項目化管理引進期刊生產(chǎn),從產(chǎn)品包裝、宣傳到品牌的經(jīng)營,從形到質(zhì)都發(fā)生改變;產(chǎn)品意識強化,商品性質(zhì)突顯,合作意識、經(jīng)營意識不斷加強,如舉辦研討會、座談會、資料展、重陽雅集、設(shè)置文學(xué)獎等,對自身大力宣傳,營銷意識高漲。這些手段提升了生產(chǎn)力和競爭力;注重與同行、學(xué)者作家等的聯(lián)系;逐漸由純粹黨營,不考慮贏利的封閉辦刊走向開門、開源、開放、開拓、開明辦刊。
今天的《文訊》初步實現(xiàn)了自立且凝練了文化品格,增殖了“象征資本”,樹立了品牌和形象,凝聚了文壇認同,增加了知名度與美譽度;而辦刊的精良又涵養(yǎng)和反哺了品牌的價值。但是,《文訊》要實現(xiàn)由“好看”到“好刊”,從“名刊”到“強刊”的跨越,必須運勢乘勢,踐行大道,堅持走“文訊式”的特色發(fā)展之路,堅持在辦刊實踐中錘煉品格強硬體質(zhì),以文化軟實力奠定做大做強的基礎(chǔ)。文化立刊,大道行之;文化強刊,大勢趨之。資深編輯家、詩人痖弦說:“《文訊》早已擺脫前人的窠臼,以不同的思維、現(xiàn)代傳播的理念創(chuàng)造出文藝雜志的新形象,……儼然成為華文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刊物。”[38]
[1]林建法.序:批評的轉(zhuǎn)型[C]//21世紀中國文學(xué)大系·2007年文學(xué)批評.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8:1.
[2]朱雙一.老中青皆尊,各流派并重[N].臺灣日報,2002-06-03(9).
[3]陳芳明.在捻滅理想之前[N].聯(lián)合報,2003-01-08(12).
[4]封德屏.獨立七周年記[J].文訊,2009(12):1.
[5]辛廣偉.臺灣出版史[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56.
[6]黃蓓伶.探究臺灣雜志的核心優(yōu)勢與未來走向[J].全國新書資訊月刊,2007(9):19.
[7]邵培仁.大眾傳媒通論[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05:112.
[8]南松山.從傳播的角度談文學(xué)的生死[J].聯(lián)合文學(xué),2003(7):90.
[9]陳昌明.困境求生:敬專業(yè)的文學(xué)團隊[J].文訊,2008(7):73.
[10]封德屏.編輯室報告[J]. 文訊,2010(1):1.
[11]陳信元.期待臺灣文學(xué)的新地標[N].聯(lián)合報,2002-05-24(12).
[12]黎湘萍.漢語文學(xué)史中的《文訊》[J].文訊,2008(7):105.
[13]孫起明.編者的話[J].文訊,1983(7):1.
[14]李瑞騰.編輯室報告[J]. 文訊,1985(4):1.
[15]李瑞騰.編輯室報告[J]. 文訊,1989(2):1.
[16]編者.編輯室報告[J].文訊,1997(7):1.
[17]編者.編輯室報告[J].文訊,1989(2):1.
[18]蘇其康.文訊的文化關(guān)懷[J].文訊,2008(7):18.
[19]須文蔚.文化公共領(lǐng)域的建構(gòu)與健全[J].文訊,2008(7):26.
[20]鄭明娳.走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文訊》[J].文訊,2008(7):79.
[21]編者.編輯室報告[J]. 文訊,1997(6):1.
[22]封德屏.編輯室報告[J].文訊,2008(1):1.
[23]封德屏.編輯室報告[J].文訊,2007(7):1.
[24]畢璞.一個老朋友的祝福[J].文訊,2008(7):69.
[25]蘇其康.搶救臺灣文學(xué),搶救文訊[N].聯(lián)合報,2003-01-06(12).
[26]封德屏.編輯室報告[J].文訊,2004(2):1.
[27]高柏園.支持文訊就是支持文學(xué)[J].文訊,2008(7):65.
[28]應(yīng)鳳凰.50年代臺灣文學(xué)論集[C].臺北:春暉出版社,2007:205.
[29]黃秋芳.《明道文藝》的淑世角力[J].文訊,2003(7):93.
[30]汪廣平.伯苓之后又一人[N].語文報,2009-10-31(15).
[31]陸堯:經(jīng)典與時尚[J]. 文訊,2003(7):99.
[32]純文學(xué)雜志走到十字路口?從《萌芽》轉(zhuǎn)制說開去[EB/OL].[2011-01-11].http://www.thmz.com/col23/col60/2011/01/2011-01-11881748_2.html.
[33]李海艦.理論頂天,實踐立地:《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期刊發(fā)展戰(zhàn)略探索[J].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2008(4):67.
[34]李瑞騰.編輯室報告[J].文訊,1985(8):1.
[35]孫起明.回顧所來徑 蒼蒼橫翠微[J].文訊,2008(7):162-163.
[36]向陽.臺灣文學(xué)的鮮活見證[J].全國新書信息月刊,2003(1):4-5.
[37]向陽.一個文學(xué)公共論域的形成[J].文訊,2008(7):4.
[38]痖弦.擁抱我們的《文訊》[J].文訊,2008(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