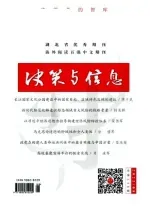朱英國:“湖北省的袁隆平”
文/皮曙初 項俊平
朱英國:“湖北省的袁隆平”
文/皮曙初 項俊平

隆冬季節,在海南省陵水縣的一處稻田里,幾位頭戴草帽、卷著褲管的“農民”正在一株一株地查看秧苗長勢;與別的稻田不同,這里的秧苗被劃分為地板磚大小的一塊塊,每一塊里都插著一個小標牌,寫著不同的系列號。
這不是一片普通的稻田,而是剛剛竣工驗收的武漢大學雜交水稻基地;這些種田人也不是普通的“農民”,他們是中國工程院院士朱英國所帶領的研究團隊——武漢大學的教授、博士、工程師們。
在過去的40多年時間里,朱英國院士在海南的基地里,開拓了馬協型、紅蓮型雜交水稻雄性不育資源新領域,從這里走出的紅蓮型雜交水稻,與袁隆平的野敗型被同時譽為“東方魔稻”,朱英國培育的珞優8號畝產可達800公斤以上……
這一系列研究成果為國家糧食生產作出了杰出貢獻,人們將朱英國院士譽為“農田院士”“湖北省的袁隆平”。
成功培育湖北首個“超級稻”
“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一個世界,一個品種可以造福一個民族。”40多年來,朱英國抱定對“種子效應”的信念,率領他的研究團隊不斷進行水稻育種材料源頭創新,培育和選用雜交水稻新品種。
早在上世紀70年代,他們就成功培育出紅蓮型細胞質雄性不育系紅蓮A,成為我國雜交水稻發展的重要基石之一,這項研究成果于1978年受到全國科學大會獎勵。
上世紀80年代,朱英國在海南陵水的農家稻品種中發現了細胞質雄性不育新類型,培育出馬協型水稻不育系馬協A。這項成果突破了理論界認為的水稻雄性不育資源只能從野生稻中獲得的定論。
近年來,朱英國和同事們利用各種分子標記結合RNA表達分析,成功地克隆了與紅蓮型細胞質雄性不育相關的嵌合基因和育性恢復基因。“基因被成功克隆是理論上的重大突破。”朱英國說,它搞清楚了“不育”與“恢復”之間的關系,為指導紅蓮型雜交稻新不育系、強恢復系選育和強優勢新組合選配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國內屬首創。
為減少雜交稻生產用種的風險,他們研究出紅蓮型雜交稻提純技術,建立了親本提純繁殖體系,使紅蓮不育系大面積繁殖的純度達到99.96%以上,為紅蓮型雜交稻實現產業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雜交稻領域,紅蓮型與袁隆平的野敗型和日本的包臺型,已被國際公認為三大細胞質雄性不育類型。
國內外學者正日益關注晶狀體在青少年屈光發育過程中的重要性,但是目前對于晶狀體屈光參數的觀察性研究存在如下問題。
近10年來,朱院士等人成功地選育出優質的紅蓮型不育系珞紅3A和紅蓮型雜交稻組合紅蓮優6、珞優8號和粵優9號等優質組合,推動了優質雜交稻的發展。其中,珞優8號的最高畝產達876公斤,并且達到國家二級優質米標準,一步跨入“超級稻”行列。
2010年,另一個組合的新品種“兩優234”通過湖北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審定,被專家們認為是首次用分子標記輔助選擇成功選育的抗蟲雜交稻并用于生產。這種抗蟲基因是野生稻的天然抗褐飛虱基因,由栽培稻與野生稻多次雜交后為人類所利用。

朱英國(左二)指導弟子做實驗
“水稻候鳥”向饑饉挑戰
盡管已是71歲高齡,在武漢大學里也早已有了自己的溫室實驗室,但朱英國院士至今仍是一只“水稻候鳥”。2010年冬天,他南下海南四五次,在那里的育種基地做著數十年如一日的實驗。
這樣的“候鳥生活”已經持續了40多年。每年的春夏之交,朱英國和同事們便在湖北育種;秋風乍起,就奔赴廣西南寧;嚴冬將至,再轉戰海南島,直到次年4月,才揣著希望的種子返回湖北。
朱院士說:“水稻是一個喜溫作物,在一定的氣溫條件下才能生長,在湖北我們一年只能種一季,可能10年才能出一個材料,而利用海南島的特殊氣候進行加代,可能三五年就出一個材料,大大節約了科研時間。”
這種候鳥般的生活,讓朱英國幾乎沒有與家人度過一個完整的春節。然而,在這位從大別山里走出來的“農田院士”心里,種子是他最難割舍的情結。
朱英國從小便目睹土地貧瘠、糧食短缺帶給父輩們的悲傷故事。上大學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慘烈的饑饉更讓他刻骨銘心。“讓世界遠離饑饉”成為他至今不渝的志向。大學期間他開始參與雜交水稻試驗,畢業留校后便專注于水稻雄性不育和雜種優勢利用研究。1974年湖北省成立了水稻三系協作組,他被任命為組長,從此開始了“水稻候鳥”生涯。

兩位院士:朱英國(左)和袁隆平(中)在海南基地
功夫不負有心人,“水稻候鳥”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紅蓮型、馬協型雜交稻和兩系雜交稻實現了產業化,得到了大面積推廣。試驗表明,紅蓮型雜交稻在長江流域、四川盆地、華南地區和河南南部均能種植。目前,他們通過審定、認定的雜交水稻新品種達18個,并形成了政產學研的推廣模式,累計推廣面積達8000余萬畝。
經過連續多年在菲律賓、越南、斯里蘭卡、孟加拉國、莫桑比克等國試種,比當地品種增產20%至50%,出口潛力也非常大。
糧食安全以創新為本
2010年12月,朱英國團隊在海南新建的第二個雜交水稻研究基地通過武漢大學驗收。“這將是我們基礎研究的一個新起點。”
在新基地上,他們將推進四大創新:一是種質資源源頭創新,抓品種就是抓源頭;二是技術創新,吸收現代生物技術用于育種實踐,發展分子標記技術;三是理論創新,攻關植物雄性不育和雜種優勢的基礎研究;四是產業體系創新,通過技術轉讓、技術參股等方式推動科研成果產業化。
在朱英國看來,創新是解決我國糧食安全問題的根本出路。“我國水稻播種面積在4.4億畝左右,其中雜交稻占55%,而產量卻占到66%,為我國糧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因此,雜交水稻的發展顯得尤為重要,而雜交水稻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種質創新。”
“我們十幾年來一直堅持品種創新和新品種兼容,就是要不斷適應糧食安全問題帶來的挑戰。”朱院士說,馬協型和紅蓮型雜交水稻開拓了雄性不育資源的新領域,有效地防止了單一細胞質來源可能給我國糧食安全帶來的潛在風險。
他說,我國糧食產量連續多年取得豐收,這是令人高興的成就。但是,根據《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2020年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要達到10800億斤以上的目標,而且我國人口還在不斷增長,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推進,糧食問題依然不容小視。所以,無論糧食產量達到什么程度,基礎研究不能放松,品種創新仍然重要。
朱英國表示,“超級稻”后,種質研究要將“高產、優質、多抗、廣適”結合在一起,建立一個長遠發展機制。“高產”指的是大面積高產,而不是指哪塊田的高產;“優質”指的是碾米品質、食味品質、營養品質、衛生品質、儲藏品質等多方面,“既要好看,又要好吃”;“多抗”是指抗蟲、抗病,一個稻米的品種再好、產量再高,但如果不抗蟲、抗病也無濟于事;“廣適”是指不僅要適應我國的氣候環境,還要適應東南亞、南亞、非洲的環境。
朱英國說:“朝著這個目標,我們的研究工作仍然需要扎扎實實,一心一意,擯棄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