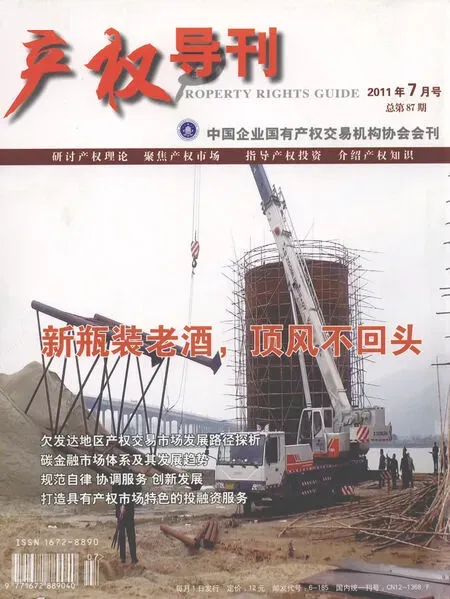新瓶裝老酒 頂風不回頭
■ 王 寧
(安徽電視臺,安徽合肥 230022)
新瓶裝老酒 頂風不回頭
■ 王 寧
(安徽電視臺,安徽合肥 230022)
香河征地事件,因其與京城毗鄰,兼且發生在中央嚴肅土地紀律、嚴格控制房價的政策背景下,成為歷年來違規征地開發的又一個縮影。事實上農村征地、城市拆遷,已成為引發社會矛盾,引起群體性事件的高危問題。而事件中香河政府打著“建設新農村”這一政策的幌子,無非是為圈地開發的“老酒”換一個新瓶罷了。

香河違規征地,一征征出了個全國大討論。中央調查、媒體圍觀、學界聲討,好不熱鬧。似乎早上一睜眼,大伙兒發現了違規圈地的新大陸。事情果真如此嗎?讓我們先回顧一下,這出“圈地四千畝,商業大開發”的戲是如何開鑼的。
事情的曝光源于新華社記者的一次采訪:“記者就當地群眾反映的土地違規流轉問題前去采訪。沒想到這次采訪過程,遭遇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怪事”。事情的經過簡單明了,口糧田“流轉”給了開發商,老百姓“自愿”的四處告狀,當地政府的“社會閑散人員”加班加點的“溝通疏導”。記者的采訪先是被地方宣傳部門“跟蹤”,隨后又被社會人員“跟蹤”,一路跟著的目的,不外乎是針對記者的“威逼”或者“利誘”,以及對群眾的赤裸裸的威脅。觀其操作手法之嫻熟,當非偶然為之。由此延伸,問題發生三年之久,前去調查的媒體恐也非只新華社一家。只是或者“威逼”了,或者“利誘”了,報道盡數胎死腹中罷了。原因為何?一言以蔽之:制度使然。中央媒體乃至中央機構的超然地位,讓其在能夠不被利誘的道德基礎上,理所當然地不被地方黨委政府及其宣傳部門“威逼”。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由上至下的、源于科層制的監督的有效性,與地方媒體無力作為,群眾申訴無門的窘境,源于相同的體制背景和原因。
在這一事件中,媒體——而不是法院,信訪——而不是法律,再次顯示了“特殊國情”下的巨大作用。在缺乏NGO(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非政府組織)的社會環境下,政權背景下的媒體報道以及隨后造成的圍觀效應,為這起2008年以來持續圈地搞商業開發的事件揭開了黑幕的一角。由此想到了李剛、想到了馬家爵、想到了“躲貓貓”、想到了上海大火后的新媒體表現。“媒體作為”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現不知該說是顯示出制度的強大威力,還是說明了黑幕隨處可見?不知是該撫手稱快,還是該扼腕嘆息?
無論是4000畝,還是坊間傳聞的1萬畝,無論是自愿,還是他愿,無論是以租代征還是“土地流轉”,違法征地既非新問題,相關法規亦非要求不嚴密。早在1986年,以租代征已屬違反土地法的行為。可以說,香河征地事件中,不論是“以租代征”的方法,還是“有親戚在政府、醫院、學校上班的,都要回家動員拆遷,否則飯碗端不穩”的手段,都非當地政府的“創新”,更不是此處獨有的“特色”。事實上,類似的描述和報道,歷年來在各類媒體的記錄中屢見不鮮,甚至司空見慣。香河征地事件,因其與京城毗鄰,兼且發生在中央嚴肅土地紀律、嚴格控制房價的政策背景下,成為歷年來違規征地開發的又一個縮影。事實上農村征地、城市拆遷,已成為引發社會矛盾,引起群體性事件的高危問題。而事件中香河政府打著建設新農村這一政策的幌子,無非是為圈地開發的“老酒”換一個新瓶罷了。
然頂風征地何時了,往事知多少?一批批政府官員“前赴后繼”,究竟所為何來?一邊是60~80萬元/畝的土地出讓價格,另一邊則是1150元/畝、每年每畝遞增30元的農民土地流轉補償——這便是香河土地故事的基本梗概。

2007年前的10年,全國土地流轉年均增長14%,2008年土地流轉猛增70%,2009年再增50%。在地方政府與開發企業的合力推動下,目前全國已累計流轉1.7億畝以上的土地,超過全國承包耕地面積的12%。在香河土地故事背后,類似的故事早已在全國大大小小的縣市鄉鎮中上演。
沒有耕地就沒有糧食,這是小學生都知道的常識。土地的肥力不同,產量也不一樣,這是種過莊稼的人都心知肚明的道理。現行的耕地保護政策允許在一地征用耕地后,異地補充使總數不變。然而實際情況是已經開墾成熟的土地多已登記備案,即便因特殊原因(如上世紀為逃避農業稅,一些鄉村曾主動少報耕地畝數)致使部分耕地沒有備案,實際生產的糧食也早已計入流通總量之中。而新增的所謂耕地有不少一直是山地荒坡,產量極低。這就造成了賬面上耕地沒減少,可是實際上糧食的產能降低,最終在供求關系上對農產品價格造成影響。今年以來新一輪農產品價格上漲,上半年的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逐月“高燒不退”。這固然是因為受到自然災害、物流環節成本上漲以及我國農業市場信息嚴重不對等的不利因素影響,上漲主要體現在終端市場,而非產地價格。但土地作為農業基本生產要素的減少,其對農產品供給量以及民眾信心造成的巨大影響,仍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
與此呼應的是,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約達14239億元,一些城市年土地出讓收益占到了財政收入的五六成之多。操作難度低,簡便易行使土地出讓金成了許多地區政府部門增加福利、提高收入的搖錢樹。而在土地收益的分配體制中,農民是喪失權利的弱勢群體,而地方政府成為城鄉二元結構下巨額土地溢價的既得利益者,這便是類似香河土地故事的動機。
到了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成交總價款2.7萬億元,同比增加70%,實際土地出讓面積42.8萬公頃,同比增加105%。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出讓金長期處于“地方財政預算外收入”這樣的曖昧地位。收入巨額且使用自由度強,讓一些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趨之若鶩。在這背后的是2010年全國范圍內商品房出售價格繼續以超過百分之十的比例上漲。政府求利,必然引來企業尋租,地方政府與房產企業的利益鏈就此搭建——這便是眾多類似香河土地故事的根源所在。
提及房地產業,地方政府常常愛做加法:拉動了多少多少上游建材產業,完成了多少多少老城區的改造,新增了多少多少就業崗位。然而對于房產業發展帶來的問題,卻往往選擇性的忘卻:征地帶來的失地農民安置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矛盾和治安隱患;城市拆遷帶來的居民不滿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政府認可度的降低;房價飛漲帶來的人才流動壁壘以及由此帶來的創造活力下降;貧富差距擴大、低收入群體住房困難引發的仇富和沖突……對于以政績促升遷的現行官員績效考察制度,房產開發之利顯而易見。如此說來,一邊政府高調抑價,一邊房價增長不休,這樣一處“雙簧”的發生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實沒有必要把房產企業妖魔化。市場中的任何一個經濟產業,都會以營利為主要目的。放棄利潤而不去賺取,這與市場經濟相悖。社會成員與房企的對立,因媒體的推波助瀾而加劇。但究其根源,實起于政府在保障性住房領域的失位,因為權衡公平與效率是政府功能的重要內容。
住房建設是政府職責的要求,無論是客觀還是主觀上,公民的住房保障責任顯然應由政府擔當。不論是文職機構改革訴求下的行政與政治分離,還是管理主義改革導致的“小政府,大社會”,或者以透明性和責任性為價值構建的服務型政府,基本民生的保障與追求民意支持的訴求都是政府必須正視的問題。在住房體制的大規模市場化改革后,政府如何維系社會公平,進而保證社會穩定,促進有序繁榮,才是平抑房價、保證民生的關鍵。
于是,香河土地故事看似經濟事件,實則政治難題。做什么樣的政府,當什么樣的官,這拷問著每一個官員的政治信仰。如何劃分中央與地方的利益,保證事權與財權的匹配,使得民生保障得以落到實處,則考驗著上層管理者的政治智慧。在這樣一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社會發展差別巨大的國家,無論是城鄉二元結構在土地政策中利益分配的改善,還是單純對于耕地數量與質量安全的監管落實,在一個房地產業構建的經濟利益鏈背后彰顯的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如何落實,是社會公平的訴求,是國計民生的安全證。
尚值得欣慰的是,在事件公布于眾后,主管部門迅速介入,并作出了嚴肅調查絕不姑息的官方表態。至于在土地利益分配體制尚待改革的當下,香河故事是否會因遭受的嚴肅處理,而不再于他處上演?如何割斷地方政府與房產企業間的利益鏈條,同時合理安排地方財政,以實現保障民生的職能,這仍是待解之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