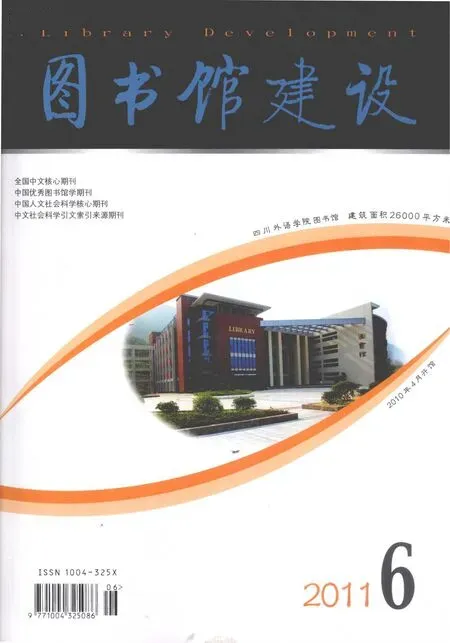中國古代藏書樓是中國近代圖書館的母體──兼議中國古代藏書樓的封閉性與開放性
黃幼菲 (西安鐵路職業技術學院圖書館 陜西 西安 710014)
中國近代圖書館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產物。西方傳教士是西方圖書館觀念的“傳播者”和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的“促進者”;清末民初知識分子是西方圖書館觀念的“踐行者”、中國古代藏書樓的“揚棄者”和中國近代圖書館的“奠基者”。除此而外,有一點必須充分肯定,中國近代圖書館是中國古代藏書樓的發展和繼續,它的母體是中國古代藏書樓,它的根在中國,絕不“是西方思想文化傳入中國的產物”[1]。中國古代藏書樓雖然具有很大的封閉性,“書藏”思想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但它并非絕對封閉,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不能因為它的封閉性,就否定它的開放性。筆者試就上述問題談一些想法,以求教同仁。
1 國內圖書館界關于中國古代藏書樓的爭議
中國有無圖書館的歷史?中國古代藏書樓是圖書館嗎?答案都是肯定的。中國古代藏書樓就是圖書館,只不過它是近代圖書館的初級形式,近代圖書館則是它的高級階段,“二者是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或歷史時期的同一事物”[2]。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原因在于這個極其重要而嚴肅的問題至今仍未徹底解決。如果中國古代藏書樓不是圖書館,中國古代就沒有圖書館;沒有圖書館的歷史,中國近代圖書館就必然“是西方思想文化傳入中國的產物”[1]。在研究主體缺失正確指謂的情況下,所有關于研究中國古代藏書樓是中國近代圖書館母體的努力也就成了無本之末的徒勞之舉。
從古代藏書樓到近代圖書館的演變,是中國圖書館史上一次重大變革。但由于此問題成因復雜,導致眾說紛紜,爭議頗大。目前學術界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近代圖書館與古代藏書樓是兩種不同的事物,近代圖書館是西方思想文化、圖書館觀念和技術傳入中國后的新生產物,是“舶來品”;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近代圖書館與古代藏書樓是同一事物的兩個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近代圖書館是古代藏書樓發展的歷史必然。
1.1 “中國圖書館西來說”
第一種觀點認為,“在研究中國圖書館的歷史時,把古代的藏書和藏書樓當作中國圖書館的源頭或前身,是極不妥當的”[1],因為它們“不僅僅是名稱上的差異,而是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事物”[1]。中國藏書樓的歷史在近代之后就中斷了,藏書樓也消亡了。“中國的圖書館實質上是‘舶來品’”[3],“采取的是‘拿來主義’,摒棄了自己的車,搭乘上西方的車”[3];它“是西方思想文化傳入中國的產物”[1],“我們姑且將之稱為‘中國圖書館西來說’”[1],因為“中國的藏書樓中缺乏演變成為近代圖書館的基本機制,不可能成為新式圖書館產生的母體”[1]。事實上,默認此觀點的人還很多,如“杜定友‘(圖書館)是現代新進事業之一’的表述”[4],在事實上“否認了中國古代有圖書館的存在。流風所及,一直影響到今人對中國古代圖書館的理解。例如,謝灼華主編的全國高校核心教材《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在述及中國古代圖書館時均采用‘藏書樓’術語,而拒絕使用‘圖書館’一詞;臺灣嚴文郁《中國圖書館發展史》一書以‘自清末至抗戰勝利’為副標題,事實上也默認中國在‘清末’之前沒有圖書館”[4]。
1.2 中國古代藏書樓是中國近代圖書館的母體
第二種觀點認為,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我國圖書館(藏書樓)同世界各國圖書館一樣伴隨著文獻的出現而產生,又隨著科學文化的發展而不斷地自我完善、自我更新。“圖書館”一詞是從西方引進的,但因此就認為中國近代圖書館是西方思想文化傳入中國的產物則違背了歷史。事實上,當與農業文明相適應的“第一代圖書館”(藏書樓)因其存在形式和活動內容而不能完成社會交給它的任務時,它就改變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活動內容,質變為“第二代圖書館”(近代圖書館)了。這就是說,“作為第一代圖書館的藏書樓階段是圖書館發展過程中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2],“是中國現代圖書館的母體”[2];同時,近代“圖書館又是藏書樓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必由之路”[2]。
《現代漢語詞典》對“圖書館”一詞的解釋為:“搜集、整理、收藏圖書資料供人閱覽參考的機構”[5]。此處圖書資料應作廣義理解,不能僅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裝訂成冊的紙質圖書資料,還應包括各種形式、材質的文獻資料。中國3 000年前的甲骨文就其本身性質而言就是一種廣義上的圖書資料。因為古代巴比倫的沉重的記事泥板都屬于英國圖書館史研究的對象,那么就不應把“我國古代具有同樣性質且相對泥板輕小易取的占卜記事的甲骨文獻排除在我國圖書館史的研究范圍之外”[6]。甲骨文獻不僅刻有文字,而且可以供人占卜參考之用。因此,我國最早的圖書館,可追溯至夏代(約公元前的巴比倫時代)。據《史記》所載,《道德經》的作者老子曾任周朝藏室史,即藏書之史,故其可稱為我國最早的國家圖書館館長。漢高祖劉邦率軍入關,秦亡漢興,宰相蕭何遍收圖籍,并建石渠、天祿二閣藏之,從此我國便有了專用的國家圖書館[7]。
事實上,中國古代藏書樓萌于殷商,形于兩漢,發于隋唐,盛于宋清。我國古代藏書機構的名稱頗多,稱為“府”、“宮”、“閣”、“觀”、“殿”、“院”、“堂”、“齋”、“樓”等,如西周的“故府”、秦朝的“阿房宮”、漢朝的“天祿閣”、東漢的“東觀”、隋朝的“觀文殿”、宋朝的“崇文院”、明朝的“澹生堂”、清朝的“知不足齋”及“鐵琴銅劍樓”。人們之所以把古代藏書機構統稱為“藏書樓”,“主要是由于古代的藏書機構‘重藏輕用’”[2],但它們已具備圖書館的最基本特征:收藏圖書和利用圖書。用歷史的觀點看問題,這一切都是正常的、必然的,是與當時社會需要相適應的。“今天的圖書館人用當代的標準苛求古人,就像成年的父母嘲笑幼兒的無知一樣”[2]。我們完全可以說,“藏書樓是圖書館的初級形式,圖書館則是藏書樓的高級階段。二者是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或歷史時期的同一事物,既有聯系(共性——收藏圖書和利用圖書)又有區別(個性——藏書樓是‘重藏輕用’,圖書館是‘藏用并重’和‘藏以致用’)”[2]。
2 中國古代藏書樓封閉性的成因
從先秦到清末,“雖然官府藏書與書院藏書在一定范圍內是開放的,但總體而言,中國古代藏書樓是以封建保守、秘不示人為特色的,尤其私家藏書與寺觀藏書更是如此”[8],其豐富的藏書雖然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影響很大,但“書藏”思想一直在古代藏書樓中占據主導地位。藏書樓最主要的功能是修史以治亂、尊經校書以施教化,同時提供國事咨詢和傳承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古代藏書樓不論是官府藏書或私家藏書,都是封建統治階級為收集各種珍本秘籍而設立的“私人書庫”,它的建樓宗旨在“藏”字上,封閉是其主流。那么,中國古代藏書樓的封閉性是如何形成的呢?
2.1 狹隘、自私的小農意識是其思想基礎
古代的中國是農業大國,以低水平的家庭為單位的小農業生產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自給自足的個體農業經濟限制了商業的發展,進而又限制了個體農業經濟形態的轉變。封建社會長期的自給自足小農經濟使廣大民眾滋生了狹隘、自私的小農意識,藏書家也不例外。小農意識的主要特征是自私、自利。民眾終身過著與世隔絕的田園生活,自產自銷,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俗語道:“扇子有風,拿在手中;有人來借,等到秋冬”,即這種意識形態的真實寫照。這些特征決定、影響著中國各項事業的命運,古代藏書樓作為社會和時代的產物,自然無法脫離其特定的社會環境而呈現出強健的開放形態。
藏書人的“自私”主要表現在:秘惜所藏,家業世守。這是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的重要特征。清末的王韜曾經指出:清代嗜古力學之士雖然“雅喜藏書”,但是“皆私藏而非公儲”[9],“若其一邑一里之中,群好學者輸資購書,藏庋公庫,俾遠方異旅皆得入而搜討,此惟歐洲諸國為然,中土向來未之有也”[9]。藏書吾之私有,不借他人乃天經地義。明代范欽就明確表示,“書不借人,書不出閣”[10]364;唐杜暹在藏書題記中也說,“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圣道,鬻及借人為不孝”[11];清代王昶更是認為借書于他人“是非人,犬家類。屏出族,加鞭”[12]。
藏書人的“自利”主要表現在借書不還、損毀污染、據為己有。應該承認,在古代讀書人中確有一些優秀讀者,如宋代杜鼎升“凡借本校勘,有縫拆蠹損之處,必粘背而歸之;或彼此有錯誤之處,則書札改正而歸之”[10]378;明代宋濂借書必“計日以還”,“走送之,不敢稍逾約”[13]。但在古代讀書人、藏書人中也有不少讀者和藏書人思想素質不高,借他人圖書或據為己有、或損毀污染。正如北齊顏之推在《家訓》中所說:“或有狼藉幾案,分散部帙,多為童稚婢妾之所點污,風雨蟲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14]宋代“穎川一士子,九經各有數十部,皆有題記,是為借人書不還者。每炫本多”[15]。這種自私自利的小農意識嚴重限制了藏書的流通和利用,阻礙了藏書樓的開放和發展。
2.2 宗法制度導致的公共意識缺乏是其倫理基礎
所謂宗法制度,是指封建社會王室貴族按血緣關系分配國家權力以便建立世襲統治的一種制度。它由周公創制、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以家庭中的“父子”關系為核心,在宗族內部區分尊卑長幼,其實質就是把家族中的親情血緣關系變為等級權力關系。宗法制度將權力疊加在血緣關系上,即權力的倫理化,使個體的服從不僅出于強制,而且要出于主動認可。孔子以仁釋禮,“對禮加以改造,使禮、儀由外在的規范轉為人心內在的要求,把強制性規定提升為自覺的理念,使倫理規范與心理欲求融為一體”[16],“將其‘自律型慎獨倫理’異化而成為‘他律型的順服倫理’”[17],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包括父子關系、兄弟關系、夫妻關系等)都被君臣化。顯然,在這種普遍的人身隸屬和依附關系的社會,人類把任何東西都看作是私有的,不是自己的,就是別人的,缺少公共認同。梁啟超在分析中國為什么不能“合群”時,就曾認為首先在于“公共觀念之缺乏”[18]。
公共觀念就是公共意識。所謂公共意識,是指獨立自由的個體所具有的一種整體意識或整體觀念。它意味著獨立自由的個體并不把自己作為孤立的個人,而是把自己認同于一個與他者聯系在一起的共同整體,并以共同整體的共同價值規范自己的行為。公共意識意味著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只有具備了公共意識,一個人才有可能把屬于私人的東西拿出來與他人共享,也才能對待他人的東西像對待自己的東西一樣倍加愛護,否則只能是自私自利。費孝通在《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一書中曾說:蘇州在“文人筆墨里是中國的威尼斯,可是我想天下沒有比蘇州城里的水道更臟的了。什么東西都可以向這種出路本來不太暢通的小河溝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廁所。明知人家在這河里洗衣洗菜,卻毫不覺得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為什么呢?這種小河是公家的。”[19]這就是公共意識缺乏的典型表現,因為人們的意識中只有縱的宰制型的關系,沒有橫的權利平等的關系。鄭觀應曾說:“我朝稽古右文,尊賢禮士,車書一統,文軌大同,海內藏書家指不勝屈。然子孫未必能讀,戚友無由借觀,或鼠嚙蠹蝕,厄于水火,則私而不公也。”[20]
試想,在宗法制度導致的公共意識缺乏的倫理基礎上,一個人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藏書與他人共享,或干脆把自己的藏書變為公共的藏書呢?
2.3 古代科技落后、圖書數量少是其現實基礎
圖書數量是藏書樓開放的物質基礎和前提。據統計,漢代劉向編目時,國家藏書才1萬多卷。自此以后,可考萬卷藏書家南北朝12位、唐代22位、宋代50位、明清超過百位。1萬卷是什么概念?“1套《二十四史》3 249卷,1萬卷約等于3套《二十四史》;《太平御覽》1千卷,1萬卷等于10套《太平御覽》 ;1套《四庫全書》79 337卷,1萬卷約等于1套《四庫全書》的八分之一”[12]。可見“1萬卷”并沒有多少圖書。
為什么藏書數量不多呢?原因如下:①文字載體笨重。秦漢時期文字載體以簡牘為主,秦始皇每天要讀120斤重的簡牘資料;漢代東方朔給漢武帝寫的一封信,兩個人才抬得動;司馬遷《史記》130卷,用簡策制作,堆積如山。②圖書制作工藝落后,成書之困難令人匪夷所思。秦漢時期,簡策的制作過程非常繁雜,除了殺青、編簡之外,抄寫時還得一手拿筆,一手拿刀,寫錯了用刀削去。即使在紙張普及之后,抄寫圖書也不容易。“清代蔣衡抄寫80萬字的《十三經》,整整耗費了12個春秋。清修《四庫全書》,先后聘用書工3 826人,用了五六年時間才算抄寫完畢”[12];“宋代成都雕印《太平御覽》,刻工多至150人。清代涇縣翟金生用泥活字印書,制成10萬個泥活字,動員親友36人參與,費時30年,最后弄得傾家蕩產,一貧如洗”[12]。③藏書復本不足,影響傳播。在封建社會,所有典籍、圖書都是靠手刻或抄寫來完成的,不僅費時費力、失誤難免,而且一次只能抄寫1部,生產量極為有限,很難保證每種書都有復本,這在客觀上限制了藏書的傳播范圍。④缺乏鼓勵發展科技的機制。早在宋代中國就發明了活字印刷,但這種圖書制作的先進技術卻遲遲得不到推廣,雕版印刷技術長期徘徊不前,直到清末西方的機械印刷術傳入中國并最終取而代之。盡管我國古代有“四大發明”等偉大創舉,涌現出了眾多杰出的科學技術巨匠,然而科學中心并沒有在我國形成,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外國用火藥制造子彈御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外國用鴉片醫病,中國卻拿它當飯吃。”[21]
2.4 沒有足夠的讀者群是其需求基礎
中國封建專制的統治是建立在對廣大勞動者殘酷侵犯和掠奪的基礎之上的。首先,殘酷的經濟掠奪使廣大勞動者只能為維持基本的生理需求而奮斗,失去了閱讀的基礎和條件。其次,原始的生產手段使勞動者不可能有剩余的經濟積累用于文化、教育這些高層次的精神需求。廣大布衣階層多為文盲,對勞動生產知識的需求不迫切,“知識、經驗的傳播基本限于傳、幫、帶的形式來完成,書籍對勞動階層來說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有的甚至是廢紙一堆”[22]。再次,在中國古代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受教育者絕大多數都是膏粱子弟,圖書成為富人的奢侈品,讀書上學成為富人的專利,但他們讀的也無非是四書五經,閱讀面極窄,圖書的需求量不大。因此,難以形成源源不斷的讀者群。沒有讀者,也就沒有開放;沒有開放,就必然封閉。用現代經濟術語來表述就是:圖書沒有市場,社會需求疲軟。
3 中國古代藏書樓“開放書藏”理念的形成與踐行
我們承認,中國古代藏書樓具有很大的封閉性,“書藏”思想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不論官府藏書、私家藏書抑或書院藏書,皆十分重視收藏和保護,而其對民眾進行開放服務和教育的功能往往被忽略。應該看到,“封閉”與“開放”是相對而言的,那種認為古代藏書樓絕對封閉的觀點是錯誤的。雖然中國古代藏書樓服務范圍狹窄、流通方式落后,但它并非絕對的封閉,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同時對保存文化典籍、維持傳統文化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事實上,建于公元前3世紀古希臘時期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和建立于公元4世紀末的羅馬教皇檔案館等西方宮廷圖書館,當時也不向社會公眾開放,僅供達官貴人使用,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開始從教堂中解放出來,向社會公眾開放。
3.1 “開放書藏”理念的孕育及形成過程
雖然受到古代社會歷史條件的種種制約,藏書的流通與利用受到了很大影響,但仍然有一些有識之士認識到文獻傳播和利用的重要性,主張開放書藏,并在這方面進行力所能及的嘗試與踐行。東漢末年蔡邕奏請靈帝后,將六經文字“書冊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23],“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兩,填塞街陌”[23],“此即著名的‘熹平石經’,這可算是官府藏書在文獻的傳播利用方面的一個早期范例”[23]。宋代館閣藏書已可在一定范圍內公開借閱流通,“讀者有皇帝及近臣、政府要員,還有一些經過許可的讀書人、科舉考生等”[24]。到了明清兩代,隨著私家藏書的興盛,許多藏書家都主張開放書藏。明代藏書家李如一認為:“天下好書,當與天下讀書人共讀之”[25],并把自己的藏書樓命名為“共讀樓”。明代的姚士曾提出“以傳布為藏,真能藏書者矣”[23]的卓見。他們采取了各種當時可行的方式,或供人借閱傳抄;或刊刻印行,廣為傳布;或延請學者,共同研討;或捐獻私藏,補充國藏,等等。這些理念和舉措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古代文化的傳播,雖然在今日看來未免有鄙陋之嫌,但對當時的古人而言已是難能可貴的了。
封建社會末期,一些藏書家逐步認識到舊有書藏模式的種種局限性,為彌補其缺陷出現了創立公藏之說。明末清初的曹溶在其著《流通古書約》中第一次闡述了開放藏書的思想,對那種“以獨得為可矜,以公諸世為失策”[22]的狹隘傳統進行了抨擊,為流通古書創一良法 ;清代乾隆年間的周永年在其撰寫的《儒藏說》中提出了“天下萬世共讀之”[22]的鮮明主張,在其《儒藏條約三則》的第三則就表達了“儒藏對四方讀書之人開放,尤其要面對無力購書的貧寒之士”[22]的先進思想,稱得上是公開利用藏書的首倡。這些都發生在鴉片戰爭之前,標志著在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史上出現了建立公共圖書館的思想,他們的共同宗旨就是打破封閉分隔的私有藏書模式,讓圖書與更多的讀者見面。鴉片戰爭之后,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所帶來的外來因素只不過刺激了中國內在積極因素的增長,大大加快了這一轉化的速度。
3.2 “借閱”是“開放書藏”的重要形式
相互借閱是“開放書藏”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我國最早的借書記載始于漢代劉向,他在整理國家藏書時,曾向中大夫卜圭、臣富參等私人藏書家借書。“晉代范蔚藏書七千余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余人,蔚為辦衣食’。南齊崔慰祖藏書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帙,慰祖親自取與,未常為辭’”[12]。唐代徐修矩藏書甚豐,著名詩人皮日休“假其書數千卷”[26]。宋代藏書家宋敏求藏書頗富,歐陽修、王安石、劉恕等都在他家借過書。“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時,就曾在崇文院設館,借閱龍圖閣、天章閣和三館(即昭文館、集賢館、國史館)、秘閣書籍。沈括、歐陽修等從事科學、史學研究,也曾充分地利用過館閣藏書”[24]。在宋代,女真族建立的金國的平陽已經“出現了一種眾人出資創辦的公共藏書樓——‘贖書樓’。這些借閱方式雖與免費借閱不相同,但它畢竟屬于開放型的”[25]藏書樓。明代藏書家徐火勃建紅雨樓藏書,提出了“傳布為藏”的觀點,極力主張借書,“賢哲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書來,是與書相知也。與書相知者,則亦與吾相知也,何可不借”[27],并為前來紅雨樓觀書者免費供應茶水,熱情接待。到清代,孫衣言的玉海樓、周永年的藉書園、國英的共讀樓、陸心源的守先閣等都陸續向公眾免費開放,徐樹蘭創辦的古越藏書樓更是將這一借閱方式推向新的高度。
3.3 開放式藏書樓是“開放書藏”理念的重要踐行階段
在論證中國古代藏書樓是中國近代圖書館母體這個命題時,決不能忽視維新派倡導的開放式藏書樓。嚴格地說,開放式藏書樓是中國古代藏書樓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是連接中國古代藏書樓和中國近代圖書館的“橋梁”,又是中國古代藏書樓“開放書藏”理念的產物和重要的踐行階段,它在我國古代藏書樓“孕育”近代圖書館的過程中承擔著“陣痛”、“臨盆”的關鍵作用。開放式藏書樓承上啟下,不可替代。
開放式藏書樓的產生源于兩個條件:①受古代藏書樓“開放書藏”理念的影響。“開放書藏”的思想是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精華所在。“明清以來,江浙一帶為中國私家藏書中心,在中國歷代藏書家4 715人中,浙江藏書家1 062人,江蘇藏書家967人”[28]。在江浙常熟派和虞山派藏書家眼中,藏書絕不僅僅是個人和私家行為,“開放者之藏書”是其主要特點之一,“藏書致用、流通古籍的思想占主導地位,他們通過編印家藏書目來傳播藏書信息,或以刻書為己任來廣傳秘籍,或提供借用以共享私藏”[28]。②維新派的積極倡導。戊戌變法前后,維新派知識分子為了解決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對未來前途進行了新的探索,掀起了群眾性思想解放運動,有力地促進了當時封建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變革,也使古代藏書樓這個母體吸允到了豐富的營養,“宮體”得到了優化改造,為開放式藏書樓的發展、近代圖書館的誕生營造了“產床”。
在古代藏書樓“開放書藏”理念的影響和維新派的倡導下,1895年后全國各地陸續設立的眾多學會、學堂、報館、譯書局大都附設了開放式藏書樓。1897年湖南長沙設立的湘學會藏書樓、江蘇設立的蘇學會藏書樓,1898年湖南設立的南學會藏書樓,1900年創立的浙江藏書樓及1905年設立的上海國學保存會藏書樓,這幾所藏書樓都具有一些近代圖書館的特性[29]。“徐樹蘭于1900年集議創辦開放式古越藏書樓,無疑是華夏第一家開放式藏書樓”[28]。在《古越藏書樓章程》中,徐樹蘭闡明了他設藏書樓的宗旨:“一曰存古、一曰開今。”[30]他認為:“不談古籍,無從考政治學術之沿革;不得今籍,無以啟借鑒變通之途徑。”[30]根據這一宗旨,他在所藏歷代經史古籍的基礎上,對“凡已譯、未譯東西書籍一律收藏。各書之外,兼收各種圖畫”[30]。同時,古越藏書樓有專門用來供讀者讀書的閱覽室,設座位60個,有3個專職人員負責為讀者借還圖書,“欲看日報,在架上自由取閱;欲看月報,按借書方法借”[31]。“古越藏書樓在性質上已區別于舊式‘封閉式’的藏書樓,它以其公開閱覽、公共使用為標志,孕育著近代圖書館的因素”[30]。
4 結 語
中國古代藏書樓是華夏文明的一枝奇葩,它雖然具有很大的封閉性,但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具備近現代圖書館“收藏圖書與提供使用,或稱知識信息的收集與傳遞”[32]的基本功能和本質屬性,它是中國近代圖書館孕育、產生和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應該看到,不管是古代的藏書樓、近現代的圖書館,還是以后的數字圖書館,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發展階段,它們都要受當時特定社會條件的制約,“沒有抽象的超然于社會機制之上的圖書館”[33],“階段是個時間概念,不涉及‘有無’問題,‘圖書館’和‘藏書樓’是個名稱概念,這是由中西文化差異性決定的”[22]。因此,中國近代圖書館是中國古代藏書樓的發展和繼續;中國古代藏書樓是中國近代圖書館的母體和源頭,是中國近代圖書館的根。
[2]于無聲“.中國圖書館西來說”質疑[J].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3(2):27-30.
[4]傅榮賢,李滿花,劉 偉,等.中國古代圖書館學為什么沒有被建構為一門成熟的現代學科:中國古代圖書館學學科建設研究之一[J].山東圖書館學刊,2009(1):13-16.
[5]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M].3版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96:1275.
[6]陳海東.中國圖書館歷史探源[J].情報科學,2002(8):875-877.
[7]劉勇華.中國圖書館變遷述略[J].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09(9):167-168,182.
[8]楊桂嬋.清末新政與近代藏書樓[J].河南圖書館學刊,2003(6):84-85,92.
[9]付璇琮,謝灼華.中國古代藏書通史:下冊[M].浙江:寧波出版社,2001:1080.
[10]黃建國,高躍新.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1999.
[11]謝灼華.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M].修訂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104.
[12]曹 之.古代藏書樓封閉之原因芻議[J].圖書館論壇,2003(6):256-257.
[13]錢仲聯.古文經典[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571.
[14]來新夏.漫話古籍的保護與研究[J].文史知識,2009(3):133-137.
[15]周少川.藏書與文化: 古代私家藏書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279.
[16]樊樹志.國史[M].3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60.
[17]林安梧.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之哲學省察:以“血緣性縱貫軸”為核心的理解與詮釋[M].北京:學林出版社,1988:118.
[18]梁啟超.新民說·論合群[G]//梁啟超全集: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93-694.
[19]費孝通. 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差序格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4.
[20]程煥文. 晚清圖書館學術思想史[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53.
[21]魯 迅. 魯迅雜文書信選續編:電的利弊[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72:126.
[22]葉柏松. 再議藏書樓與圖書館[J].圖書館,2003(1):92-94.
[23]趙彥龍. 試論中國古代藏書業的歷史地位[J].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3(2):31-34.
[24]朱麗萍,喬高社.我國古代圖書館藏書的利用發展過程[J].山西大學師范學院學報,1999(1):92-93.
[25]馬艷霞.我國古代私人藏書的致用與開放[J].圖書館建設,2007(3):109-112.
[26]陳 忻.唐宋文化與詩詞論稿[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131.
[27]鄭偉章, 李萬健.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68.
[28]曹培根.藏書開放思想與實踐:古越藏書樓與常熟藏書樓簡論[J].常熟高專學報,2003(3):113-115.
[29]彭一中.我國近代圖書館的產生[J].廣東圖書館學刊,1983(2):25-29.
[30]張樹華“.戊戌變法”與我國開放式藏書樓的產生[J].北京圖書館館刊, 1999(1):112-114,61.
[31]丁宏宣. 徐樹蘭創辦“古越藏書樓”的進步性[J].圖書與情報,1995(4):67-68.
[32]黃宗忠. 圖書館學導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230.
[33]湯樹儉. 圖書館是人類社會文明進程的“扁桃體”[J].新世紀圖書館,2009(5):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