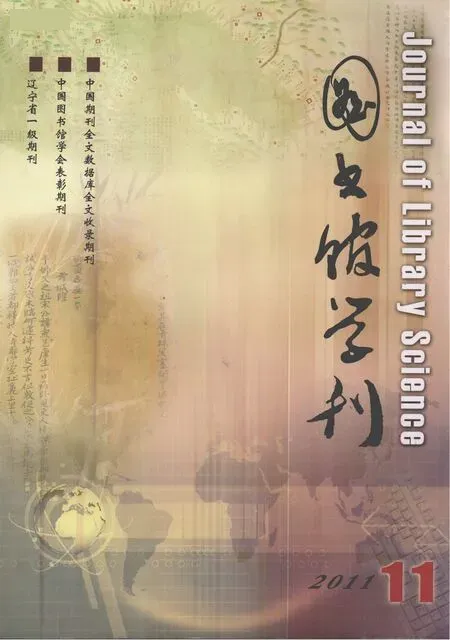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圖書(shū)流通與諸子百家爭(zhēng)鳴*
李杏麗
(河北聯(lián)合大學(xué)圖書(shū)館,河北 唐山 063009)
李杏麗 女,1979年生。碩士,館員。研究方向:信息資源管理。
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是中國(guó)思想文化史上無(wú)可爭(zhēng)議的黃金時(shí)代,先后出現(xiàn)了孔子、老子和墨子這3位偉大的思想家以及他們所創(chuàng)立的學(xué)派,他們的學(xué)說(shuō)奠定了中華思想文化的基礎(chǔ)。到戰(zhàn)國(guó)中期至戰(zhàn)國(guó)末期,更是一個(gè)大發(fā)展、大繁榮的時(shí)期,學(xué)派林立,儒、道、墨三大學(xué)派之外,更有法、名、陰陽(yáng)、農(nóng)、縱橫、小說(shuō)家等學(xué)派相繼出現(xiàn),并迅速達(dá)到發(fā)展的最高峰,各家學(xué)說(shuō)之間爭(zhēng)論激烈,真正形成了百家爭(zhēng)鳴的局面。這一繁榮局面的出現(xiàn),雖和當(dāng)時(shí)政治、經(jīng)濟(jì)發(fā)展息息相關(guān),而與當(dāng)時(shí)圖書(shū)事業(yè)的發(fā)展無(wú)疑也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隨著周王室的衰微,王室藏書(shū)閱讀范圍擴(kuò)大,士階層中私人藏書(shū)增加,各學(xué)派圖書(shū)著述的豐富,使得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圖書(shū)流通速度大大加快。各學(xué)派學(xué)術(shù)思想隨著閱讀的增加而日益深入并活躍起來(lái),思想的活躍又為各派著書(shū)立說(shuō)、論辯與爭(zhēng)鳴提供了雄厚基礎(chǔ)。同時(shí),在論辯與爭(zhēng)鳴中,各學(xué)派又在完成著圖書(shū)的匯聚、利用及散佚的流通過(guò)程。可見(jiàn),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百家爭(zhēng)鳴學(xué)術(shù)局面的出現(xiàn)與當(dāng)時(shí)圖書(shū)的流通現(xiàn)象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筆者試從以下幾個(gè)方面論述、分析。
1 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圖書(shū)之“聚”
私人藏書(shū)、著書(shū)局面的繁榮,為百家爭(zhēng)鳴局面的出現(xiàn)提供物質(zhì)保證。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在士階層中出現(xiàn)私人藏書(shū),這是圖書(shū)流通史上的一個(gè)轉(zhuǎn)折性標(biāo)志。《莊子·天下》中就描述了春秋時(shí)期學(xué)術(shù)文化發(fā)生重大變化的軌跡,指出:天下大亂,“內(nèi)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fā)”。官師之學(xué)已分裂為百家之學(xué),而“其明而在數(shù)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詩(shī)》、《書(shū)》、《禮》、《樂(lè)》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1]也就是說(shuō),官藏之書(shū)已流散到私人手中,人們能夠從中鉆研學(xué)問(wèn),闡明道術(shù)。孔子(前551~前479)就是一個(gè)著名的藏書(shū)家。“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guó)寶書(shū)一。”(《春秋公羊注疏》)可見(jiàn)孔子藏書(shū)之富。正因?yàn)椴貢?shū)多,所以孔子有條件“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進(jìn)行研究考證,從而著書(shū)立說(shuō),聚眾講學(xué)。墨子(前468~前376)也以藏書(shū)豐富而聞名。《墨子·貴義》載:“子墨子南游使衛(wèi),關(guān)中載書(shū)甚多。”[2]孫詒讓注:“蓋古乘車,箱 間以木為闌,中可庋物,謂之扃,亦謂之關(guān),故墨子于關(guān)中載書(shū)矣。”墨子藏書(shū)多,讀書(shū)多,熟悉古代歷史,所以常在宣傳自己政治主張時(shí)引用史事。戰(zhàn)國(guó)時(shí)縱橫家蘇秦(?~前284)游說(shuō)秦國(guó),“負(fù)書(shū)擔(dān)囊”以便隨時(shí)使用,游說(shuō)失敗后的蘇秦回家“陳篋數(shù)十,得太公陰符之謀”,發(fā)憤讀書(shū)終被六國(guó)重用。一個(gè)窮困的說(shuō)客還有數(shù)十篋藏書(shū),可見(jiàn)當(dāng)時(shí)在士階層中私人藏書(shū)已不是希罕事。蘇秦也從多藏書(shū)、多讀書(shū),進(jìn)而著書(shū)立說(shuō),《漢書(shū)·藝文志》中就著錄《蘇子》31篇。
齊國(guó)著名的稷下學(xué)宮便是這一時(shí)期的典型例證。稷下學(xué)宮首先就是私人藏書(shū)的集中地,是聚書(shū)、讀書(shū)的好地方,因而是學(xué)術(shù)研究的中心。在它存在的150余年中,先后延攬?zhí)煜沦t士近千人,其中代表人物有鄒衍、慎到、尹文、荀子等,成為一個(gè)學(xué)者薈萃的文化中心,許多學(xué)術(shù)著作在這里問(wèn)世,已知的有《管子》、《宋子》、《 子》等。學(xué)宮內(nèi)容納道、法、儒、名、農(nóng)、陰陽(yáng)等各家學(xué)說(shuō),共同切磋,自由爭(zhēng)辯,互相詰難,各抒己見(jiàn),為百家爭(zhēng)鳴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和活躍的學(xué)術(shù)空氣,促進(jìn)了學(xué)術(shù)文化的繁榮。稷下學(xué)宮雖僅曇花一現(xiàn),但在中國(guó)文化史上的意義則是永恒的。
可見(jiàn)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由于圖書(shū)的社會(huì)流通量逐步增加,私人藏書(shū)日益普遍,士階層從藏書(shū)、讀書(shū),進(jìn)而著書(shū)立說(shuō),經(jīng)歷了由讀者到作者的演進(jìn)過(guò)程。最終促成了思想解放、學(xué)派林立、自由爭(zhēng)辯的學(xué)術(shù)風(fēng)氣。
2 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圖書(shū)之“散”
王室、官府藏書(shū)閱讀范圍的擴(kuò)大,為百家爭(zhēng)鳴局面的出現(xiàn)提供社會(huì)基礎(chǔ)。西周以前,圖書(shū)屬于國(guó)家秘藏,由史官掌管。史官既是圖書(shū)的編纂者,也是保管者。春秋以后,“天子失官,學(xué)在四夷”,意味著官書(shū)已經(jīng)散入民間并開(kāi)始進(jìn)入流通領(lǐng)域。各諸侯國(guó)也開(kāi)始擁有自己的藏書(shū)所,并設(shè)置掌管圖籍的史官。藏書(shū)體系的突破在先秦圖書(shū)流通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它意味著圖書(shū)傳播范圍的擴(kuò)大。在這以前,由于王室壟斷,書(shū)籍的閱讀范圍受到嚴(yán)格控制,圖書(shū)無(wú)法進(jìn)入社會(huì)流通領(lǐng)域。隨著政治動(dòng)亂和王室圖書(shū)管理的松弛,閱讀范圍逐漸擴(kuò)大,由周王室貴族擴(kuò)大到諸侯貴族,到了春秋末,士階層也已經(jīng)能夠讀到王室圖書(shū)。《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孔子“西觀周室,記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3]孔子是沒(méi)落貴族的后代,他可以看到周室藏書(shū),可見(jiàn)王室藏書(shū)的閱讀范圍已經(jīng)擴(kuò)大到士階層。現(xiàn)存《墨子·明鬼》也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晉之《春秋》、齊之《春秋》”,可見(jiàn)周王室和各諸侯國(guó)的藏書(shū)已經(jīng)允許墨子這樣的一般人士閱讀。進(jìn)入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書(shū)籍更是完全突破了官方的壟斷而流傳入民間。這是古代藏書(shū)史上的一大進(jìn)步,對(duì)百家爭(zhēng)鳴局面的出現(xiàn)有著極大的意義。
書(shū)籍傳入民間,使圖書(shū)獲得日益廣泛的社會(huì)性,不再為極少數(shù)上層貴族所壟斷。士階層成為官府藏書(shū)的讀者群,使得圖書(shū)更能夠發(fā)揮它的社會(huì)功能。廣泛地涉獵書(shū)籍,對(duì)士階層自身文化知識(shí)的豐富、學(xué)術(shù)思想的提高有著重要作用,他們“各著書(shū)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4]在這種背景下,“諸子蜂起,百家爭(zhēng)鳴”,形成了空前的學(xué)術(shù)繁榮局面。
3 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圖書(shū)之“用”
創(chuàng)辦私學(xué)與游說(shuō)諸侯,豐富了百家爭(zhēng)鳴的內(nèi)涵。春秋時(shí)期,王權(quán)衰落,禮制破壞,戰(zhàn)爭(zhēng)頻繁。在這種情況下,官學(xué)遭到極大破壞,形成了“天子失官,學(xué)在四夷”的新局面。貴族官學(xué)的日益衰落,無(wú)法發(fā)揮培養(yǎng)人才的職能,而普通士人要從師受教,學(xué)習(xí)知識(shí),作為入仕的途徑,因此創(chuàng)辦私學(xué)就成為當(dāng)時(shí)教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shì)。孔子就大力提倡辦私學(xué),相傳孔門“弟子三千”,可見(jiàn)在當(dāng)時(shí)就是一所規(guī)模很大、影響深遠(yuǎn)的學(xué)校。私學(xué)的出現(xiàn),不僅是中國(guó)教育史上的重大變革,而且直接關(guān)系到圖書(shū)流通。私學(xué)的分布及其流動(dòng),意味著圖書(shū)已經(jīng)開(kāi)始以學(xué)術(shù)交流和辦學(xué)活動(dòng)的形式進(jìn)行流通,弟子既有沒(méi)落貴族,也有庶人平民,意味著書(shū)籍的傳播對(duì)象已開(kāi)始向社會(huì)上更廣泛的士階層流通。到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更發(fā)展為諸子百家辦私學(xué),如墨子、莊子、孟子、荀子等都廣收門徒,形成不同學(xué)派,由于講學(xué)的需要,從而從事文獻(xiàn)的整理并著書(shū)立說(shuō),對(duì)圖書(shū)流通的促進(jìn)作用就更大了。
另一個(gè)具有廣泛意義的現(xiàn)象是,春秋以后,諸子周游列國(guó),游說(shuō)諸侯,其內(nèi)容除了宣傳自己的理想和策略外,也傳播了圖書(shū)和文化,促進(jìn)了圖書(shū)的流通。
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各諸侯國(guó)為了在兼并戰(zhàn)爭(zhēng)中力圖自存,進(jìn)而爭(zhēng)當(dāng)霸主,紛紛延攬人才,競(jìng)相養(yǎng)士,追求富國(guó)強(qiáng)兵之道。作為士階層的代表,諸子周游列國(guó),游說(shuō)王公,尋找入仕機(jī)會(huì),以便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政治主張。如孔子就曾率領(lǐng)弟子周游列國(guó),尋求出路,先后到過(guò)衛(wèi)、宋、鄭、陳、蔡、楚等國(guó),奔波40年,直到70歲才回到魯國(guó),繼續(xù)從事文化教育活動(dòng)。墨子也曾先后在魯、齊、魏等國(guó)宣傳他的政治主張。他和孔子師徒一樣,流動(dòng)辦學(xué),隨身攜帶藏書(shū),作為游說(shuō)、教學(xué)之用。孟子作為孔門傳人,亦是一邊講學(xué),一邊游說(shuō),先后到過(guò)齊、宋、魯、梁等國(guó),史稱孟子出去游說(shuō)時(shí),“凡車數(shù)十乘,侍從數(shù)百人”。在他的數(shù)十乘車中,當(dāng)然有不少是簡(jiǎn)策,可以說(shuō)他的旅行就是一個(gè)流動(dòng)的藏書(shū)點(diǎn)。這種特有的社會(huì)現(xiàn)象,在先秦圖書(shū)流通史上具有特殊意義。諸子從事游說(shuō)和講學(xué)的行蹤遍布各諸侯國(guó),形成了圖書(shū)流通的網(wǎng)絡(luò),促進(jìn)了圖書(shū)的流通,具有典籍傳播的意義。
綜上,可以看出,隨著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圖書(shū)流通的速度大大加快,各學(xué)派學(xué)術(shù)思想隨著閱讀的增加而日益深入并活躍起來(lái),各主要學(xué)派自身的理論建設(shè)獲得了充分的發(fā)展達(dá)到了鼎盛時(shí)期,出現(xiàn)了大師級(jí)的人物和標(biāo)志性的、集大成的著作。例如儒家涌現(xiàn)出孟子和荀子,法家出現(xiàn)了代表三晉法家的商鞅、韓非和代表齊法家的《管子》,道家則出現(xiàn)了莊周。此外,名家的惠施和公孫龍、陰陽(yáng)家的鄒衍等,都是各學(xué)派發(fā)展的最高峰。
同時(shí),各主要學(xué)派在發(fā)展的過(guò)程中出現(xiàn)了迅速的分化,促進(jìn)了學(xué)術(shù)思想的繁榮。這些分化有的是學(xué)派內(nèi)部在傳承中發(fā)生的自然分化,如《韓非子》所說(shuō)的“儒分為八,墨離為三”,有的則是不同學(xué)派的思想理論在廣泛的交流和爭(zhēng)鳴中互相影響、啟發(fā)、借鑒、汲取而發(fā)生的。即使是師生之間和同門之間也不例外,他們“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shuō),取合諸侯”,[4]百家爭(zhēng)鳴迅速達(dá)到高潮。通過(guò)激烈的爭(zhēng)鳴,各家學(xué)說(shuō)的優(yōu)點(diǎn)得以充分顯現(xiàn),逐漸為大家所首肯,缺點(diǎn)也得以充分暴露,為大家所規(guī)避。于是,百家之學(xué)一方面激烈爭(zhēng)鳴,另一方面又在爭(zhēng)鳴辯駁中互相影響、吸取、滲透、貫通,在很多問(wèn)題的看法上逐步形成了共識(shí),“舍短取長(zhǎng),則可以通萬(wàn)方之略”,成為了各家學(xué)說(shuō)努力的共同方向。
[1]莊子[M].孫通海譯注.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7:374.
[2]墨子[M].司馬哲編著.北京:中國(guó)長(zhǎng)安出版社,2009:279.
[3]司馬遷.史記[M].蘆葦,張贊煦點(diǎn)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113,710.
[4]班固.漢書(shū)[M].趙一生點(diǎn)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595.
[5]論語(yǔ)[M].張燕嬰譯注.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6.
[6]李學(xué)勤.春秋公羊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
[7]來(lái)新夏等.中國(guó)古代圖書(shū)事業(y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8]李瑞良.私人藏書(shū)的出現(xiàn)——早期圖書(shū)流通的直接產(chǎn)物[J].出版科學(xué),1999(1):44-45.
[9]李瑞良.早期圖書(shū)流向何方——先秦圖書(shū)流通的區(qū)域和網(wǎng)點(diǎn)[J].出版科學(xué),1999(2):41-43.
[10]白奚.論先秦黃老之學(xué)對(duì)百家之學(xué)的整合[J].文史哲,2005(5):3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