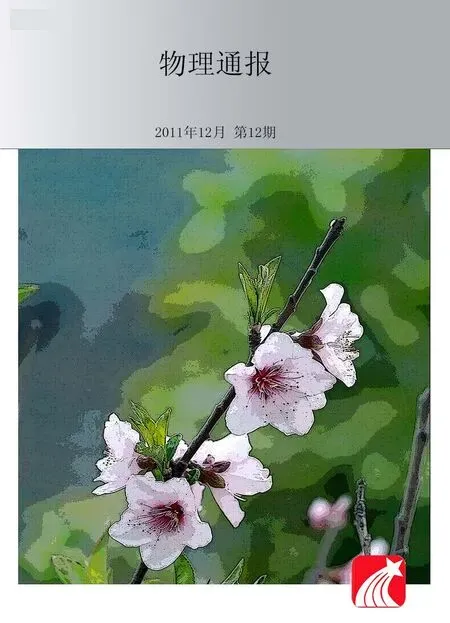矢志照亮全中國
——徐敘瑢院士訪談錄
丁兆君 陳家新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安徽 合肥 230026)
徐敘瑢(1922~ ),山東濟南人.1945年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1946~1951年在北京大學物理系任教.1951年被中國科學院派往蘇聯П·Н·列別捷夫(Лебедев)物理研究所學習、研究,1955年獲得物理數學副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先后在中科院(應用)物理研究所(1955~1965年)、長春物理研究所(1965~1987年)、天津理工大學(1987~1996年)、北京交通大學(1996年至今)等單位工作.
在科學研究中,徐敘瑢院士最突出的貢獻是在發光物理方面.在20世紀50年代赴蘇深造期間,他首次發現了不同能量的導帶電子具有不同的行為特征,開創了過熱電子研究的先河.該研究成果沖破了諾貝爾獎得主莫特(N.F.Mott)的有關論斷.回國后,他倡導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發光學研究室,自此開始了我國發光學領域的研究,研究成果曾得到毛澤東的鼓勵和贊賞.在對電致發光諸多基本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又提出了電致發光器件結構的分層優化方案.此外,徐敘瑢對高激發密度下的光譜變化、能量輸運在納秒及皮秒的時域特點,輸運的反向、瞬態光譜中的激發態弛豫及聲子發射的特征,非線性效應的皮秒特性及來源等方面都有創新性研究.他還十分重視發光學在軍事、農業、醫學等領域的應用,曾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技之星、香港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等多種獎項.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除了在學術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外,作為我國發光學科的創始人之一,徐敘瑢院士為我國發光學科的整體發展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組建了我國的發光學會,并多年擔任理事長.徐敘瑢還在我國發光學界的對外交流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1987年,在他的爭取下,第八屆國際發光學會議在北京召開.特別重要的是,多年來,他培養了我國發光學科的主要骨干,幫助建立了主要研究基地.
1959年,徐敘瑢和黃有莘等人一起在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創建了我國第一個發光學專業,并親自制定了發光學教學計劃,開設發光學專業課,編寫發光學講義.期間所培養的發光學方面的人才大部分已成為我國發光學領域的中堅力量與學術帶頭人.
1 求學聯大——步入物理殿堂
問:徐先生,您好!西南聯大,尤其是物理系,培養出了大批科技人才,您覺得其內在原因是什么?
答:鄒承魯院士在臨去世之前特別寫了一個建議,就是要重新建立一個西南聯大.我覺得西南聯大之所以能培養出大批的人才,是靠它的動力,靠它的環境.這對物理系來講,對別的系來講,都是一樣的.當然,物理系有它的特點,所以它的人才是比較多的.比如做低溫的洪朝生,當時他留美、留英都考上了.他不是物理系的,后來把留英的機會讓給了物理系.所以我認為,聯大之所以能培養出比較多的人才,最主要靠它的動力,動力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當時的政治、歷史環境.
問:您當時為什么選擇物理系?
答:我哥哥是北大數學系畢業的,后來在濟南教書.六中是所有山東學校集合地,他在那是比較受歡迎的.他跟我說學數學太抽象,不如學工、學物理.于是我就學物理了,當時并沒有一個要揭示自然問題(奧秘)的目標,但很感興趣.我在中學里專長是數學,但是我的語文也是很好的,考試都接近或是100分,這兩科都非常好.物理老師是北大畢業的,教得也很好,但沒有多少印象了.
問:近代物理開設了哪些實驗?其他課還做了哪些實驗?
答:只有密立根油滴等四五個實驗.其他的,無線電有個實驗室,我也沒什么印象了.普通物理沒有實驗室.
問:當時為研究生開了很多課,本科生也可選修.您選修了嗎?老師的講課有什么特點?
答:我就選修了量子力學.這也是物理系的一個特點.當時的講課特點:一是沒有教材,講課時就列一個提綱;二是比較接近最新的成就.這些教授剛從國外回來,國際上有什么動態,他們都能夠介紹進來.但只有近代物理有實驗,其余好象沒有什么實驗.再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是學術氣氛濃厚,有不同意見就吵.最突出的是楊振寧、黃昆、張守廉,這三個人在茶館里吵,在路上也吵,走到哪吵到哪.還有我們的上一屆(1944屆),他們住在對面,經常吵,吵的都是科學問題.我覺得這一條非常重要,而現在卻保密,有什么思想生怕別人知道.
問:您覺得聯大物理系的培養目標是什么?
答:也沒有說的很明確.我覺得當時培養的主要是研究人才.我大學畢業那年,同班的幾個,朱光亞、鄧稼先、林書閔,大概五六個人,都考研究生,誰也沒被錄取.
問:您覺得聯大的教育和當前的教育有什么不同?
答:這有很大的差別.現在人說不干就走人.比如美國給一個office,給基金,就到那去.這也就是科協后來提到的科學不端行為.我覺得人最主要的就是誠信.當時在很艱苦的條件下,我們都很努力地學習,還半工半讀.大一的時候,我哥哥把他的毯子等值錢的東西賣了供我上學.可是一年以后,我就掙錢了.當時昆明市聯大學生工讀的比例大概要占百分之九十幾,甚至連大鐘都是聯大人敲的,聯大人在社會上到處都可以找得到.我在念一年級的時候,老師看我做的一些習題,發現我的字體很好,就叫我抄文獻,有法文的、德文的,看見什么就畫什么.一個暑假下來,掙的錢就剛夠吃飯的.因為我在那里沒有社會關系,只能依靠學生會,做教學模型,甚至磨豆腐,哪兒缺人就上哪兒干.這樣,時間就變得非常珍貴了,要保證學習時間,就得早起晚睡.
問:聯大的學習資源怎么樣?
問:看您的英文筆記記得這么好,您當時的老師授課時,是用中文還是英文?
答:都有.周培源用中文,摻雜一些英文.趙忠堯完全用英文,姜立夫也是.教我數學的那位教授用中文.我覺得當時用英文也是不得已,為什么呢?因為中文說起來人們根本聽不懂.比如饒毓泰,江西話,聽不懂.還有教無線電的朱物華,說浙江話,也聽不懂.所以說是不得已才用英文.吳大猷的課我聽過,他出了一套書.饒毓泰是第一個提出來要在大學里做研究的人.
2 繼續深造——確定研究方向
問:后來您是如何到北大任教的?
答:1945年我畢業以后,聯大要北遷,什么人都不要,我就到光學廠工作了一段時間.因為到北京去可以做助教,所以1946年3月份我就去了,真正到北大工作是1946年秋天.
問:您到北大以后做了饒毓泰先生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什么?
答:我跟他做拉曼光譜.美國送了他一個光柵,很大的一個光柵,我前頭有一個研究生沒做好,就沒能畢業.為什么呢?就是因為他的那個顯影液配得不對,后來他就走了.
問:您又是如何到蘇聯留學的呢?
答:這是很偶然的事了,當時是面向全國招考,沈克琦(后來的北大副校長)、我和清華的兩個人,我們都去作主考.考完了以后,科學院一看,他們一個人也沒有,就不干了.于是就提出讓北大、清華給他們派人.北大就派了我和化學系的陶宏(就是陶行知的兒子),清華派了黃祖洽和馮康.
在保證各項安全交底工作的基礎上,項目部還需要加強對安全技術管理,做好相關技術安全措施。并且在此過程當中,項目部需要嚴格執行安全生產管理制度進行開展相關作業。基于河道整治工程的特點,以及其存在的危險點而言,加強對風險較大的分項目工程進行管理,同時制定出專項的安全生產方案。并組織相關人員針對工程的實際情況,對其所制定的方案進行審核,對專項方案進行可行性研究。此外,項目部還需要做好安全管理過程控制,實現動態化管理的目標。
問:為何您到蘇聯之后就師從瓦維洛夫做發光學研究呢?
答:是這樣的:我臨去之前,中科院物理所當時的所長(施汝為)找我談話,說物理所各個方面的研究都有了,就缺發光方面的.所以,我到蘇聯之后就開始做發光學研究.瓦維洛夫當時是蘇聯科學院院長,后來他的一個學生獲得了諾貝爾獎.現在他已經去世了.他的工作作風傳承得非常好,就是要“頂天立地”.
問:您在那兒的學習、研究情況如何?
答:那兒和美國差不多,實行綜合考試:自己準備差不多了,就去參加考試.
問:論文由誰指導呢?
答:室主任給我配了兩個導師,一個物理的、一個化學的,都很好.一個叫安東諾夫·羅曼諾夫斯基;另一個是女的,德國人,叫康斯坦丁諾娃,這兩個人都去世了.
3 兼職科大——培養發光學人才
問:您對1958年科技大學的創辦有什么印象?
答:“全院辦校,所系結合”,當時科學院的計劃就是要各研究所去開課.所以,我們就成立了一個班,我、范希武、許少鴻都去講課.1958年的時候很需要人,后來,我們吸收一部分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專門成立了所謂的“中國科技大學二部”,專門教授發光學的知識,然后就直接到我們研究所,我們叫它二部.科大本部那邊我們不管,是黃有莘管的.我們共有10個人左右,老人員有5個,其余都是1955年后才進來的.我們都是兼職的,而黃有莘當時是系副主任、支部書記,是專職的.
問:科大的發光學方向是怎么確定的?
答:我們幫科大建立的這個方向,別的我們也不會啊.我們要建立就只能建立發光學,1958年建校時就有.那時研究所要幫助科大建立各學科,所里有什么,就建立什么學科.當時施朝淑是助教,就一個人,黃有莘是主角.就在計算所對門上課,我寫的講義都還有.大概有三十幾個學生.開始上課時就4個學生,一個班還不夠,就開設了一門課,一開始就有講義.我們分段上課.我是一開始就講,大概是一二三章,我不大記得了.許少鴻接著講,范希武是1957年去的物理所,后來就派他勞動去了.所以他只能做助教的工作,還不能馬上講課.
問:您能否談一談當時的教學情況嗎?
答:那不很簡單嘛!是我寫的講課大綱,就是按發光學的內容列出一些主要的東西.那時有些實驗是學生到我們實驗室做的.最早考研究生的是張新夷,1965年,他跟我到東北去了,文化大革命后就沒有再上課.那時很馬虎,能畢業的就畢業了.當時大家很努力,所長施汝為說,你到那去兼課吧.我們就去了.發光學方向是根據物理所的研究方向提出的,黃有莘是院里決定派到科大的.我們帶了兩個班的課,第一個班是方容川那班,然后是蔣雪茵那班;蔣現在在上海大學.他當時也考了我的研究生,第二屆的.后來就不知道了,施朝淑比較清楚.后來在發光學領域比較有名的有方容川、樓立人、郭常新,他們幾個人都是頭一屆.后來經過鍛煉,他們及施朝淑都成為科大發光學的主力.
問:您到東北以后,長期任物理所的所長,這一時期科大的發光學方向是不是給你們輸送了一些人才?
答:那當然是了;后來一任的所長就是科大畢業的.
問:我這有一份1977年科學院給吉林省的一個文件,說這一屆科大發光學方向分配一批學生到吉林,要求盡量照顧物理所.這是不是你們當初要的?
答:對,是這樣,就是要科大的學生.后來我們所招收博士生時,對科大的碩士有時就采用免試的辦法,因為科大的學生質量是比較好的.這么多年科大為吉林物理所輸送了大批的發光學方面的人才.現在吉林物理所并到了長春光機所,成為長春光機物理所;留下的主要是凝聚態物理,有一個激發態開放實驗室.而這里的頭兒,主任、副所長,都是科大的.
4 科研歷程——奠中國發光學之基
問:下面我們想請您談一談您的科研歷程.
答:做科研也要繼承革命傳統.那么多人拋頭顱、灑熱血,好不容易創造出現在這么一個條件,在這一代手里把它破壞了,那我堅決反對.
問:您在參加12年科學遠景規劃的制定時有沒有就發光學提出一些建議?
答:有啊!通過陰極射線,就是電視機(顯像)方面,通過這種形式設一個專項,在半導體這個項目里頭.當時我到蘇聯去,他們特別給我做了一臺陰極射線的測試儀,后來產業部門也去要這個東西.蘇聯當時對我們建立發光學的幫助很大;我需要什么儀器,他們很快就做出來了.
問:我們的發光學實驗室建立的過程是怎樣的?
答:那就是先考慮一下要弄些什么設備.有些是我們親手做出來的,像加熱發光的設備,是用木頭做的框架.如何用它來控制加熱都還是個問題,都是通過我們積累經驗,把它的規律找出來了.單色儀從蘇聯買了一個.剛才講的陰極射線儀也是從那兒買的.當時儀器還是比較落后的,幾乎沒有光電的設備,都是用眼睛看.他們曾送我一套校準的標準燈,還有亮度計等,都是他們用過的,焦距都定好了.那時中蘇關系很好的.
問:白手起家將實驗室建起來,除了您之外,還有其他人嗎?
答:還有陳一詢,后來到新疆物理所當所長去了,他是比較早來和我做這套設備的.化學方面就是蘇方中(音),已經去世了.后來又進來幾個人,羅唏、范希武等.
問:您在1961年開始電致發光的研究,1979年轉向能量傳遞的研究,1983年又開始生物發光的研究.這些研究方向的轉變是出于什么明確的目的嗎?
答:沒有.我對導帶電子的電子行為比較感興趣.在20世紀30年代,莫特在《晶體中的電子過程》這本書中,不止一次地斷定,導帶電子不可區分.我的工作就是反對他的觀點,但我并沒有正面提出這個問題,盡管我的結果證明他的結論是不對的.
問:您指出他的錯誤,他有沒有什么反應?
答:我沒有跟他提,在蘇聯的一個會議上講過.1981年,我到英國訪問的時候,英國皇家學會會員黑爾色姆(Hilsum)請我到威爾士去看雷達及信號中心,要乘火車.到了火車上,我看見莫特坐在那里等我.所以我非常欽佩外國的這種做事風格,他不因為你否定他的結果,而對你不滿意.他一直陪我到信號中心做過報告以后才走.這件事說明真正的大科學家,他的胸懷是寬闊的.
問:1987年5月,由您主持的國際發光學會在北京舉行,這有什么背景?
答:在這之前的國際發光學會議上,我就提出來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的一些工作在國外為同行所了解,很受歡迎.那時我們的工作跟國際上是同等水平的.經過“文革”以后,我再出去看一看,有些都看不懂了.他們的方法、提出的問題、所用的設備都是新的.我回來以后,當時的想法就是“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1978年做了所長以后,我就做了三件事:第一就是培養人才,我派出去大概42個人到不同的國家,因為我去參觀訪問過,知道哪里水平高,哪里有比較強的研究人員.第二是更新設備,當時就有很多人反對了.因為我不是給你配一套,給他配一套,而只是給研究所配一套.我堅持在所里成立一個能譜實驗室.盧嘉錫講開放實驗室,頭一個候選人就是我們.第三是調整課題.原來的課題太陳舊了,要更改成新的課題.從1980年開始,很快就有一些新成成果了.所以1983年在科大召開了一個發光學會議,我就提出想辦法召開國際學術會議,他們都同意.1984年這個國際會議在麥迪遜(Madison)召開,當時我才做過開顱手術不到一百天,就出國去爭取了.我覺得有責任把中國的發光學推到國際舞臺上;所以我就去爭取了,就爭取來了.1987年,這個會開完了以后,外國人開始以另外一種眼光看中國.原來還有人認為“這個會在中國開,不是開玩笑嗎?”但開完了之后,他們認為比上一屆在日本開得還高明.自那之后,我們已經開了4次國際會議了.那時國內還沒有召開過比較大型的國際學術會議.
問:上世紀80年代初,您就組織成立了發光學會,并創辦了專業雜志《發光學報》,這是不是標志著發光學的成熟?
答:對!我一直主張大家要互通有無、互相幫助、共同提高.所以1964年我就組織了一次場致發光會,1965年組織了材料發光會.1966年就“文化大革命”了;但在“文革”當中,周總理曾經有過一個指示,要開展基礎研究.當時我就行動了,但后來又是“批林批孔”,又不行了.“四人幫”垮臺以后,我、許少鴻、吳伯僖幾個人在全國走了一遍,宣傳、組織成立發光學會.發光學會現在已經10屆了.這個學會高度團結、互相支持、共同提高.學報之前,在長春物理所就有了《發光與顯示》,原來是情報性質;到《發光學報》就變成學報性質了,有創新性的見解都可以在這兒發表.
問:當時國際上的發光學研究狀況如何?跟他們相比,我們的差距在哪里?
答:國際上,我認為比較分散,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德國,這幾個國家都比較強.我都去參觀過,我派人也都派到最強的那里去.但有的在承擔國家任務,不接納外國人.我們的差距首先就是理論比較差.我后來就希望夏上達能夠在這方面做一些工作.在應用方面我們還可以.到目前為止,和我們同時的幾個七十幾歲,近八十歲的人還承擔著1 500萬支熒光燈的應用研究課題.有的人開創了四五個公司,還有的人通過產業化對于視覺和照明的關系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
問:您說我們的理論差些,是指那時的狀態,還是現在?
答:一直是這樣.在此領域,我國的理論工作者還沒有做出應有的貢獻.
1 北方交通大學,中國發光學會.徐敘瑢科技活動生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2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云南師范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3 (蘇)A·K·委米賴席夫.俄國物理學史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