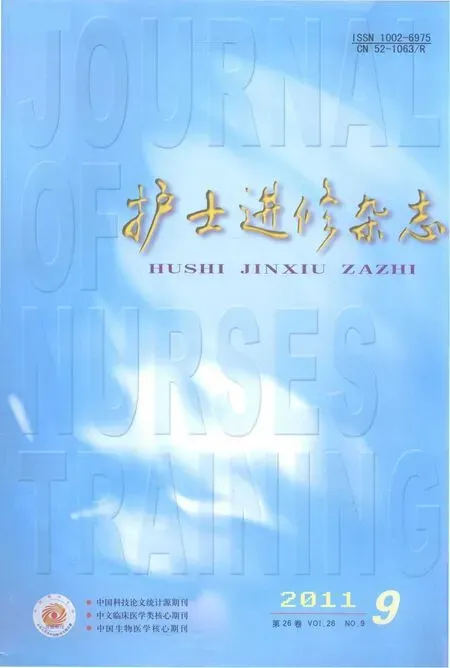三種不同保溫措施對胃癌根治術患者體溫變化影響的研究
李勝云 魏薇 潘蘆翎 張增梅 畢慧萍 陳皓 王韞琦
(鄭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手術室,河南鄭州450052)
體溫是人體重要的生命體征,保持體溫恒定對維持人體正常代謝及各項生理機能的穩定至關重要。正常情況下,機體通過自身體溫調節使產熱及散熱保持動態平衡,從而使核心體溫維持在(37.0± 0.4)℃。手術過程中,由于麻醉藥物、手術操作、周圍環境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容易造成術中體溫下降[1]。研究顯示,體溫下降不僅使患者在手術后易出現寒戰[2]、肢體發涼、發麻等不舒適的感覺[3],造成恢復期的躁動,更重要的是可對機體的循環系統、凝血機制、免疫機制等產生多方面的嚴重危害,導致手術患者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率增高[4]、術中失血量增加[5]、腎臟對藥物的排泄能力下降而使麻醉恢復期延長、傷口感染等并發癥的發生率明顯增高[6],影響患者預后,延長住院時間,增加患者負擔等。所以,國內外醫務工作者采用被動隔絕和主動加溫等措施保持術中、術后體溫恒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0年1月~2010年7月在我院手術室實施胃癌根治手術的患者120例,分別采用薄棉被、充氣加溫系統、綜合保溫三種保溫措施,通過紅外線溫度探測器對外耳道鼓膜的溫度進行監測,觀察并分析三種保溫措施下患者核心體溫的變化。(1)入選標準:患者自愿加入本試驗,并簽訂“知情同意書”;ASA分級(美國麻醉醫師協會體格情況分級)為Ⅰ~Ⅱ級;年齡≥18歲;術日清晨鼓膜溫度介于36.5~37.5℃;手術靜脈通路均建立在上肢血管;采取靜脈吸入復合全身麻醉;(2)排除標準:術中出現大出血、休克、呼吸心跳驟停等;術中變換手術體位的患者;手術時間超過180 min者。
1.2 方法 將符合入組標準的患者隨機分為薄棉被組、充氣式加溫毯組和綜合加溫組(聯合運用充氣式加溫毯及靜脈輸液加溫),每組40例。由于薄棉被組有1例患者術中發現腫瘤位置較高,需要由平臥位改為側臥位,進行胸腹聯合胃癌根治術,且手術時間超過 180 min,所以薄棉被組有效病例為 39例。三組病人的手術間溫度均控制在22~24℃。
1.2.1 薄棉被組 采用常規保溫法,患者進入手術間后即刻為患者覆蓋單層薄棉被,范圍為頸部以下覆蓋到雙足。手術開始后,為了不影響手術范圍,將薄棉被退至雙側髂前上棘連線以下并覆蓋到雙足。
1.2.2 充氣式加溫毯組 采用美國TYCO公司生產的Warm Touch·WT-5900型充氣式加溫系統,患者進入手術間后即刻為患者覆蓋充氣下半身毯(范圍雙側髂前上棘連線以下),將加溫系統調至中檔36~40℃,上身覆蓋單層薄棉被(范圍頸部以下至雙側髂前上棘連線以上)。手術開始后將單層薄棉被去除。
1.2.3 綜合加溫組 除與充氣式加溫毯組應用相同方法以外,還采用奧地利 Biegler公司生產的BW585型干式輸血輸液加溫器對輸注液體進行加溫,將溫度調至37℃。
1.3 監測指標 患者進入手術室后即使用美國TYCO公司生產的GENIUS Model 3 000 A型鼓膜測溫儀監測其鼓膜溫度變化(以鼓膜溫度代表患者的核心體溫),并記錄入室時、麻醉誘導后、手術開始(切皮)時、手術中每30 min、手術結束時的鼓膜溫度。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6.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P<0.05表示差異有顯著意義。計量資料用均數和標準差描述,三組患者一般資料中的計量資料和計數資料分別采用方差分析和卡方檢驗法,以反映組間的可比性。三組患者核心體溫變化趨勢的比較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三組患者同一時間點核心體溫變化的比較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方法檢驗三組間的差異。
2 結果
2.1 三組患者一般資料的比較 本研究119例患者中,男69例,女50例,年齡46~77歲。實施麻醉誘導時的靜脈麻醉藥均為異丙酚,去極化肌松藥均為氯化琥珀膽堿,非去極化肌松藥均為阿曲庫銨,吸入麻醉藥均為異氟醚。三組患者的年齡、性別、身高、手術時間、麻醉時間、入手術室體溫、手術室溫度及輸液量資料(表1)。

表1 三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2.2 三組患者核心體溫變化趨勢(圖1)

圖1 三組患者核心體溫變化趨勢
2.3 三組患者同一時間點核心體溫變化的比較(表2)

表2 三組患者同一時間點核心體溫變化的比較(℃)
3 討論
3.1 薄棉被組患者核心體溫變化趨勢分析 如圖1所示,本研究中薄棉被組患者的核心體溫呈現持續下降趨勢,從進入手術室到麻醉誘導,體溫出現小幅下降;從麻醉誘導至手術開始90 min,體溫下降幅度增大,直至手術結束,體溫下降的幅度趨于平緩。薄棉被是傳統的被動隔絕保溫方式,它通過阻隔皮膚與冷環境的直接接觸,減少體表有效散熱面積,降低經皮膚的輻射和對流作用導致的散熱,從而達到預防體溫下降的目的。患者進入手術室時,為其覆蓋室溫薄棉被,由于周圍環境低于患者體溫,熱量會通過傳導喪失,所以核心體溫出現小幅下降趨勢;麻醉誘導后,麻醉藥引起血管收縮反應被抑制,外周血管擴張,熱量從核心室向外周室重新分布[7],隨著手術的進行,在手術間低溫、體腔暴露及低溫靜脈液體輸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散熱超過產熱,體內熱量快速減少,而薄棉被本身不能產生熱量,所以從麻醉誘導開始,核心體溫下降幅度增大;熱量繼續散失,核心體溫顯著降低時,血管收縮反應被觸發,熱量被限制在核心室,核心體溫也趨于穩定,核心體溫降低速度趨于緩慢,直至手術結束。這與Siew-Fong Ng等[8]的結論一致。因此,使用薄棉被不能預防手術中患者核心體溫的下降,難以起到有效的保溫作用。
3.2 充氣式加溫毯組患者核心體溫變化趨勢分析本研究中,充氣式加溫毯組患者核心體溫在手術開始后有小幅度下降,但均大于36℃,未出現低體溫現象。充氣式加溫毯是以加熱對流空氣為基礎的持續主動暖療系統,通過屏蔽輻射和對流兩種機制加溫,能夠為大面積體表提供有效的熱傳遞。保溫毯可形成一個溫暖氣囊,使溫暖氣流直接接觸患者體表,在患者肌膚間形成特有的暖流層,主動維持和升高體溫。本研究選擇胃癌根治術患者,由于手術切口長、消毒范圍大,為了不影響術中的無菌操作,充氣式加溫毯選用下半身毯,其覆蓋范圍在雙側髂前上棘連線以下,這就使主動保溫范圍限制在雙下肢及會陰部,只占體表面積的47%,患者雙上肢未進行保溫,再加上室溫液體從上肢靜脈輸入,所以手術開始后出現核心體溫小幅度下降趨勢。但隨著手術時間的推移,充氣保溫毯發揮主動升溫作用,由于充氣毯的溫度始終高于體表溫度,使患者始終處于溫暖環境中,可以通過反向的輻射、傳導、對流,使熱量從加溫毯向與之接觸的皮膚方向流動,從而有效地阻止了機體總熱量的丟失,故在手術開始90 min以后體溫達到平衡且維持在36.2℃左右。這與De Bernardis RC[9]的研究結果一致。
3.3 綜合加溫組患者核心體溫變化趨勢分析 本組中在應用充氣式加溫毯的基礎上,增加了輸液加溫器。據報道[10],成人靜脈輸入1L與環境溫度相同的液體,核心體溫下降約0.25℃,通過輸液加溫器可使這種情況得到改善。如圖1所示,在切皮后本組患者核心體溫出現小幅度下降,分析其原因是由于低溫消毒劑的使用及腹腔暴露所致。但通過充氣式加溫毯和輸液加溫器的共同作用,加熱至37℃的溫液體從未保暖的上肢輸入體內,手術開始60 min后,患者的核心體溫就達到平衡,在整個手術過程中,核心體溫均維持在36.4℃以上。雖然在三組中綜合加溫組保溫效果最佳,但是這種方法也有缺陷,例如,在時間較短的手術中其與充氣式保溫毯效果相同,況且同時使用兩種加溫設備,會增加護士工作量,加大醫療資源的消耗等。
3.4 三組之間保溫效果的比較 如表2所示,通過重復測量方差分析,F=33.566,P=0.000<0.05,三組患者核心體溫變化趨勢的差異有顯著性意義。同一時間點三組間患者核心體溫的比較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方法檢驗,結果顯示,薄棉被組與充氣式加溫毯組、薄棉被組與復合保溫組在切皮時P值分別為0.016<0.05、0.002<0.05,差異均有顯著性意義;手術開始30 min及以后各點,薄棉被組與充氣加溫毯組、薄棉被組與綜合保溫組組間比較的P值均<0.05,差異有顯著性意義。這說明薄棉被的保溫效果不如其他兩組。提示我們在今后的護理工作中,不能將薄棉被作為保溫措施來預防患者圍手術期低體溫的發生。充氣加溫毯組與綜合保溫組之間,從手術開始60 min開始以后各時間點的P值均<0.05,差異有顯著性意義。說明在本研究中,在手術時間超過60 min時,聯合應用輸液加溫器和充氣加溫毯的保溫效果要好于單獨使用充氣加溫毯。本實驗所使用的充氣加溫設備溫度均設置在中檔(36~40℃),實驗過程中無一例患者發生低溫燙傷,安全性可靠。
綜上所述,薄棉被保溫效果較差;充氣式保溫毯雖然也能夠相對有效的保護患者圍手術期體溫,但不能有效地維持圍手術期體溫的穩定;綜合加溫方法可以很好的保持患者體溫平穩,可有效避免圍手術期低體溫的出現,同時在小于60 min的手術中和充氣式保溫毯保溫效果相同,提示在手術時間短的手術中,單獨應用充氣式保溫毯既能即刻達到有效的保溫措施,又可以減少護士的工作量,避免醫療資源的消耗。
[1] Seeler DI.Complications and treatment of mild hypothermia [J].Anesthesiology,2001,95(2):531-543.
[2] 林衛紅,張麗清,錢黃靜,等.加溫二氧化碳建立氣腹對腹腔鏡手術患者體溫及寒戰發生的影響[J].中華護理雜志,2007,42 (10):953-954.
[3] Weirich T L.Hypothermia/warming protocols:Why are they not widely used in the OR?[J]AORN J,2008,87(2):333-344.
[4] Good KK,Verble JA,Secrest J,Norwood BR.Postoperative hypothermia-the chilling consequences[J].AO RN J,2006,83 (5):1054-1066.
[5] Rajagopalan S,M ascha E,Na J,et al.T he effects of mild perioperative hypothermia on blood loss and transfusion requirement[J].Anesthesiology,2008,108(1):71-77.
[6] Fry DE,Fry RV.Surgical site infection:the host factor[J]. AORN J,2007,86(5):801-810.
[7] 趙俊.新編麻醉學[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2:155-179.
[8] Siew-Fong Ng,Cheng-Sim Oo,Khiam-Hong Loh.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Warming Interventions to Determine the Most Effective in Maintaining Perioperative Normothermia [J].Anesth Analg 2003,96:171-176.
[9] De Bernardis RC,da Silva M P,Gozzani JL,et al.Use of forcedair to prevent intraoperative hypothermia[J].Rev Assoc Med Bras.Jul-Aug,2009,55(4):421-426.
[10] Bruer A,Perl T,Quintel M.Perioperative thermal management[J].Anaesthesist,2006,55(12):1321-1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