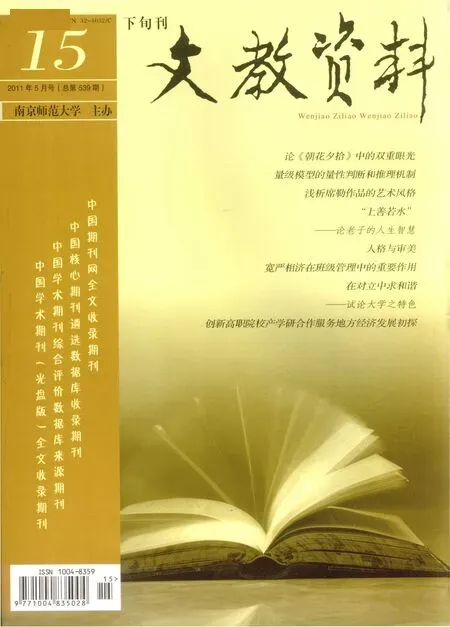從作者角度看中國古典悲劇大團圓結局
周佐霖
(河池學院,廣西 宜州 546300)
大團圓結局是中國古典悲劇最為鮮明的民族特色之一,正因如此,于是產生了中國古代有無悲劇之爭,有人認為中國古典悲劇劇情發展均以大團圓告終,給人一個“光明的結尾”,并以西方文藝理論體系為參照,認為中國缺乏悲劇意識,從而認定中國古典戲劇沒有悲劇。筆者從不反對拿來主義,也承認西方戲劇理論自有其科學性與普遍性,但以西方的戲劇理論為標準來規范中華民族的戲劇創作,這一做法是不科學的,因為各個民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所創作的悲劇都有其特殊性,用西方的戲劇理論來套中國的戲劇,認為中國古典戲劇沒有達到“悲劇是人底偉大的痛苦,或者是偉大人物的滅亡”[1]的效果,就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悲劇創作,這種忽略文學創作民族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1983年5月邵曾祺在《試談古典戲曲中的悲劇》一文中指出,一部戲曲是否是悲劇,要看整個劇本是否具有悲劇的性質與氣氛,而不是決定于它是否有“大團圓”的結尾。筆者認同這個觀點。那么,為什么中國的古典悲劇大多均以大團圓作為結尾呢?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近幾年人們往往從社會心理這一角度進行研究分析,因為“任何一個民族的藝術都是由它的心理所決定的”,[2]而中國的社會心理是一種樂天精神,王國維先生說:“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劇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亨。非是而欲厭閱者之心,難矣!”[3]認為這僅僅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本文嘗試從戲劇家的創作指導思想、創作心理、創作環境等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從作者角度來解讀中國古典戲劇頻頻以大團圓為結局的原因,并以此求教方家。
一、作家創作指導思想對大團圓結局的影響
文學創作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反映作家的創作指導思想,或者說作家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都在指導作家的創作實踐。中國古代優秀戲劇家的創作指導思想自然是以中國優秀的文化思想為主,中國古代優秀文化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對歷代文人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中國古代戲劇家們也自然地接受這些優秀的文化思想,在具體的戲劇創作中自覺地承擔起傳承這些優秀文化思想的責任,以這些優秀的文化思想作為創作指導思想,尤其是在安排戲劇的結局加以體現,因為結局在戲劇中的作用十分明顯,它往往直接表現了戲劇家對事情的看法。那么,戲劇性家們具體的創作指導思想又是什么呢?我認為,戲劇性家們具體的創作指導思想主要是以下三種思想意識。
1.強烈的“中和”思想意識。儒家思想是中國古代優秀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思想對歷代文人的影響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有的甚至浸入骨髓。儒家的“中和”思想意識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備受歷代文人接受與推崇。“中和”的意思是人事物要和諧、適中、均衡有序,不能極端。《中庸》記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顯然,儒家認為人和萬物相處的最佳狀態就是“中和”的狀態,只要實行“中和”之道,萬物就能達到和諧的境界,世界就會平衡有序。由此可見,儒學就是一種追求主張穩定和諧的學說。因此,歷代統治者都十分尊崇儒家思想,把它奉為統治階級思想。對于以孜孜追求功名為己任的文人而言,他們自然信奉統治階級的思想,自然也成為“中和”思想的信仰者,戲劇家們自然也毫不例外。這是十分關鍵和重要的,因為“中和”的思想意識一旦指導戲劇家們的創作實踐,他們在安排情節時就必定注重情節的均衡有序,使悲劇情節與喜劇情節交替出現,既不能一味地悲,又不能一味地喜,要以喜劇的氣氛來沖淡悲劇的氣氛,要化解觀眾的悲愁之感,要達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目的。總之,由于“中和”的思想意識的作用,戲劇家們在考慮安排結局時就不能一味地宣泄悲愁,要給人看到一線光明,這樣就自然而然地把大團圓作為結尾了。王季思先生說:“如果說西方戲劇將悲劇的崇高和喜劇的滑稽加以提純而發展到極致。……中國戲曲則將兩者綜合在一起,相互調劑、襯托……表現為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中庸調節。達到明辨是非,懲惡揚善后的超越。”[4]這樣,中國古典悲劇在結構上就往往表現為“喜—悲—喜—悲—大悲—小喜”模式,而不像西方“喜—悲—大悲”的結構模式,戲劇家們通常都用小喜的氣氛沖淡大悲的氣氛,從而進入一種和諧安適的心理狀態,獲得創作的滿足感,滿足內心的“中和”思想需求,這樣中國古典悲劇以大團圓作為結尾就不足為奇了。另一方面,大團圓結尾也是戲劇家們維護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的需要,因為大團圓結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現實社會中的尖銳矛盾。戲劇是一門舞臺藝術,大團圓結尾同樣給觀眾(普通老百姓)一種愉悅的感覺,存在一種美好的幻想,得到一種心理平衡,有利于維護社會的平穩。可見,“中和”的思想意識決定了戲劇家們以大團圓作為戲劇的結尾,既是表明他們人生觀與價值觀的需要,又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
2.鮮明的善惡有報思想意識。中國人向來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意識,認為上天只保佑有德之人,對于造惡作孽之徒則施以惡報,認為善惡報應應該各得其所,十分注重“天理”的應驗,一旦覺得“天理”不公就要責天問地,竇娥含冤時就拷問天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可見懲惡揚善、善惡有報的思想是十分鮮明的,也是深入人心的。另外,東漢末年,佛教思想逐漸傳入中國,其因果報應輪回的觀念也頗為流行,佛教與中國固有的報應思想意識相互融合,人們的善惡有報的思想意識就更加根深蒂固了。作為中華民族的普通一員,戲劇家們本身也具備有這樣的思想意識,所以他們在創作的過程中,就自然地把這種思想意識灌注于戲劇之中,使戲劇起到勸善懲惡的作用。高明《琵琶記》的“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就是最好的說明。魯迅先生曾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古典戲曲小說的兩大特點:一是賣弄學問,二是懲惡勸善。戲劇家們知道,只有是非分明、善惡昭彰的戲劇作品才能迎合觀眾的欣賞需求,如果戲劇的結尾不是好人得好報、惡人得惡報,那么傳統的思想道德觀念將面臨信仰危機,就會引起觀眾的強烈不滿,戲劇作品將遭受唾棄,戲劇家們是不會這樣做的。為了滿足民眾的信仰需要,宣揚傳統的倫理思想,戲劇家們往往會安排一個光明的結尾,大團圓的結局就順應而生了。
3.強烈的尚圓傳統思想。
中國古代的尚圓傳統思想是中華民族集體無意識經過長期積淀而成的。它對古代戲劇的劇情安排同樣產生巨大的的影響。在上古初民的潛意識里,人們對上天充滿了敬畏。孔子說:“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易經》記載:“乾為天,為圓。”“這種對天的崇拜就引起了對天的運行規律——‘圓’的親和與崇尚”。[5]人們認為圓象征著美滿、完美,沒有缺陷。再者,人們對日月之圓同樣無尚崇拜,這些思想意識經過長期發展最終就形成了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的宇宙觀。同時,圓是曲線的,象征著柔和、和諧、平衡,‘圓’與‘和’是相通的,于是尚圓的思想意識就逐漸形成。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努力追求一個圓滿的結局,這是我們民族共同的心理趨勢,也就是所謂的凡事要善始善終。因此,戲劇家們在安排情節的最終結局的時候就會安排一個圓滿的結局,即使現實并非如此也罷,這既符合傳統的尚圓思想,又是戲劇家對觀眾的一個圓滿交待。“中國古典悲劇的情節結構……苦樂相錯,悲喜交融,順境逆境相互對轉,遞成圓形,這也構成了中國古典悲劇的情感結構以及情節結構最為顯著的特征”。[6]以大團圓作為結尾,是戲劇家的創作需要,也是廣大民眾的心理需要。
二、作家創作心理對大團圓結局的影響
弗洛伊德認為:“文藝本質上是被壓抑的性本能沖動的一種升華。……文藝的功能就是一種補償作用,作家和讀者在現實生活中難以實現的愿望可以通過創作或欣賞文藝作品得到變相的滿足。”[7]所以,當作家的現實愿望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就有借助文學藝術創作來補償的心理傾向。中國歷代文人都有立德、立功、立言的強烈愿望,尤其是立功(博取功名)的愿望更為強烈。作為一種文化傳統,通過科舉考試獲取功名是文人安身立命的正途,是下層文人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途徑。然而元代的戲劇家們卻生不逢時,命運多舛,較之前之后的文人而言,他們的生活狀況是最為困頓郁悶的。因為蒙古族建立政權、統一中國之后,在中原地區曾廢除科舉制度長達八十年之久(1234—1315年),在南方廢除科舉制度也近四十年之久(1279—1315年),即使偶爾開科,所錄用的名額也極其有限,這樣,許多下層文人以科舉求仕的理想被無情的現實擊得粉碎,“金榜題名”已是無法實現的夢想。王驥德的《曲律》記載:“中州人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多以有用之才,寓于歌聲,以紓其怫郁感慨之懷。”戲劇成了文人們的精神家園,為了生活,戲劇也成了他們的謀生手段,戲劇家們大多數成了書會才人。現實理想成了鏡花水月,他們也就只能在戲劇創作中寄托自己的理想追求,在感到悲苦萬分之時,安排一個大團圓的結局,以期得到心理補償,使內心得到一些平衡。李漁在《笠翁偶寄·卷二》中的“賓白”記載:“予生憂患之中……總無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詞之頃,非但郁藉以舒,慍為之解,偕作兩間最樂之人,……未有真境之所為,能出幻境之上者。我欲做官,則頃刻之間便臻富貴,……我欲娶絕代佳人,即做王嬙、西施之原配。”李漁的這段記述真實地刻畫了文人們的幻想補償心理。以大團圓結尾的戲劇最能體現戲劇家們的這種幻想補償心理。再者,有很多的戲劇家與下層藝人也有廣泛接觸,如關漢卿與朱簾秀等。地位卑微的民間藝人與喪失進身之階的落魄文人可謂是 “同是天涯淪落人”,這些民間藝人的悲歡離合同樣時時在感染著戲劇家們,他們對藝人們的人生遭遇深表同情,所以大團圓的結局對戲劇家們起到自我安慰作用的同時,也表達了他們對藝人們的美好祝愿,在心理上補償了藝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缺陷。總之,作家在創作的時候,他們有安排作品中人物命運的主動權,并借助作品中的人物來寄托自己的某些愿望,渲泄內心的郁結之情,給作品中的人物安排一個美好的結局,借此消除胸中塊壘,滿足自己的心理補償需求,因此大團圓結局的出現順應了戲劇家們的心理需求,這是可以理解的。
三、作家的創作環境對大團圓結局的影響
戲劇家們大多數都是社會地位較為低下的書會文人。作為文人,他們大多數都是經過儒家思想的薰染,盡管他們也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抨擊了封建禮教的不合理性,但是他們的思想認識高度是無法超越時代局限的,他們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他們無法從根本上說明戲劇中產生悲劇的原因,即使劇情發展到結局,他們也無法解決悲劇沖突,只能把解決悲劇沖突寄希望于明君、清官、英雄、神怪力量等偶然的因素上,于是就只能安排大團圓結局,這是戲劇家所處的時代環境限制的結果。另一方面,中國歷代統治階級都十分重視文學作品的教化作用,為了達到教化的目的,統治者除了政治統治之外,也特別重視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與監視,通過禁止或提倡某類戲劇的措施,使戲劇符合統治者的統治教化要求。如《元史·刑法志》就有“諸妄撰詞典,誣人以犯上惡言者處死。”“諸亂制詞曲為譏議者,流。”等對戲劇的限制條例的記載,統治者對戲劇作出了種種嚴格的限制,他們提倡“義節夫婦,孝子孝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之戲,禁止“譏議”之戲,面對如此苛刻的律令,戲劇家們在創作時就不得不考慮再三,謹慎從事,如果反映現實的不平、揭露黑暗的尺度把握不好,就可能身處險境,引來牢獄之災,甚至殺身之禍。再者,戲劇的結尾都必須交代人物的最終命運結果,否則劇情就不完整,而如果以悲情作結,一味地渲染悲情,就會很容易引發人們心中的不平之氣,因為“人之性,必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則憤,憤則怒,怒而思動,動則手腳不凈”。[8]“手腳不凈”就意味著情緒失控,就容易引起越軌之舉,這是統治者絕對不充許出現的,所以皆大歡喜、團圓和樂的結局就成了戲劇家解決悲劇沖突的首選了,這是戲劇家所處的政治環境使然。
總而言之,大團圓結尾并沒有改變悲劇的本質傾向,這個“光明的結尾”也“不影響全劇的悲劇性質和悲劇氣氛”(王季思,《中國古典十大悲劇集》),它是中國古典悲劇最重要的民族特征之一,如果以此而認為削弱了悲劇的效果,并貶之為“瞞和騙”的文學,這是沒有以正確的態度來分析中國古典悲劇的民族特征,是不妥的。當然,大團圓結尾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各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必然產物,而作家的創作指導思想、創作心理和創作環境僅僅是諸多決定因素之一。
[1][俄]車爾尼雪夫斯基.論崇高與滑稽[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85.
[2][俄]普列漢諾夫.美學論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王國維.紅樓夢評論[M].長沙:岳麓書社,1999.
[4]王季思.悲喜相乘[J].戲曲藝術,1990,(1).
[5][6]危磊.中國藝術的尚圓精神[J].文藝理論研究,2003,(5).
[7]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8]張雙棣.淮南子校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