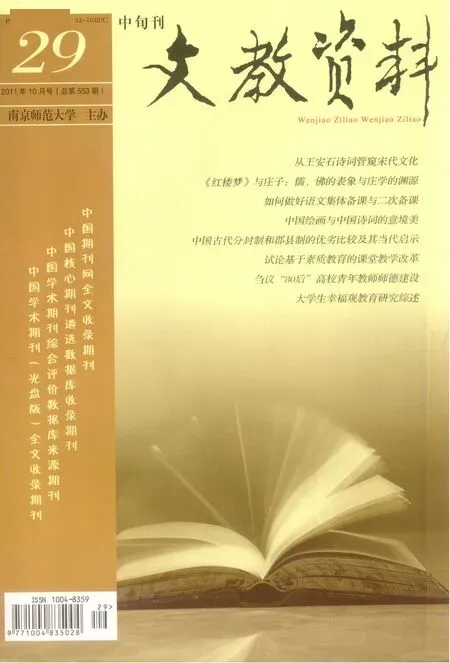劉克莊詩學中的宗教思想
李茜茹
(遼寧師范大學 文學院,遼寧 大連 116030)
理學作為宋代占主體地位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潮,必然與宋代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有著密切的關聯。理學的繁榮興盛對同時代的詩人必然產生一定的吸引力,與此同時,理學家探討道德義理的“性理學說”對詩人的詩歌創作觀念也發生著影響。同時,宋太祖建國后,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修廢寺、修禁毀佛像;而真宗、徽宗崇道,三教的繁榮發展,有利于宋代文化的發展。
劉克莊生于這樣大的時代背景,其祖父劉夙、叔祖劉朔都深通理學,是“隆(興)、乾(道)第一流人物”,其父劉彌正也是好學不倦的人物,可謂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同時劉克莊得到葉適和真德秀等大儒的提攜。在對詩歌本質的認識上,劉克莊繼承儒家的詩教,標舉“六義”,強調詩當切于世教,發揮其社會教育作用。《序王子文詩》曰:“古詩皆切于世教。……合于詩人之所謂六義者。”舉凡忠君愛國、父慈子孝、孝悌仁義之類的道德情感,他都稱為“性情”,詩歌表達了這種性情,也就符合了六義。《跋方俊甫小稿》曰:“余觀古詩以六義為主,而不肯于片言只字求工。季世反是,雖退之高才,不過欲去陳言以夸末俗,后人因之,雖守詩家之句律嚴,然去風人之情性遠矣。”他所標舉詩的六義、性情,也就是對詩的本質、價值的確認,同時也是對偏重格律形式或書本學問等非本質因素的批判。再如《跋何謙詩》:“自四靈后,天下皆詩人,詩若果易矣,然詩人多而佳句少,又若甚難,何欽?余嘗謂:以情性禮義為本,以鳥獸草木為料,風人之詩也;以書為本,以事為料,文人之詩也。世有幽人羈士,饑餓而鳴,語出妙一世;亦有碩師鴻儒,宗主斯文,而于詩無分者,信此事之不可勉強欽!……夫自國風、騷、選、玉臺、胡部至于唐宋,其變多矣,然變者詩之體制也,歷千年百世而不變者,人之情性也。”劉克莊所標舉的“性情”更多地偏重于那種憂國憂民的政治道德情操,如他推崇杜甫、元結為民請命,盛贊陸游、楊萬里忠義報國,都可見他的價值取向。正是這種思想情操使詩有了有益世教的意義:“觀其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疏直之氣;傷時聞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委婉之義;感知懷友之行,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恥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敖慢襲押、閨情春思之類,無一字一句及之。”詩歌的教育作用是通過它所表現的道德人格境界來實現的,而這種精神人格往往在逆境困頓中更能得到磨礪激發,從而閃現出它的光華。為此,劉克莊更著意于艱難坎坷的人生境遇對詩歌創作的激勵作用。《跋章仲山詩》云:“詩非達官顯人所能為,縱使為之,不過能道富貴人語。世以王岐公詩為至寶丹,晏元獻不免有‘腰金’、‘枕玉’之句,繩以詩家之法,謂之俗可也。故詩必天地崎人、山林退士,然后有標致;必空乏拂亂,必流離顛沛,然后有感觸;又必與其類鍛煉追璞,然后工。”文學史上的創作實際也證實了這一規律,《序王子文詩》云:“謂窮乃工詩,自唐始,而李、杜為尤窮而最工者。”《唐博士祠》云:“今觀名世作,多在滴官時。太史玩湘筆,儀曹永柳詩。”艱難困頓所激發出的往往是那種慷慨抑塞的忠憤怨徘之情,所以好詩往往是這類抒憤寫憂之作,所謂“伯倫酒頌老義詩,腹憤胸奇略泄之”,“自古放臣多感慨,吾評《哀鄒》勝悲秋”。劉克莊上述的詩學觀雖然只是“發憤著書”、“詩窮后工”之類觀念的翻版,但他在南宋那樣一個偏安一隅、內外交困的時代背景下重申這樣的觀點,實有針砭時弊、發揚詩歌的社會政治功能的意義。他本人在仕宦中經歷過較大的挫折,但仍舊懷著強烈的報國之志、憂患意識,在詩中表達救亡圖存的恢復之意,揭露統治者的茍且偷安、將帥的腐敗無能,對普通士兵、民眾的苦難傾注深切的同情,這一切都印證了他的詩學觀,即以儒家治世,弘教化為主導。他雖然師承真德秀等理學大儒,卻與他們有著本質的區別,是對傳統理學的顛覆。
劉克莊的母親林氏,出自書香門第,知書達理,晚年潛心佛教。由于深受母親的影響,劉克莊很早就對佛教充滿濃厚的興趣,研究各種佛教典籍,具有深厚的佛學修養。但劉克莊在接受佛學時深受理學的影響,主張儒釋異跡而同理,他說:“儒釋有異同之跡,倫跡無絕滅之理。世所傳釋氏事,多失之過而流于誕。其忠厚而蹈乎常者,余信之;乖悖而不近乎情者,余疑焉。試以其書考之,已入涅槃,猶起棺中,為母說法。他日迦葉本遺意以金縷僧迦黎衣屬之何難?嗟乎!釋氏何曾自外于倫紀哉!儒詆釋為夷教,義理一也,豈有華夷之辨哉?吾聞身毒罽賓諸國,皆有城郭君民,其法度教令,雖不可得而祥,竊意其獎忠孝而禁悖逆,大指無以異于中華,不然,則其類滅而國墟矣。”他從忠孝倫紀的角度出發,認為儒釋其實并無不同。同時,劉克莊還對詩禪有著深刻的見解,他認為詩禪的本質區別在于:詩須文字,禪則舍棄文字;詩真實而禪虛幻;詩情真而禪空虛。這些見解極為深刻,同時又把儒釋二教相融合。
除了儒釋思想外,老莊思想也對劉克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劉克莊和很多道士交往,不過他與道士交往不是為了煉丹學道,而是為了切磋詩藝。劉克莊所謂的“詩非易作須勤讀,琴亦難精莫廢彈。憶上洪崖題瀑布,因游試為拂塵看”也許可以看成對他自己的準確寫照。在老莊所說的自然中,大多是指事物的非人為的、天然的、原始的存在狀態,并且認為這種狀態是最合理的、最真實的,也是最美的。《莊子·駢拇》云:“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余,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所謂“不失其性命之情”,就是不能按人類的審美標準和價值觀念,改變事物天然的存在狀態,基于此,莊子還認為儒家倡導禮樂仁義,都是人為的矯揉造作,是少數人撈取功名利祿的工具,要獲得真知,要領會真美,要聆聽至樂,必須徹底拋棄音樂、美術、語言等人類文明。劉克莊因“落梅詩案”被貶,有將近20年的時間居住在鄉間,更加接近自然。因此,他的美學觀接近老莊的自然觀:“風之翏然也,水之淙然也,嘯之□然也,入于耳同也,然南郭子綦以為天,元結以為全聲,阮籍以為鼓吹、為鳳音,得于心異也。……昔之人有以竹陶寫為樂者,有以朋友切偲為樂者。絲竹,托于物之聲也,人也;雨,自然之聲也,天也。朋友,取諸人之樂也,外也;兄弟,修于家之樂也,內也。今夫大衾長枕,短檠細字,漏斷人寂,塤唱箎和,當此之時,溜于檐,滴于階者,如奏簫韶,如鼓云和,靜者聞,躁者不聞也,定者知,動者不知也。”劉克莊認為自然界的風聲、水聲、嘯聲,出自天然,是美的最高境界,只能用“天”、“全”來形容,這種“全聲”、“鼓吹”、“鳳音”只有像元結、阮籍等內心靜定之人才能領會和體認;而絲、木、竹、陶等演奏的音樂都是外在的、人為的,是“托物之聲”,審美境界遠低于那些天籟之音。道家自然觀深深影響了劉克莊的文藝觀和詩學觀,他認為不論什么樣的“人巧”,也不可能奪“天工”;相反,只有滅“人巧”,才能讓事物恢復它的天真狀態。這在他的詩學上就集中表現為崇尚“自然”、“天成”,反對雕章琢句,破壞詩歌整體的美感。這樣的觀點在《大全集》中隨處可見,他經常以此來評價后學詩歌的優劣:“不鍛煉而精粹者,天成也,或以人力為之,勉強而不近矣。”“設的于心,發無虛弦,其稿于腹成不加點,讀之盡卷,不見其辭窮義墮處。”劉克莊雖然是受老莊影響,但卻不否定以儒家為主導的價值觀,而是能把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相區分。
劉克莊生于南宋理學盛行的年代,同時又深受家庭的影響與受黨爭牽連被貶,居住田間的命運,這些因素的相互滲透,形成了劉克莊獨特的詩學觀——以理學為基礎,同時雜糅儒釋道,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非儒非佛亦非仙”,也正是他的這種詩學觀,讓我們看到了儒釋道的融合,而不是一味地排斥。
[1]劉克莊.后村詩話[M].中華書局,1983.
[2]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M].四部叢刊本.
[3]王述堯.劉克莊與南宋后期文學研究[M].東方出版中心,2008.2.
[4]王明見.劉克莊與中國詩學[M].巴蜀書社,2004.
[5]曾棗莊.宋代文學與宋代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M].中華書局,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