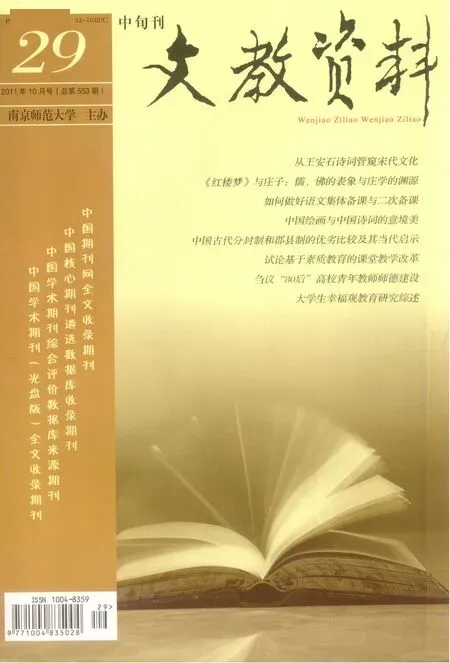生態批評視角下的《老人與海》
張 琴
(巢湖學院 外語系,安徽 巢湖 238000)
生態批評(Ecocriticism)是美國批評家威廉·魯克特(WilliamRueckert)于1978年在《文學與生態學:一次生態批評實驗》(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次提出的概念。生態批評是以保護生態為中心,研究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的文學批評理論,旨在確定文學、自然與文化之間的關系。隨著生態批評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經典作品被重新解讀,目的在于發現其中的生態意義,以及喚醒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
許多中外文藝評論家已著重就硬漢形象、悲劇意識和藝術特色等來闡釋小說《老人與海》。然而,海明威是一位迷戀大自然的作家,所以自然不能不是海明威創作的主題之一。莽莽蒼蒼的森林,川流不息的河流,波濤洶涌的大海,浮崗暖翠的山巒為海明威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創作源泉,打獵、釣魚、滑雪等這些接近大自然的活動,他保持了一生。對大自然的熱愛,對戰爭的厭惡,對人類文明的失望,使海明威終生都在尋找未遭破壞、未被開發的自然,以求慰藉,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海明威所具有的生態保護意識,我相信這種意識也會在他的作品中體現出來。本文擬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探討《老人與海》中體現的生態意識:對人類征服自然的批判以及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批評,人與自然應該和諧發展。
一、對人類征服自然的批判
大自然的威力是無窮無盡的,所以人類只能在某個層面上暫時地征服自然。生態批評的任務是批判人對自然的無情征服。為了更好地融入自然生態圈,首先要認識到人是自然的一分子,培養正確的生態審美觀。“生態美所體現的是人與自然的關聯和生命共感”。格倫·拉佛認為《老人與海》體現出了一定的生態意識。《白鯨》中的亞哈,固執,對自然只有強烈的憎恨和復仇的狂熱;而圣地亞哥卻總是把海洋看成女性,“她給人或者不愿給人莫大的恩惠,如果她干出了任性或缺德的事兒來,那是因為她由不得自己”。老人對象征自然的大海進行了贊美,表現出對自然規律的深刻認識和理解。反過來,正是處于認同自然規律的立場,所以他熱愛大自然。“老人如今只夢見一些地方和海灘上的獅子。它們在暮色中像小貓一般嬉耍著,他愛它們”。即使在與象征自然威力的馬林魚和鯊魚搏斗的過程中,他也明顯流露出對自然的愛,甚至崇敬。
然而,老人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憑借他的意志和智慧置魚于死地。“魚啊,”他說,“我愛你,非常尊敬你。不過今天無論如何要把你殺死。”圣地亞哥把馬林魚看成自己的兄弟、朋友,并對馬林魚優美的姿態、絢麗的色彩、頑強的生命力進行了贊美,他由衷地說道:“魚啊,我愛你,非常尊敬你。”可是在斗爭過程中,圣地亞哥把馬林魚看成自己的對手,不同于自身的外部存在,為此他還時常把自己同魚做比較,找出二者的差異:我比它更聰明,而它比我們高尚,更有能耐,也許我僅僅是武器比它強。這里深刻地體現了海明威對人類愚蠢行為的諷刺,表明如果人類不依靠外在的武器是打敗不了大自然的。這種靠武器征服自然取得的短暫勝利,最終會因為人類膨脹的欲望,無視自然規律對自然盲目改造而演變成更大意義上的失敗,以致人類自身的覆滅。
老人雖然暫時戰勝了象征大自然的馬林魚,最終卻被象征復仇的鯊魚打敗。圣地亞哥在和大魚做殊死搏斗中心里一直很矛盾,雖然表現出了很強的負罪感并對自己的欲望進行譴責和自我反省,但最終還是殺死了大魚。老人不停地對以這種方式證明自身價值的途徑加以懷疑、反思,不停地自我批判又自我辯解:“它們這情景是我看到最傷心的了。”“也許殺死這條魚是一樁罪過。”難能可貴的是,老人思考了失敗的原因,那么是什么把你打敗的?“什么也沒有,只怪我出海太遠了。”說到底,是人類自己打敗了自己,怪不得自然。海明威出于對大自然的迷戀和對人類破壞自然的譴責而特意在故事結束時,安排了戲劇性的一幕:它(魚的骨架)如今不過是垃圾了,只等潮水來把它帶走。人類千心萬苦戰勝自然所締造的輝煌文明,到頭來因為出海太遠而導致最終的毀滅,只有等待著時間來沖刷輝煌過后的殘跡。對人類來說,這不能不算莫大的悲哀,海明威留給世人的警鐘引起我們深刻的反思。
二、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批判
隨著人類自身的不斷發展,改造自然的能力也隨之加強,進而人們會片面地、盲目地以人類自身為中心而忽視大自然的威力。人類中心主義主要表現在三個不同的層面上:生物學意義上的、認識論意義上的、價值論意識上的。生態倫理學反對的是價值論意義上的人類中心論。正如《人類中心論與環境倫理學》一文指出的那樣:“人類中心論所崇尚的價值王國是人根據其對人的完美形象的理解和對人的存在的終極關懷所構建的意義世界,是人塑造、確認和完成自我的一種方式。”這種價值觀認為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則的唯一出發點,人可以為了使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無視自然規律,對自然加以踐踏和蹂躪。
海明威在肯定了征服自然的物質欲望膨脹最終導致人類文明毀滅的同時,隱晦地強調人應該在征服自然的精神勝利中實現自我價值。硬漢式的精神勝利的安慰與精神生態是背道而馳的。生態的價值觀從道德或類似于宗教的高度敦促人們在人性中培養對大自然的熱愛和憧憬。放棄過度追求物質欲望,從精神上融入自然。海明威置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于整個自然界的整體和諧之上,不顧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而去追求所謂的精神勝利,這實質是人類中心主義在價值觀上的表現。老人在對自己的掠奪行為內疚的同時,卻又自我辯解,認為他天生就是干這行的。捕獲大馬林魚,戰勝兇狠的鯊魚,是圣地亞哥確立自己的社會價值,完成上帝在創世時賦予人類光榮的使命,證明自身能力的方式。在那場人與魚的殊死搏斗中,老人充滿了自信與驕傲,他把與大魚的殊死搏斗視為維護人的尊嚴所必需的。正如老人所說,他殺死魚是“為了自尊心”,是為了讓人們和他自己相信“你永遠行的”,也要讓大自然知道人有多少能耐,人能忍受多少磨難。
持人類中心論必然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后果。在這個時代,人類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作用于自然界,為自己創造了日益豐富的物質財富。此后,在經歷了兩個多世紀與大自然作斗爭的歷史之后,當人類沉浸于自己取得的偉大成就而洋洋得意時,卻同時嘗到了人類中心主義給自己帶來的苦果。大自然向人類敲響了警鐘:臭氧空洞,溫室效應,全球變暖,物種滅絕,資源枯竭,大氣污染,人口爆炸,土地侵蝕和沙漠化,等等,這些現象已經嚴重地威脅著人類自身的生存。
三、人與自然應該和諧發展
生態批評把批評的焦點從社會關系轉移到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把個人看做既是生態系統中的一員,又是社會中的一員。它思索、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并試圖改善這種關系。格倫·洛佛也認為《老人與海》體現出了生態意識。在《老人與海》中,海明威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了哲學思考。他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有對立的一面,也有統一的一面。對立中體現著統一,統一中包含著對立。所以要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平衡人與自然的發展。
重返自然的懷抱是生態文學批評的理想。最初,人類曾與自然相依為命,保持著和諧的關系,在生態危機不斷加劇的現代社會里,人類渴望與自然重新建立和諧統一的關系。在《老人與海》中,圣地亞哥就是敬畏自然的原始居民的化身。他是生活在古巴的一位老漁民,他撐的是古老的小漁船,他手拉的是古老的纖繩……沒有一樣不是古老的,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原始的老漁民。他對自然充滿了熱愛和敬畏之情。作品中反復描述了老人在殺死大魚的過程中所表達對自然的敬意,第一天與大魚較量時,老人就說“很尊敬你”。隨著大魚與老人的進一步較量,老人對大魚的敬意也越來越濃,他對大魚說:“我從沒見過比你更偉大、更美麗、或更從容、或更崇高的兄弟。來吧,殺了我。我不在乎咱們誰殺誰。”老人的自然觀是原始民式的,自然是偉大高尚的、物種之間是平等的,人的生存要靠與自然界的物質交換。同時,老人認為無人配吃大魚,沒有人配毀滅自然。在殺死大魚的過程中,罪惡感始終糾纏著老人,他反復提出疑問:“也許殺死大魚是罪過的……他想了很多,不斷地考慮罪過問題。”罪惡感又致使老人反復地為自己辯解,“不要在想是否有罪的問題了……你生就一漁民,而魚生就為魚……從某種意義來說每個事物都會殺死另外別的事物的。打魚能讓我生,也能讓我死。”老人的辯解是想讓自己心里舒服點。老人的夢境也充分表達了回歸自然的愿望。在老人遠航前,船上休息時,以及老人遠航歸來的睡夢里,呈現的都是金色的海灘,與人相處融洽的獅子,還有怡然自得的人們,人完全地融入自然。這是老漁民的夢想,也是生態文學批評的理想。
綜上所述,《老人與海》是一篇可以從生態批評視角來解讀的文本,生態文學旨在喚醒人類的生態保護意識:人類應該熱愛大自然,不應該以破壞自然環境為代價來發展經濟,否則會適得其反。
[1]常耀信.美國文學簡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2]董衡巽.海明威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70.
[3]雷毅.生態倫理學.[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2000.
[4]王諾.歐美生態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5]楊通進.人類中心論與環境倫理學[J].人大復印資料·倫理學,1999,(3):62.
[6]趙富春.老人與海[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3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