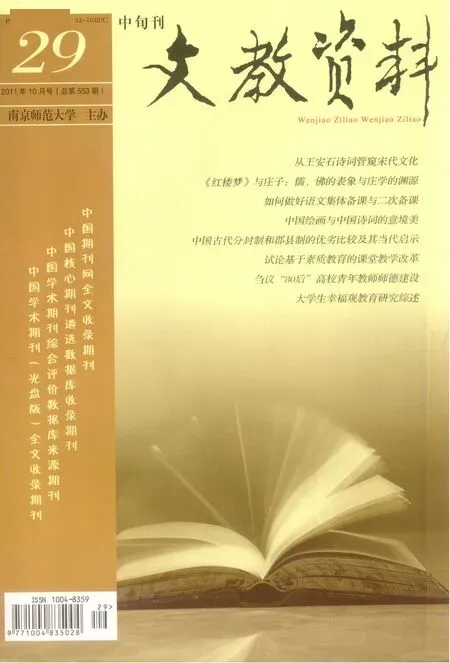“主 問 題”、“建 構”及 “對 話”——蘇教版《〈論語〉〈孟子〉選讀》教法研究
陸 琦
(江蘇省南菁高級中學,江蘇 江陰 214437)
《選修課課程實施章程》指出:教師應“從課程的目標和學生的具體情況出發,靈活運用多種教學策略”,“創造性地使用教科書和其他有關資料”。落實到蘇教版《〈論語〉〈孟子〉選讀》的教學,我認為,以下三種方法較為實用,較具新意。
一、“主問題”教學法
《〈論語〉〈孟子〉選讀》教材編選突破了《論語》《孟子》的原有形式,按“主題”整合呈現——對原典的選擇性,增強了教材的可讀性;選文的梯度性,體現了邏輯的周密性。教材整體予人中心突出,條理明晰之感,既貼近社會生活,又兼及學生需求。編選形式還暗示了一個基本事實:每課的教學都應是有章可循的。教師提煉每章主題,重整教材,以簡馭繁的“主問題”教學法是完全可行的。
采用“主問題”法教學《〈論語〉〈孟子〉選讀》,“主問題”的設定要遵循以下原則。首先,“主問題”應有利于簡化頭緒、強化重點。例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共16章,選文從《論語》的《學而第一》一直延展到《陽貨第十七》,不能理出一條清晰的思維脈絡的話,師生的教和學都將是“一頭霧水”。其次,“主問題”應利于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如《道則高矣,美矣》課后練習:“孔子和孟子是怎樣形容‘道’的?他們提出的‘道’有哪些內涵?”如果據此設置此篇主問題為“孔孟之‘道’的內涵”的話,就大而無當,很難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再次,“主問題”的設置要立足于文本。即便是選修課,即便是特別注重文化思想探究的《〈論語〉〈孟子〉選讀》教學,仍應以“本”為“本”,忌架空式分析、拓展。基于文本的“主問題”探討,最終也必須回歸文本。最后,“主問題”的設置必須具備現實意義。如《天之未喪斯文也》教學中我設置了幾個“主問題”,其中一個為:“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在原文中是如何體現的?請結合歷史與現實,談談你對孔子這種思想、行為的認識。”這個“主問題”的設置,超越了對孔子思想的靜止探討,聯系現實,引導學生對孔子的人格精神一分為二式地批判繼承,也正體現了新課程“探究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和作用”的教學目標。
二、“建構型”教學法
“建構”作為一種教學理論,由教育家奧蘇貝爾提出,后來逐步形成一定的教學形式:“以學生為中心,在整個教學過程中由教師起組織者、指導者、幫助者和促進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協作、會話等學習環境要素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首創精神,最終達到使學生有效地實現對當前所學知識的意義建構的目的。”
這種教學法涉及四要素間的關聯:“情境”,要求教師創設利于意義建構的教學環境;“協作”,是學生以小組方式搜集資料,提出、驗證假設(意義建構),并能有效進行學習評價的合作過程;“會話”,搜集到的資料集體共享,形成學生與教學資源的會話,教學“情境”中,學生不斷交流“協作”,最終形成“意義建構”;“意義建構”,即發現事物的性質、規律,揭示事物間的內在聯系。教師實施教學,主要就是通過情境課堂的創設,幫助、促進學生獲得關于這些規律和聯系的較為深刻的認識。
《〈論語〉〈孟子〉選讀》的教學,關鍵即是意義的建構。“文字意義”、“文學意義”和“文化意義”,應成為教學的主要定位,也即學生學習應達成的意義建構。在建構型教學中,教師是主導,意義建構的主體是學生,經由交流合作獲得意義。這一點特別符合現代教學,尤其是選修教學的理念。
“文字意義”的建構:教師可布置小組進行字詞句的文言重點整理,然后進行組際交流,其間學生可就預習內容提出一些想法、疑問等;“文學意義”的構建:教師引領學生進入感知情境,通過指導他們反復誦讀、體驗,讓學生歸納,教師適度整合、提升;“文化意義”的建構:教師可以通過一些較為寬泛的問題的創設,如“談談你最喜歡的一章”“說說你最喜歡哪句話,為什么”等,采取學習心得交流、成果展示等形式,學生個別發言、互評、討論、辯論等協作會話方式,教師在關鍵處注意點撥,把學生導向較有探討價值的內容意義層面的切磋、思辨上去。
三、“對話式”教學法
孔子善用“對話式”教學,與蘇格拉底“對話式”教學遙相輝映。“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一句話拉開了《萬物皆備于我》開篇的經典一幕——“沂水春風吾與點”。初始即以對話領入,孔子鼓勵學生縱談志向;當曾點參與對話,志向異于兩位同學時,孔子進一步鼓勵:“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最終孔子以一句“吾與點也”,予彼時乃至后世學子們無盡的玩味。這種教學方法,營造和諧愉悅的教學氛圍,與學生平等切磋,相互啟發,潛移默化,一切盡在“對話”中。教學《〈論語〉〈孟子〉選讀》,不妨借鑒這種方法,具體操作如下。
(一)引進話題,展開對話。
孔子展開對話教學,往往先確定一個核心話題。對話中教師適度點撥,學生自我生成,教師再追加評點。這完全契合新課程“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教學理念。本教材教學,采用此種做法不可或缺。如《學而時習之》教學時,要求學生對章節內容進行對話式點評。教讀“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時,請學生結合實例理解交流。有的同學想到《石鐘山記》,有的提及《傲慢與偏見》,有的回顧韓非子《智子疑鄰》,有的甚至結合佛學的“正見”、“斷見”、“偏見”,以及王陽明“心學”內容,甚而至于聯系當下生活趣事:課堂形式精彩紛呈,對話交流互為補充,學生在妙趣中感悟收獲。最后我結合篇章的話題重心適度拓展。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的認識,讓學生真正體悟到經典包容萬事萬理的高度涵容和深度智慧,經典意蘊在不知不覺中更能散發出燭照現實的光輝。
(二)延展對話,拓寬視野。
孔、孟時代,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群星閃耀的時代”,包括儒家在內的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等“諸子百家”,其思想如奇葩異蕾爭奇斗妍;教材從選文到練習羅列了不同學派觀點的比較;現實生活中,“百家講壇”等文化普及欄目也所在皆是:眾多渠道都共同指向教學對話多方延展的可操作性。適度地講解老莊“無為”、墨家“兼愛”、楊朱“為我”、韓非“法治”的思想主張,介紹適合高中生閱讀的鮑鵬山的《寂寞圣哲》、于丹的《論語心得》等書籍;安排學生觀看電影《孔子》及百家講壇的相關視頻,讓學生盡可能拓寬眼界,全方面多渠道地感知孔、孟對時代、社會的全面影響力。這種對話,超越了文本與現實課堂,“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對學生來說無疑更具現實意義。
(三)反思對話,辨疑創造。
教學需“從無疑處生疑”。孔子對話式教學中,“辨疑”比比皆是。如《政者,正也》選段:“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中,我們就看到了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聰明學生子貢,誨人不倦的淳厚長者孔子。
在《〈論語〉〈孟子〉選讀》教學中,教師既要引領學生切磋、感悟圣哲智慧,又要關注時代需求與價值評判,發現古圣先賢的思維局限。教師要盡可能地創設問題情境,讓學生在矛盾感的糾結中自然激發疑問,不斷的對話盤問最終會贏得“且驚且喜”的意外收獲,教學亦隨之收獲越來越多的學習熱情。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中孔子“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和“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的教學思想,已不切合知識爆炸時代的教學訴求,這時就需要促進學生在對話中加強反思,以真正鍛煉他們的思維能力,讓經典在對話的語境中歷久彌新。
[1]余映潮.我對閱讀教學“主問題”的研究與實踐.
[2]陳建華.高中新課程《論語》選讀教學策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