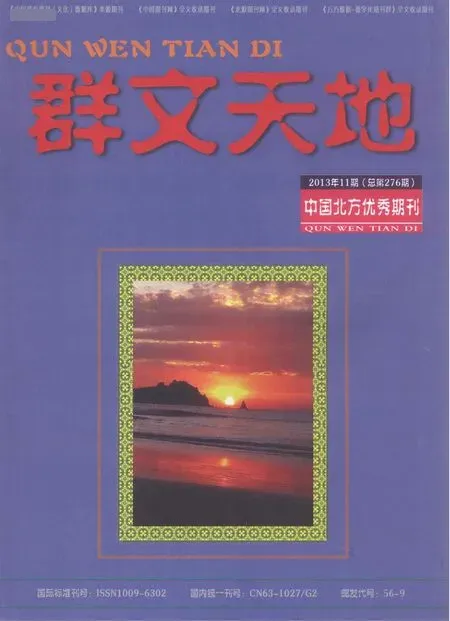環青海湖茶馬互市的沿革與發展
■任玉貴
茶馬互市沿革史
茶馬互市起于兩漢,興于唐宋,衰于清代。
茶,尤其是湖南益陽出產的磚茶和出自四川的松潘茶,一向都是高原民族的生活必需品。時至今日,這種茶需求有過之而無不及。據《西寧府新志·藝文》記載:北宋時代的唃廝啰“人喜啖生物,無蔬茹醋醬,獨知用鹽為滋味,而嗜酒及茶。”《明史·食貨志》中說:“蕃人(指藏族)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倚中國茶為命。”對這種現象,清初大學者顧炎武這樣解釋:“茶之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于此。”看來,居住在青藏古道的民族,喝茶主要是為了消食和健胃。有“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之說。
茶葉來自漢地的故事,藏族中有這樣的流傳:吐蕃王朝的第36代贊普身染重病,經所有名醫診治后,不見好轉。有一天,一只稀有美麗小鳥口含綠葉,落在王宮樓頂的檐墻上跳來跳去。曬著太陽的贊普,拖著病體輕輕走上前去想逮住這只小鳥,但它嘰嘰喳喳叫了幾聲后飛走了,而它口中的那片綠葉卻落在贊普的雙腳前。贊普拾起這片綠葉放在自己又干又澀的嘴里,頓覺這片綠葉有滋有味,口內生津,精神也爽快了許多,于是,便傳旨眾大臣快快去找這種樹葉。眾大臣踏遍吐蕃全境,一無所獲,失望而歸。只有一個特別忠誠的大臣,滿懷希望,來到漢藏交界的地方(一般指青海東部)繼續尋找,仍然見不到小鳥口含的那種樹葉。他沒有死心,又渡過黃河,前往漢地充滿生機的森林里去找,上天不負苦心人,他在漢地林中終于找到了那種樹葉。他大喜若狂,就摘了兩口袋,搭在一只母鹿的背上,渡過黃河,馱回吐蕃。贊普用開水沖喝了這種樹葉后,身體很快康復了。
《唐國史補》中說:常魯公出使吐蕃,一天在帳篷里煮茶,贊普問道:“你煮的是什么?”魯公說:“洗滌煩悶,治療口渴,就是所謂的茶。”贊普說:“哦,這個”,便叫侍從搬來許多茶葉,以手指著說:“這是壽州的,這是舒州的,這是顧渚的,這是蘄門的,這是昌明的,這是西湖的。”沒有一樣不是漢地的。顯然,這些來自中原大江南北的茶葉主要是通過易馬換來的。
早在西漢時期,漢朝就同匈奴在邊境地區設立互市,南北朝以來邊地茶馬互市發展迅速,隋代王朝專門成立機構,管理茶馬互市。唐代青海的畜牧業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青海有良好的畜牧業自然條件。吐蕃進居青海草原后仍以畜牧經濟為主,史稱吐蕃“俗養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為褐而衣焉”,“其畜牧,逐水草,無常所”,“其獸,牦牛、名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為裘,獨峰駝日馳千里”,吐蕃經營畜牧業的生產技術已相當進步。據藏文史書記載,早在吐蕃七賢臣之首如勒杰之時,已知“在夏天將草割下成捆收藏以備冬天飼養牲畜”。唐高宗中期,黨項除降唐內遷的以外,留居故地者成了吐蕃部屬。史載黨項人“俗皆土著,有棟宇,織牦牛及羊毛覆之”,“男女并衣裘褐,仍被大氈,不知耕稼,土無五谷,氣候多風寒,以牦牛、馬、驢、羊、豕為食。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黨項人世代以畜牧為生,創造和積累了適應本地高寒氣候的生產經驗,為青海畜牧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青海畜牧業中養馬業尤為發達。吐谷渾人培育的“青海驄”在唐代仍馳名于世。吐蕃在河曲之地培育的河曲馬也名聲遠揚。青海詩人吳栻在《青海駿馬行》中寫道:“極目西平大海東,傳來冀北馬群空。當年隋煬求龍種,果能逐電又追風。”描述了青海良馬不同凡響。據《青海通史》記載:唐太宗非常重視茶馬互市,于赤嶺(今日月山)設立官方茶馬互市。以茶換取戰馬和耕牛,從貞觀到麟德(公元627—665年)將近40年間,唐朝的官馬發展到70.6萬匹。唐置八使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為隘狹,更析為監,布于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文中“河曲豐曠之野”即今青海黃南、海南和果洛藏族自治州北部一帶,是當時重要的牧養官馬地區。后來,由于河南之地一度劃贈吐蕃,影響到唐官馬的發展,開元初,牧馬下降到24萬匹。玄宗任用王毛仲為太仆卿主持馬政,與吐蕃在赤嶺互市,以茶、絲絹等易馬,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官馬又發展到43萬匹。北宋前期,青唐吐蕃各部與宋朝以茶馬貿易進行,官運川茶,出賣博馬。吐蕃各蕃向宋朝輸出的馬匹總數中,青唐政權所屬各部占有最大份額,國家買馬歲二萬匹,而青唐十居七八。
貢賜貿易是宋代青海吐蕃各部與內地經濟貿易關系的重要環節。青唐政權及其大小首領不斷把以馬匹為主的各種畜產品以“貢品”形式輸入內地,宋代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唃廝啰和李立遵向宋朝貢馬582匹,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董氈貢馬460匹,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阿里骨貢馬179匹。出于支持青唐政權抗擊西夏的需要,北宋朝廷還給其大小首領以“歲賜”、“月賜”等各種形式直接提供大量的物資援助。其中包括茶葉、布帛、藥品乃至一些通常被禁止出邊的物資。如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宋朝定例給唃廝啰彩絹1000匹,角茶1000斤,散茶1500斤。
吐蕃各部與宋朝內地的經濟貿易使雙方都獲得了可觀的利益,大大彌補了各自經濟上存在的不足,大量馬匹源源不斷輸入內地,保障了宋朝馬政的正常運作,支持了邊防。而經濟落后、物資匱乏的吐蕃各部由于得到來自內地的不可或缺的經濟補給,使其社會生產生活得以正常維系,應該說,青唐吐蕃政權政治軍事上的聯宋抗夏正是以經濟上的這種互補性作為物質基礎的。
明代,西北地區茶馬貿易空前繁榮,這一方面是由于明朝為抵御蒙古,需要從西北輸入大量戰馬;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內地封建商品經濟日趨繁榮的影響,西寧與河州、洮州成為茶馬貿易的三大中心。
明初,全國戰事尚未結束,因對戰馬的需求量很大,就不斷派人員到青藏地區購買或用實物交易馬匹。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監而聶又以茶30萬斤易馬10300多匹,這些交易規模都很大,也表現出了青藏地區各部參與這種交易的積極性很高。有詩道:“交給馬匹換茯茶,上馬飛奔各進山”。
明后期,西海蒙古與明廷在沿邊路口規定的地點定期進行互市。互市期間,先由官府與蒙古各部貿易,然后開放邊口民市。清初,清廷與青海蒙古諸部繼續開展邊口互市。順治年間,互市地點大致定在鎮海堡、北川口、洪水口等地,后因貿易發展,互市地點增多,白塔兒(今青海大通縣老城關)、多巴市場都相當繁盛。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以后,規定每年二、八月在西寧西川邊外那拉撒拉(今湟源日月山)地方茶馬互市。
清前期,青海地區各種形式的貿易都有較大發展。伴隨貿易的發展,茶馬貿易是青海地區最主要的也是傳統的一種民族貿易形式。清沿明制,繼續實行茶馬互市,并在西寧、洮州、河州、莊浪、甘州設了5個茶馬司,由陜西茶馬御使管轄。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定例,上馬給茶12篦(有時也可以用青稞、布匹等物換取牛、羊、駱駝等牲畜),中馬給茶10篦,下馬給茶8篦。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因西域用兵,急需馬匹,又恢復茶馬交易,上馬一匹,給茶12篦;中馬一匹,給茶9篦;下馬一匹,給茶7篦。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新疆戰事結束,馬匹需求量減少,而藏族各部也易馬為累,于是以茶易馬再次停止。由于茶馬互市實行日久,積弊叢生,以茶易馬已失去了原本控制少數民族手段的作用。清朝幅員廣大,前期國力強盛,馬匹易得,用不著在青藏地區用茶葉易換,于是在中國西北地區實行了1000多年左右的茶馬市易制度從此被廢除。此后,茶馬司變成了“茶司”,不再管理易馬之事,但仍是清廷實行茶葉官賣的專門機構。
地處湟水上游的丹噶爾市場因“路通西藏,逼近青海”,“出則達西海,入則貫中原”,“為漢、土、回民遠近番人及蒙古往來交易之所”,嘉慶、道光之際,商業特盛,“青海、西藏番貨云集,內地各省客商輻輳,每年進口貨價至百二十萬兩之多”。丹噶爾商業地位突出,以馬、牛、羊為主的畜產品與茶、糧、布為主的日用品又成為西北地區民族貿易的重鎮,美稱“環海商都”。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領事館在中國西北旅行》一書中無不驚嘆地稱“西寧丹噶爾(今湟源)是偉大的環青海湖貿易中心,貿易如今達到非常大的規模”,《丹噶爾廳志》也一呼三嘆“迄今商業發達,幾成巨埠,歲輸白金幾十萬,盛矣!”
茶馬互市日月山
從秦漢時代開拓邊疆,到隋唐的大一統,中國疆域便有了擴大。眾多的兄弟民族,共同組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但由于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版圖廣大,地域遼闊,社會發展階段自然很難一致。一般來說,邊疆地區生產發展比內地較為落后,缺乏糧食和日常用品,而他們所生產的大量牛、羊、馬匹和畜產品,又是內地所特別需要的。古時候內地與邊疆物品的交流,一般是通過“進貢”和“賞賜”兩種方式來進行的。
早在赤嶺(今日月山),唐蕃設茶馬互市之前唐就與吐谷渾開始了以茶易馬的商貿活動。據《青海風物·聯姻通好》中記載:“唐朝初年,在平定了盤踞金城的薛舉后,以送回被隋留作人質的伏允長子慕容順為條件,遣使約吐谷渾夾擊盤踞涼州的大涼王李軌。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伏允出兵助唐滅李軌,唐送慕容順回青海地區,雙方建立了和好關系”。作為進一步完成大一統事業的唐朝,在削平薛舉、李軌的割據后,便在青海東部地區設置鄯州刺史,駐樂都,以今西寧為鄯城縣。這種措施,使西陲重地與祖國內地更緊密地聯系起來了,但對吐谷渾來說,感到有點不安,因此不免有一些小沖突。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唐派廣德郡公李安遠來青海(這里青海指今青海湖,日月山)與吐谷渾和好,雙方達成互市協議。這件事情在《舊唐書·李安遠傳》中記載:“使于吐谷渾,與敦和好,于是,吐谷渾允請與中國互市,安遠之功也”。當即《冊府》所書者云:“非僅吐谷渾一族,蓋此地邊諸要求于互市于此,邊場利之”,足見商易互市的重要性。在封建社會中,各民族間除聯姻外,互市又是促進文化與產品交流、加強相互往來的一條重要渠道。從此吐谷渾的龍駒和牛、羊被交換到內地,而內地的絲、茶及日用品,也源源不斷進入西部廣大地區,滿足了邊疆地區兄弟各民族的需要,促進了民族之間的進一步團結。
日月山,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所使然,長期以來青海的經濟是以自給自足的農牧業經濟為基礎的,畜牧業經濟使青海很大一部分地區的生產方式呈現出牧中有農、農中有牧、農牧業產品互為補充以滿足人們生活需求的特點。青海一般以日月山為界,西部以牧業為主,兼及農業;東部則以農業為主,兼及牧業。在牧業方面,從諸羌時代起,各民族牧民群眾就繁殖適應高原氣候特點的耐寒畜種。青藏高原的藏系羊,個頭大而耐寒,長期以來解決牧民群眾的主要食物——肉食,主要服裝——皮襖,以及毛織等用品;他們養牧羊、犏牛以解決畜力馱運、住房——牛毛帳篷,油料——酥油,飲料——牛奶等生活問題;他們飼養馬匹,解決了交通工具問題,歷史上與中原地區進行“茶馬互市”以換取必需的日用生活,如糧、油、布、絲、茶、瓷等,也是提高生活質量的必然追求和實際需要。
唐蕃在赤嶺的茶馬互市在《方輿紀要·陜西十三·西鎮》赤嶺條中又專門作了詳盡的敘述:“開元十九年,吐蕃請交馬于赤嶺,互市于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為界,表石刻約。二十二年,又立碑于赤嶺,分唐與吐蕃之境。二十六年,命河西節度使蕭炅、隴右節度使杜希望經略吐蕃,碎赤嶺碑。天寶八年,哥舒翰克吐蕃石堡城,復以赤嶺為西塞。長慶二年,吐蕃復請定疆候、大理卿劉元鼎過石堡城西行數十里,土石皆赤,名曰赤嶺,蓋隴右故地,距長安三千里,即開元中與吐蕃分界處也。”
赤嶺即今日月山,在《可愛的青海·日月山》中專門對茶馬互市做了直截了當的記述:日月山的聞名于世,還在于它是古代邊防重地和“茶馬”互市的地方。日月山,因山頂土質呈紅色,故古稱赤嶺。公元734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唐與吐蕃遣使于赤嶺劃界立碑,定點互市,赤嶺遂成為唐蕃古道上的重要貿易集市。唐與吐蕃劃界立碑,雙方保證:“不以兵強而害義,不以為利而棄信。”并正式確定赤嶺為入藏道上的重要邊防關隘。隋唐時頗具盛名的石堡城,自隋朝筑城設戍后,到唐代改設振武軍,其遺址就在日月山下的今湟源縣日月鄉莫多吉村。山上古城堡的斷垣殘壁,仍依稀可見,昔日雄姿尚可窺見一斑。
有的學者提出,赤嶺(今日月山)有“互市”而無茶馬。對于這種說法在《青海通史》第207頁中有鏗鏘有力的回答:“開元初,牧馬下降到24萬匹,玄宗任用王毛仲為太仆卿主持馬政,與吐蕃在赤嶺互市,以茶、絹等易馬,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官馬又發展到43萬匹”。互市離不開茶馬,茶馬交易又需要互市。
日月山茶馬互市除了歷史文獻可作依據,歷史遺留的文物也是可靠的見證。據《西寧府續志·地理志》記載:新設的丹噶爾廳(后來湟源縣)有“字爾石”,在城(今湟源縣)南三十余里藥水峽中,有巨石,高丈余。上寫漢番字跡,剝落不可辨。惟開元十九年數字顯然,故名“下面”。周子揚箋:“按《通鑒》開元十九年春正月,遣鴻臚卿崔琳使吐蕃,是年九月,吐蕃遣其相(論尚定律)入見,請于赤嶺為互市,許之”。
公元734年(唐開元二十二年),唐與吐蕃在赤嶺今湟源縣日月山互市易馬,肅宗以后,“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是為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茶馬互市”。由于牧區沒有農業,不產糧食,素以奶、肉為食,茶馬互市既開,吐蕃牧民可用馬匹換取糧食,以后又增換縑絹和茶,對改善牧民生活帶來很大的好處。能夠“釋氈裘、裘紈綺、漸慕華風”。唐王朝推行“茶馬互市”制度,在政治上起到了控制邊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促進了唐蕃雙方經濟的發展。如自赤嶺開市后的十多年中,唐王朝獲得數十萬計的青海良馬,軍馬得到了極大補充。同時農用役畜的耕牛,也在互市中得到了相應的滿足。以后赤嶺茶馬互市時設時廢。明末,今縣城地區商賈漸集,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年羹堯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之后,在向清政府所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條》中稱:蒙藏牧民“其與內地相互交易之處,定以每年二月、八月兩次,俱以邊外為集,臣選得西寧西川邊外有那拉撒拉地方(即日月山),請指定為集,不準擅移”。于此可見,隋唐以來,日月山又因茶馬互市而遐邇聞名。
茶馬重鎮托拉圖
托拉圖清代稱“哈拉庫圖爾”,民國時稱“哈城”。設官理商,筑城護商。據《西陲史志研究》記載:“此地依日月山,為商旅要區”。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清政府增設丹噶爾營守備一員、把總一員,駐哈拉庫圖爾,歸丹噶爾參將統轄。駐軍有馬戰兵一百名,步戰兵一百名。駐軍之舉,肯定了哈拉庫圖爾為邊陲關隘的地位。時西寧道僉事楊應琚以哈拉庫圖爾地倚日月山,為行商往來之要區,“委西寧知縣靳夢麟巡督”(見《西寧府新志卷之九·建制志》),筑城一座,定名為哈拉庫圖爾城,城設東西二門,周回二百二十八丈,根寬一丈八尺,頂寬九尺。西門倚山,無所往來,常年關閉,或謂古昔有兵一旅,自西門出征,沒于陣,無一生還,故閉西門,惟開東門,與居民相通。
城為旗形,東西門并設甕城,城四角設有碉堡。現今其城墻垣因久經風蝕雨剝,碉堡等建筑已蕩然無存,東城墻已經拆除,其余西南北城墻尚在。1993年6月,湟源縣政府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土城筑于龍山之上,當地鄉親說:昔日筑城于龍山,是因為龍山是塊風水寶地,青龍居住之所,山上有眼龍泉,青龍吐水,水質甘甜,水草豐美,山花爛漫,筑城以縛青龍,使“龍頭戴枷”,永駐寶地,福佑地方。
名為城,但城內并無民房設施,也無居民居住,進入東門,橫在眼前的是守備署舊址,俗稱衙門,是守備辦公之所。拾級而上,右側是土地廟,再后是城隍廟、禹王廟,左側是山神廟,再后是關帝廟。玉皇廟后面即是西門。這些廟宇等建筑現在銷聲匿跡,一無所在。出了東門,在龍山腳下,設南北街,曾建有過街樓。是繁華的商區,也是居民區。昔日南北街商店林立,湟源縣城的洋行和“歇家”大戶,均在這里設有分支商務辦事機構,接待蒙藏牧民,經營畜產品業務。此外,在城外東北臨河流處設演武場、趟窩(訓練軍馬的設施)直至莫多吉村。隔河山坡有料瓣臺,在城東南坡上有營盤臺,系古道盤遺址,疑是西漢古河源軍故城。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川陜總督大學士郎阿據議奏請添設哈拉庫圖爾等八營堡,哈拉庫圖爾營駐軍一百四十三名,千總一員。下轄日月山塘、窩卜兔卡汛、鐵勉庫卡汛。乾隆十二年以后,除增添、裁汰、移駐外,截至五十年止,存留馬步兵仍保持一百四十三名。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鑒于哈拉庫圖爾為邊內第一要沖,清政府將鎮海堡守備移駐哈拉庫圖爾,哈拉庫圖爾營千總移駐鎮海堡。由鎮海堡撥添馬兵二十四名,步兵三十八名,守兵三十七名。以后駐軍因裁撥、裁汰、暫停募補等原因,時有增減。于民國3年(1914年)哈拉庫圖爾營裁撤。
清政府在哈城駐軍設防,促進了哈城的開發。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年羹堯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之后,在向清政府所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條》中稱蒙藏
牧民“其與內地相互交易之處,定以每年二月、八月兩次,俱以邊外為集。臣選得西寧邊外有那拉撒拉(即今日月山一帶),請指定為集,不準擅移”。哈城距“海藏咽喉”的日月山近在咫尺,東南地方遼闊,蒙藏牧民的帳房牛羊彌望山谷,南山高峻,界限內外,東至東峽分水嶺,一層三十余里廣闊草原,中間哈城河自西南向東北,匯入兔兒干河,水甜草盛宜牧宜宿,當為開展貿易的支點,“城里扎的是營兵,城外灘上放羊人”。放羊牧馬的是住在這里的蒙藏牧民;市場上做中介的是來自丹噶爾會說蒙藏話的“刁郎子”;車拽馬馱的是環湖周圍千百戶;管理市場的是哈城守備。有“其買賣交易,東至湟源縣城而止,西至海藏地區而至,年交易千萬計”。
哈拉庫圖爾城為茶馬互市在《青海通史》中記載:明后期,西海蒙古與明廷在沿邊路口規定的地點定期進行互市。互市期間,先由官府與蒙古各部貿易,然后開放邊口民市。清初,清廷與青海蒙古諸部繼續開展邊口互市。順治年間,互市地點大致定在鎮海堡、北川口、拱水口等地,后因貿易發展,互市地點增多,白塔兒(今青海大通縣老城關)、多巴市場都相當繁盛。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以后,清廷曾對和碩特蒙古各部與河湟間漢回群眾的貿易往來予以嚴格控制,并將此視為駕馭控制青海各族的手段。規定每年二、八月在西寧西川邊外那拉撒拉(今青海日月山)地立交易,不準擅移,并令鎮營率兵彈壓,倘敢無故接近邊墻者加罪懲治。后因“各蒙古需用茶葉、布、面等物,交易之期過遠,必致窮乏”,經清廷議政大臣會議討論,又將日期定為每年四季四次交易,即以“二、五、八、十一月為互市日期”。但這仍不能滿足蒙古各部與回、漢各族間交易之需要。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奮衛將軍岳鐘琪奏稱:“親王插漢丹進(察丹津)、鎮國公拉查步等諸臺吉部落,位居黃河之東,切近河州,去松潘也,下甚遠,向來原在河州、松潘兩處貿易,今若只令在那拉撒拉一處,無論有無商販到彼,即就西寧一路所出藏馬口糧亦是無多,恐不足供黃河東西翼蒙古易買。且插漢丹進等部落遠隔黃河,渡涉為難,馱運繁費,即來貿易,恐也不能多多買賣,而又限于互市日月,未免匪其意愿。”清朝采納了岳鐘琪的建議,規定以河州土門關附近的雙城堡和松潘黃勝關外的西河口為互市之所。以后又由于游牧于青海湖南的郡色騰扎爾(綽羅斯南右翼首旗)和居于青海湖北的郡王厄爾德尼厄爾克托鼐(和碩特前左首旗)等諸臺吉部落地近西寧,遂將互市之所由口外那拉撒拉移到丹噶爾寺(今青海湟源境)。至于互市日期,也予以放寬。清統治者考慮到蒙藏貿易,全憑牲畜,都希望在六月以后牛羊肥壯之際貿易,于是規定每年任其不時貿易。
據歷史記載:清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定例,上馬給茶12篦(1篦重10斤),中馬給茶9篦,下馬給茶6篦(有時也可以用青稞、布匹等物換取牛、羊、駱駝等牲畜)。順治年間對茶馬交易中的大小茶引、征稅比例做了一些調整。康熙年間因私茶充斥,規定“凡攜帶私茶十斤以上無官引者論罪”。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令西寧等處征茶篦,停止易馬,將茶變價折銀,以充軍餉。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西寧茶馬司茶務歸西寧府管,并規定自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起,茶蓖以5年為一周期,5年內全征本色,5年后變賣舊茶,以防止茶葉年久泡爛。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因西域用兵,急需馬匹,又恢復茶馬交易,上馬一匹,給茶12篦;中馬一匹,給茶9篦;下馬一匹,給茶7篦。
茶馬互市貿易始于唐,興于宋,盛于明清,前后延續近千年。一方面,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歷代封建王朝通過控制茶馬互市,獲取了大量的戰馬,達到了“以茶馭番”、“羈縻”的效果,確立并穩固了對甘青川藏區人民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加強了其邊防防御能力。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視,它在中國多民族統一的封建國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對推動邊疆和中原經濟發展和各民族間文化交流,密切漢族與邊疆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維護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統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環海商都丹噶城
湟源民族貿易發端于清代在日月山所設互市,同蒙古、藏族茶馬交易開始。日后隨著規模不斷擴大和輻射范圍的拓展,則主要發揮了湟源自身所占據的地理和交通優勢。湟源地處湟水源頭,農區和牧區的接合部,“路通西藏,逼近青海”,是湟中羌道、唐蕃古道、絲綢輔道和青藏要道交通往來必經之地,地理位置和交通要沖是民族貿易賴以興盛的內在依托,清政府設立互市,又為地理和交通優勢轉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形成了環青海湖商貿大都市。
據史記載: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延續千年的茶馬互市宣告結束后,但并沒有影響湟源民族貿易的發展。湟源的民族貿易在嘉慶、道光年間,極為繁榮昌盛,西藏及環湖廣大牧區的羊毛、皮張、藥材、青鹽及硼、鉛、硫等礦產品,云集丹城,內地各省商客輻輳,來自京、津、山、陜、川、鄂等地的茶、糖、布、綢緞、瓷器等大宗商品也紛至輸來。每年入境的各類貨物金額達白銀120萬兩,還有來自省內和本縣的糧油、鐵木銅器、皮靴等各種生活用品,全年貿易總額達白銀250萬兩。其中:商品進貨總額中,蒙藏牧區進貨約占百分之六十,內地進貨約占百分之二十八,本地產品約占百分之十二;總銷售額中銷往牧區的占百分之十七,銷往內地約占百分之五十八,本地銷售占百分之二十五,比當時西寧的貿易總額超過六七倍。
據《丹噶爾歷史淵藪》記載:清末畜產品數量俱增,每年蒙古、藏地區運到湟源的馬400至500匹,牛5000至6000頭,羊2萬余只,各種野生動物皮4000至5000張之多。羊毛貿易興起,每年運進400余萬斤,總價值達40萬兩白銀。收購羊毛之商,不僅包括了上海、天津、北京、太原、西安等地商貿,還吸引美國、德國、俄國、英國等“洋行代辦”,故貨價蒸蒸日上。
茶糧源源不斷。進入湟源的糧食主要有大麥、小麥、青稞、豌豆。據記載,清末每年進市糧萬余石,每石銀價五兩至十五六兩不等;茶葉主要來自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甘肅等地,自蘭州運至,數量一萬封之多,大半轉銷蒙藏地區。
洋布打進市場。延至清末,湟源布匹市場又被“洋貨”占了大半,當時進洋布約5千匹。每匹以銀六兩算,共價3萬兩;土布輸市約1千卷,每卷銀25兩,共價2.5萬兩,此外還運銷羽紗、綢緞等不下百余匹,轉售蒙藏王公頭人。
名貴藥材大量上市。名貴藥材有鹿茸、麝香、大黃、甘草等,其中清末每年運往丹地的鹿茸角400余架,最多達1700余架,銀價高達9萬余兩。
手工制品頗受青睞。當時每年由山西運至湟源的鐵鍋1000余口,銀價1500余兩;江西景德鎮陶瓷龍碗頗受蒙藏牧民的青睞,故每年運進百余擔,銀價達6千兩。此外還有銅制鍋、罐、壺之類也予轉售,丹地生產的藏刀、陳醋、白酒、藏靴、牛毛帳房單子等質優價廉,運銷蒙藏及印度、尼泊爾等。
清后期以來,工商業發展較快,從事手工業的人數逐漸有所增加。湟源手工業號稱“8坊2院14匠”。8坊是粉、醋、掛面、豆腐、油磨、酒、煙、染坊;2院是制革的缸院、翻沙的爐院;主要工匠有銀匠、鐵匠、銅匠、石匠、木匠、靴匠、鞋匠、氈匠、皮匠、裁縫、口袋匠、褐匠、蠟匠、泥水匠等。光緒末年,從事工匠之師有四五百人,以資食者2千余人,占丹城總人口的50%左右。
又據《丹噶爾廳志》記載:藏貨,每年由西藏商上噶爾琫(商上即西藏“商上堪布”,是西藏地方管理財政商務機關。噶爾琫,為西藏的經商頭目)運至丹邑,共約千余包。其中氆氌居十之五,藏香居其二,藏經居其一(以金寫者,值最昂,每卷經有售銀五六百金至千余金者)。其余為棗、杏、花茜、紅花及各種藥材。其中惟藏香最著名,每束有售銀數兩者;銷售于湟源者,不及十之一。其余“即由藏客自行馱運,近赴西寧、塔爾寺,遠或徑赴北京、大庫倫各處銷售。”
據約在民國10年前后,西藏噶廈政府在湟源城關南城壕購置房產,供藏商居住,一處稱“郭巴院”,亦叫“公館院”,產權歸藏政府。一處稱“拉郎”,在西城壕,前后兩院,產權歸后藏,作為后藏來湟藏商住所。由于西藏商人來湟經商,即與當地商人接觸來往日繁,交情日深,丹地商人遂對西藏市場逐漸了解,因此,商界中出現了“藏客”這一新興行業,民族貿易又有了新的拓展。
湟源首批藏客,進藏時間約在民國10年(1921年),至民國25年(1936年),原國民政府監察院委員黎丹組成西藏巡禮團,前往拉薩考察時亦請他們結伴同行。上個世紀30年代,藏商隊伍逐漸擴大,一些富商眼看藏客生意興隆,獲利可觀,遂不避路途艱辛,長途跋涉之苦,躍躍欲試,以展雄圖。
藏客進藏時,采辦的主要商品是:以騾馬為大宗,其次是生活用品,有湟源陳醋、威遠燒酒、陜西紅棗、柿餅及景德鎮龍碗,還有少量槍支,名為自衛槍,領有護照,但至藏后,大部分作為商品出售。丹地至西藏行程約6000華里,行程近四個月,路途遙遠而艱難,途中騾馬及貨物損耗亦屬不小,但只要平安進入西藏,獲利也巨,以大宗騾馬為例,在湟源以白洋三百元購進的,到西藏只要顧主看中,可以賣到白洋一千五六百元;再如燒酒,每市斤約合白洋三角,而售價一盅(約二兩多)酒可賣白洋五元。酒、醋是用木筲包裝,待運至西藏,其消耗已在一半以上,但其利潤不謂不可觀。藏客返回時,運往內地的商品仍然以民族用品為主,如氆氌、藏香、經卷、金線、水獺皮、名貴藥材藏紅花、斜布(俗稱藏斜)、皮鞋等。上個世紀50年代以后,遂以手表為大宗,手表體積小,便于攜帶,以羅馬表為主,是50年代風靡一時的新鮮貨,獲利很厚。
返回時,由藏政府尕本宴請即將返回的湟源商人(包括青海各地的在藏商人),一是為了會面(尕本每三年一換);二是商定起程時間,一般是農歷九月從拉薩起程,年底抵湟;三是由尕本負責解決各商家的馱牛。議事結束后,由尕本帶領,在拉薩八角街舉行祭神儀式并騎馬環行八角街一周。宴請即告結束,按期起程。
解放前,湟源人到西藏做生意,深受藏人的喜愛和尊敬,藏人稱湟源人為“西令巴”,認為是佛祖宗喀巴的娘家人,頗受青睞,藏政府特別允許可在西藏購置房地產,辦理出境(如印度、尼泊爾)手續也及時方便。
以上所述明顯看出,在清代湟源民族貿易中,占主導地位的是農牧產品的交換。這種貿易的存在,對于保障從事單一游牧經濟的蒙藏民族來說無疑對生產、生活的正常進行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大量的畜產品、藥材進入湟源而集散內地,內地的日用百貨也大宗輸向湟源,也促進了中原腹地的經濟發展。正是這種互補互利起中介的湟源,由一片不毛之地一舉成為湟水上游環湖區域性的商業重鎮,發揮了青藏高原與內地經濟聯系、物資交流的樞紐作用,正由于此,環海商都之名遐邇聞名。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領事館在中國西北旅行》一書中無不驚嘆地寫道:“西寧丹噶爾(今湟源)是偉大的青海湖貿易中心,貿易如今達到非常大的規模”。《丹噶爾廳志》也一呼三嘆地寫道:“番貨云集,毫無他泄;山陜京津,商客輻輳;洋行歇家,日趨大盛。以收購羊毛、皮貨、茶葉、糧油為大宗,雜貨與之相乎,歲輸白金數十萬,盛矣”。
丹地美稱小北京
湟源民族貿易鼎盛時期被譽為蜚聲中外的“小北京”,標志性的代表就是丹城明清老街。
“老街原屬繁華地,商賈屯云百貨充;地扼海藏引萬貫,貿遷京津舞長風。”這首詩就是當時明清老街的真實寫照。明清老街,東西城門對開,一條相望,曰東大街、西大街。臨東城門北曰倉門街,南曰九間街。由東大街直西曰小什字。北曰北街,南曰南街。再西大什字,當協署西柵門口。再西,西小什字。北曰廟巷子,南曰燈山樓兒街。臨西城門北曰隍廟巷子,南曰西城壕。自西城壕中間一巷,直達東城壕之九間街,曰大巷道,與大街平行。再南,南城壕,寬闊平坦,東西通徹,城內之人恒于此處跑馬焉。有“北廟南街三道巷,大小什字二里長”之說。
據《丹噶爾歷史淵藪》記載:明清老街商鋪順序是:從北面看有世誠當鋪、馬億年藥店、蔡銀匠、張伯然雜貨鋪、于宣清布匹鋪、李道武銀匠鋪、王家鋪、李尊山皮毛店、董蠟匠、世宗山書店、洋行、廣泰藥店、鐵壽安平民醫院、陳醋房、忠信昌商號等。從南面順序是:王義三鋪、德興海、世誠當鋪、謝遷珍雜貨鋪、張建霖鋪、王子科藥店、李增華商號、同合堂藥店、李積堂布匹店、蘆宗武石板鋪、李美如布匹店、王壽伯鋪、李醋房、羅義興鋪、李發榮雜貨鋪、李家菜鋪、王仁肉鋪、德興成商號、張效武布匹店、富興奎商號、三興盛商號、王富山雜貨鋪、宋子新百貨店、胡二爺豆腐坊、馬進賢布匹店、歲生堂藥店、光世武布匹鋪、李富盛百貨店、劉玉厚照相館、京貨鋪、日州盛商號、杜星臣鋪、羅文甲鋪、吳瑞卿鋪、程興山鋪。城外豐盛街西有德興奎、恒慶棧、豐泰興、天泰興、濟元長、永盛恒、德合祥、信義和、泰源涌、德厚堂、德興和等商號。城外萬安街有:雜貨鋪、牛家百貨鋪、簡醋房、包家鋪、安家鋪、李家鋪、楊家斗行(糧食)、靳品山旅店、文盛合等。明清老街店鋪林立,密密麻麻、人頭攢動、摩肩接踵。
老街既是蒙藏牧民出入之門戶,又是全省皮毛的唯一集散地,牧民每年秋冬趕著牦牛、駱駝數百頭(峰),運來以羊毛為主的畜牧產品,抵老街后,就地露宿,人畜在城鎮上生活,在貿易方面有諸多不便。同時洋行和內地人初來乍到老街,對蒙藏語言一竅不通,開展業務困難重重,針對這種情況,當地手握資本、又精于蒙藏語言的商人以中間商身份出現,形成新興的“歇家”行業。據《丹噶爾廳志》記載:“僅領取官照的歇家就有48家之多”。所謂“歇家”,都是熟悉蒙古族、藏族的生活生產等情況,精通蒙藏牧民語言的為固定顧主,凡蒙藏牧民馱運來的羊毛、皮張等,除零星出售少許外,全部交給與己有聯系的“歇家”,再由“歇家”介紹出售于洋行或住莊客商,有的直接由“歇家”收購,“歇家”囤積居奇,按照市場的供求變化,適時拋出,賺取更大利潤。同時,以自己所掌握的物資,脅制外商,故洋行、山陜京津等客商,必須委托當地“歇家”,每年春夏先預付巨款或茶布糧食前往牧區預定皮毛,秋冬交回羊毛皮張,蒙藏牧民經“歇家”中介,將皮毛等銷售后,又托“歇家”買回自己所需的青稞、面粉、掛面、茶葉、饃饃、布匹等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有的由“歇家”直接供應,有的由“歇家”從市面買進后轉手賣給牧民。這樣,“歇家”在整個經營過程中,不僅是蒙藏牧民經商的代理人,又成為洋商貿易的代理人,還從洋行外商、蒙藏牧民兩方面賺取豐厚利潤,這就是“歇家”廣開門路、生財之道,如墜煙海。
由于市場繁榮,民貿發達,客商輻輳,貨物云集,所以各類經紀牙行業應運而生。直至民國初年,明清老街共有各類牙行十個,其中有羊毛秤行、斗面行、山貨過載行、水果行、魚行、青油行、煤炭行、牛羊牲畜行、騾馬行、裘皮行,各行業經紀人近40戶。諸如大宗成批交易的羊毛都須經由羊毛牙行居間介紹,尋求買主,評定等級,商議價格,成交后由牙行過秤結算,清結賬款。該行業組織形式健全,頗得買賣雙方的信任,全行設有固定辦理業務的地點,推行總負責一人,司秤、劃碼、記賬、結算等若干人,羊毛成交過秤中買賣雙方及牙行三方劃碼記賬,經核對無誤后,由牙行負責結算,按期收回貨款,收取傭金。對各經紀人在一個年度內,按傭金收入,分次預分給部分個人所得,年終結算后扣除各種稅費及行內公用經費外,余額部分按各經紀人應得分額進行分配。
各牙行因行業的不同特點,經營形式也有所不同,大致可分為兩大類經營形式:一類是設立店鋪,定點經營,如斗面行、魚行、山貨過載行、水果行、青油行等;一類是沿街市巡回、流動經營。在流動經營中,有的行業如羊毛秤行則定點辦公,統一集中流動。如煤炭、牛羊、騾馬、裘皮等行,各業主時合時分流動經營。老街貿易,十分火爆。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后,國際市場上羊毛、皮張緊缺,國內外商人合資經營的天津洋行,開始伸入湟源地區,以明清老街為據點,大量收購羊毛,先后來駐莊的外商有英商新泰興、仁記,美商平和、怡和、居里、瑞記,俄商美最斯、土商瓦利等八家。青海羊毛統稱西寧毛,西寧毛在國際市場上負有盛名,轉手之間,獲利很大,當時毛價由最初的每百市斤白銀三兩漲到三十至四十兩。豐厚的利潤,對省內外大商巨賈有著極大的吸引力。于是山陜、京津等地商人接踵而來。至民國初期,來湟駐莊的山西客商商號有瑞凝霞、德盛奎、恒慶棧、世誠當、日新盛五家;天津客商商號有天長仁、華北洋行兩家;西寧商號有泰源涌、德興旺、自立德、豐泰興、慶盛西、天泰興、永盛恒等。明清老街早已是環湖商都漢、回、蒙、藏民族物資交易的據點,當地巨商借地熟、人熟、行情熟的優勢,或開店坐地經營,或派員直接深入牧區收購皮毛,經濟實力已可左右市場,當時有名商號有萬盛奎、寶盛昌、福興源、順義興、德興誠、忠興昌、福興連等,每家資金有白銀十萬兩至四十萬兩。由于外商及內地商人多集中老街,他們由內地發貨也直抵湟源卸貨。故省內西寧等地商人亦來進貨,市場呈現一片繁榮景象。當時每年集散的牛羊毛總數約達四百萬斤以上,各類皮張三十多萬張。老街大、中、小商,及手工業者共達一千余戶。資金總額約在白銀五百萬兩以上,商務頻繁,每逢春節、元宵佳節,商店用彩布篷街,爆竹通宵。沿街吊燈排燈齊放光彩,火樹銀花。各路社火,順街演唱,笙簧悅耳,人人喜形于色,可謂極一時之盛。
民國13年(公元1924年),集散羊毛達500萬斤,各類皮張達30余萬張,大批皮毛、藥材等貨運抵天津,轉銷國外。各種“洋貨”及京津珍寶海味涌進湟源。民國15年(公元1926年),商民共約3000家。家給人足,物美價廉,市井繁榮,貿易昌盛,盛況空前。丹之人以商業謀生者過其半,商民生活奢侈,絲布、洋緞服者比比,中人之家海陸珍錯,如數家珍,跑馬風、宴席風、社交風、服飾風、娛樂風、建房風、祭祈風、崇文尚武,革故鼎新與北方大都市北京不銷幾分,由此而發展下來就形成了湟源上世紀初“小北京”的黃金時代,在國內外譽稱“小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