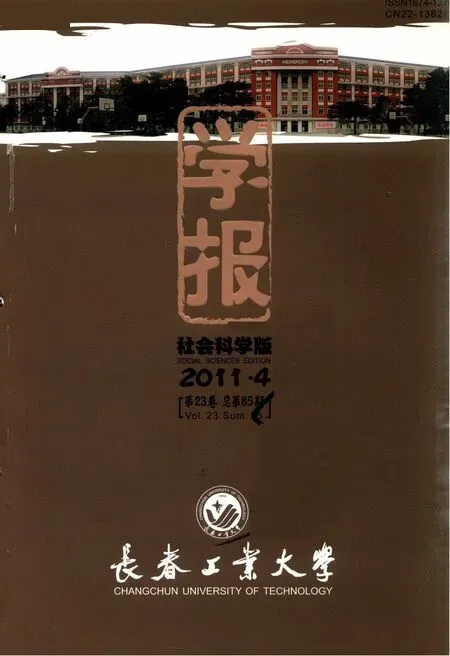先秦法家行政思想剖析
——商鞅與韓非行政思想之比較
楊福華唐冰開
(長春工業大學a.化工學院;b.政治與行政學院,吉林 長春130012)
先秦法家行政思想剖析
——商鞅與韓非行政思想之比較
楊福華a唐冰開b
(長春工業大學a.化工學院;b.政治與行政學院,吉林 長春130012)
商鞅和韓非雖然同為法家的代表人物,但其行政思想卻表現出諸多不同,這些不同表現在思想基礎、行政目的、行政理念等諸多方面。然而,他們從國家利益的高度來探討行政改革的必要性,規定政府職能轉變的取向,以及他們所提出的依法治國的理念對今天的行政改革依然具有積極意義。
法家;法治思想;以法為教
先秦時期是我國歷史上進入封建社會后首次出現的思想大繁榮時期,主要是指從西周開始至秦始皇統一天下期間的這段時間。在這段時間中各種學說、流派相繼出現,相互影響、交融,學術上總以諸子百家來形容這一時期著名的學說門派和著名的思想家。其中法家作為獨立的思想派別,對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對專制制度和專制國家的出現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其思想中蘊含的行政理念至今值得今人審視與學習。學術上對法家的研究均以商鞅與韓非這兩個法家代表人物為主,本文從行政思想研究的角度立意,對先秦法家行政思想即對商鞅與韓非的行政思想進行審視與分析,并采取比較研究方法,希望能清晰地展現法家行政思想的面貌。
一、理論基礎
法家行政思想來源于其政治思想的主張,顧名思義“法家”一詞已經足夠說明其行政思想的理論基礎何在,即以法為治國根本。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與韓非對法的理解自然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著不同的角度。
(一)思想前提
商鞅與韓非生活的時代十分接近,而且二者的思想主張均都在秦國被接受和奉行,在此不對兩位思想家所面臨的時代背景和時代精神進行過多的討論,單就他們的行政思想本身的主張進行研讀。在自己的學術選擇上,商鞅選擇了儒家“人性”觀的角度作為自己思想的出發點,以“人本好利”的人性假設為思想前提,他認為“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百姓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故曰:名利之所奏,則民道之。”[1]而韓非則是認同了道家對世界本體的主張,把“道”看成是其思想主張的出發點,韓非說:“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2]從此可以看出韓非的行政思想中,老子的“道”被借用來指稱是維護國家的根基,即“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3]可以看出同屬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與韓非二人對法的選擇是一致的,但倫理基礎的出發點卻有所不同。
(二)對法的理解
商鞅提出了“世事變而行道異”的主張,他這是以進化觀的眼光看歷史,認定“天地設而民生之”,“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既然世事在變,那么法也要改變,這也是他終生“變法”的根本動因。在他看來,所謂“世事變”,這是一個由“上世親親”、“中世上賢”到“下世貴貴”的合乎事理的演變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立禁”、“立官”、“立君”都是無可非議的,其內在要求就體現在“法治”統治秩序的建構方面。他的這番見解的提出,實際上是在為其變法尋求理論依據,也是他“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術,求使民之道”的理論深化。
韓非對法的理解更多的是橫向的,他沒有考慮法本身如何,而是偏重于法的應用,在學術界有人認為韓非的法治思想是術治主義,但韓非除了術的論述,還對勢進行了論述,并最終提出了“以法為本”,法、勢、術相結合的完整理論體系。韓非在認同商鞅的法治理念基礎上,對商鞅進行了批評,認為商鞅只講重法而不知用術,說“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雖勤飾于官,主無術于上之患也。”[4]由此可見,韓非對商鞅的重法主張是有所保留地予以承繼的。
二、行政目的
(一)商鞅變法的目的
商鞅變法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改變當時秦國的因循守舊,偏安積弱的狀況,希望變法圖強,實現秦國的“地廣國富,立威諸侯”的目的,所以可以肯定他的法治思想是從國家利益的高度來定位的,其政治目的就是要“變法”而“富國”。為此商鞅以行政改革為主旋律,最后形成政府治理的法制化,完成了他變法圖強的目的。司馬遷說他“相秦十年”,以孝公為后盾,兩度主持變法,可謂位高權重,得心應手;其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5]充分肯定了當時商鞅的變法功績。
(二)韓非法治的動機
韓非認同商鞅的法治理念的同時對其行政思想也進行了反思和批評。認為商鞅顧此失彼,只知道重法不知道用“術”,說:“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雖勤飾于宮,主無術于上之患也。”[5]由此可以看出,韓非法治思想的直接目的是維護君主的強權統治,其法、術、勢的理論主張都是出于“權術”與“權謀”的考量,從這可以看出韓非沒有擺脫封建貴族階級的束縛,其思想學說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以君主為核心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與商鞅這種以國家強盛為目的的行政思想相比顯得有些狹隘。
三、行政理念
(一)商鞅“政府治理法制化”的行政理念
商鞅的法治理念是以人本好利的人性預設為思想前提的。在商鞅看來,既然人性好利,那么,沒有制度,社會就必然混亂。因此,社會治理需要他律性制度的外部控制——“立禁”,既借助國家權威,建立官制,以法治的強制力對個人的行為實施嚴格的監控。據此可見,他所提出的“法任而國治”的主張,堅持的正是政府治理的法制化路線。
相對于自律而言,他律作為來自主體外部的規范和約束,是帶有外在強制性的。在商鞅看來“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1]他律本身還有一個有效性問題。即在某些情況下,人的好利本性又可能無視他律而使之對個人行為失去約束。因此法治的有效性要講究其合理性和權威性。因此商鞅強調制度和制法的制定要察,要慎。他認為法制的權威性首先要體現在對官吏的政治控制,他試圖通過限制官吏的自利性來強化其依法行政的意識。為此,他嚴格規定了官吏執法的紀律,例如“有不聽王令、范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6]“有敢剟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之類,目的就在于借助強硬的法禁措施對官吏的執法行為加以嚴厲的制約。
商鞅行政理念中的這種從嚴治吏意識,大概是出于對春秋以來“禮崩樂壞”政局的體察與思慮的結果。作為早期國家時期帶有松散聯盟性質的三代王朝的行政治理,其禮治模式盡管在周公執政的時期較好地發揮了政治效力,然而當諸侯國被允許擁有較大的政治自治權時,禮治就相當于一種“放松管制”,極容易從國家行政體制內部遭到嚴重的挑戰。所以,商鞅從嚴治吏以增強法制的有效性的設想,并不是由于心血來潮,而是基于對歷史教訓的深刻反思,這也正是他強化政府管制理路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其政府治理法制化的一個重要動因。
(二)韓非“政治與行政分離”的行政理念
韓非認為,君主與臣僚是不可能忠誠合作、共掌大權來治理國家的;君主與大臣“共國”,大臣往往因“重利”、“用私”而“譎主便私”,如果任其發展,極容易造成“主上卑而大臣重”、“主失勢而臣得國”的后果。因而他把君臣共權視為政治秩序的“公患”。順著韓非清理君臣關系的思路,他認為君主作為國家權力的最高執掌者,必須高度集權以維護獨尊的地位;而作為僚屬的官吏只能“賣智力”、盡心治政以獲取“爵祿”,“作為臣下,則決不允許私自討好民眾,與君主爭奪民心”[7](P310)。顯然,韓非的思慮已經涉及到了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問題。
韓非之所以傾向于主張政治與行政分離,是基于春秋戰國時期“權臣現象”后果的嚴重性。“四分公室”、“三家分晉”,都是典型。這類“權臣”謀私篡權,不僅破壞了正常的政治秩序,而且很容易引發社會動亂。就其實質而言,韓非堅持匡正君臣關系的用意在于求取一個獨立政治領域的純潔性,在于強調官吏系統在功能上應該是事務性的、非政治性的工具。也就是說,官吏的行為必須是匿名的,任何國策、政令的制訂與行政者個人無關。
基于此,從某種意義而言,韓非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全面闡述政治與行政關系問題的第一人,先秦儒家孔子著眼于以禮義忠信來規范君臣關系,孟子遵循道德高于權力的認識路線來審視君臣關系。荀子主張君主以誠心對待賢能之臣,樂兼聽,喜納諫,而前期法家人物慎到著眼于君臣關系的人性基礎,認為人性好利,君臣關系就是權力與利益的較量,是一種相互利用的關系,尤其強調”君無事,臣有事“的馭臣之術。韓非則集先秦法術家學說之大成,其關于君臣關系的思辨體現了一定的形式理性。他認為倘若忽視為君之道、為臣之禮,則易于混淆政治與行政的界線,最終將破壞既定的政治秩序。這種注重形式化的思辨理性,在先秦思想界崇尚實用理性的傳統中是一個珍貴的亮點。
四、歷史意義
(一)當時意義
法家的行政思想在春秋戰國的變革年代,由于商鞅執掌了秦國權柄所以能夠在實踐上給予貫徹實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收效,推動了當時社會的發展。商鞅的法治思想在秦國的實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其時代意義就在于他從國家利益的高度來探討行政改革的必要性,規定了政府職能轉變的取向,他曾明確的表述:“治國能摶民力而壹民務者,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8]在這里他實際上他把變法的目標定位在有利于國家富強的層面上。在一定程度上標明了商鞅變法理念順應了戰國時期國家管理職能的轉變需要。秦國的強盛及其吞并六國、一統天下,就是其行政思想貫徹落實的結果。然而,強秦“二世而亡”也與法家不重視仁義道德、不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一位地嚴刑峻法、不知攻守兼備、不愛惜民力等思想密切相關。
秦統一中國后,秦始皇根據韓非的中央集權理論開始強化國家機器。在中央,確立了一套為皇權服務的官僚體制,使皇帝總攬國家一切大權;在地方,廢除了所有的分封制諸侯國,將全國統一劃分為三十六個郡,每郡下設若干縣,皇帝直接掌握地方行政官的任免。皇權的加強和神化,郡縣制的全面推行,體現專制皇權的官僚機構和各種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完備和統一,皇帝對軍隊的控制的加強等等,這些就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主要內容。自此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正式確立起來,以后各朝各代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按照秦朝的這一體制承襲下來。這是功是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難以細說。
(二)現代意義
依法行政是現代行政思想的重要理論內容,我國現代社會正在積極的推進行政體制改革,依法行政是堅定不可動搖的原則。這一理念既有對現代西方行政思想的接納也有我國傳統法治思想的傳承,自秦國滅亡之后,儒、法、道三家漸趨融合,很難把“法”的思想獨立的加以思考,但先秦法家思想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學派,其行政主張自然融入到后世的行政管理理論和實踐當中,直到今天仍然在發揮影響。
[1]商鞅.商君書·算地[M].石磊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
[2]韓非子.韓非子·揚權[M].陳秉才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
[3]韓非子.韓非子·解老[M].陳秉才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
[4]韓非子.韓非子·定法[M].陳秉才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
[5]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2010.
[6]商鞅.商君書·定分[M].石磊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
[7].徐克謙.韓非子現代版[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商鞅.商君書·壹言[M].石磊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
楊福華(1969-),女,長春工業大學化工學院資料員,主要從事圖書資料管理研究;唐冰開(1969-),女,博士,長春工業大學吉林省人才測評研究中心主任,政治與行政學院副院長,教授,主要從事行政思想史,行政人才測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