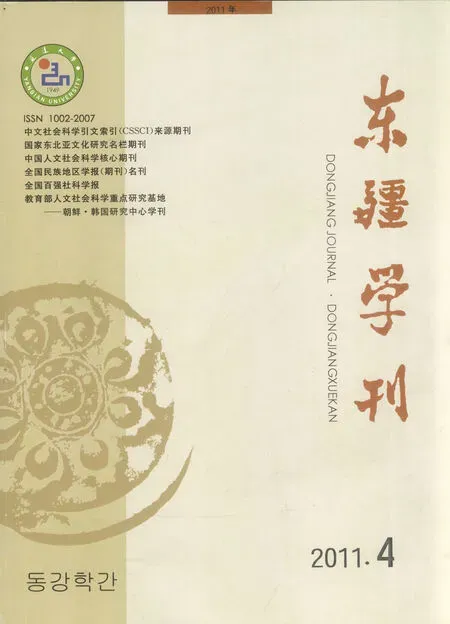法律身份的政治歧視對社會公平的影響
李壽榮
法律身份的政治歧視對社會公平的影響
李壽榮
法律身份的政治歧視是指法律通過對不同身份的人規定了不同的政治權利、政治資格、政治待遇或者對特殊政治主體的保護優于對其他主體的保護而不具有合理性的制度缺陷。身份性的政治歧視是社會不公的制度根源,它嚴重影響了社會公平的實現。因而,從三個方面提出剔除法律身份、消除政治歧視、實現政治平等、促進社會公平的措施:一是構建權利本位的法,以權利限制權力;二是規范國家權力,強化權力責任,轉變權力的身份意識,削弱政治身份在法律中的特殊性;三是從理性差別出發,確立合理的法律身份。
法律身份;政治歧視;社會公平
在人權發展史上,政治權利是把人作為政治動物并區別于其他自然動物而提出的第一代人權,這驗證了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是要過政治生活的動物”的正確性。政治性是人本質的社會屬性,沒有政治生活的人就是喪失了社會人格和社會尊嚴的自然動物。政治權利在不同國家的差異標識了不同國家國民的政治待遇和政權對人權的尊重程度,表現為一個國家社會公民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和博弈。公權力和私權利這一對關系的矛盾處理只有在法律的規定下似乎更加合理也更具有普遍性和執行力。法律中關于公民政治權利的表述是國家機關與社會公民在政治權力方面博弈的結果。當然,法律的優劣最終決定于這個國家的法律是如何產生和如何運行,因而也就與這個國家的政治權力的性質和民主程度有關。專制國家的法只是形式的法而不是實質的法,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相統一的法應該是在民主制度下產生的體現社會普遍意志的保護公民權利、限制國家權利的法。因此,從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正義性來研究法律身份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影響是研究政治公平的出發點和基礎。
一、法律身份的公平性取決于政治制度的民主文明程度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如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1](3)一個國家法律內容的正義程度如何直接與這個國家政治制度的性質有關,制度越民主越文明,法律也會越正義越理性。一般來說,不同的社會歷史形態決定了政治制度的性質,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政治制度與社會類型間并不絕對地存在著一一對應的關系,即使在很早以前的奴隸制社會也存在著今天一些民主國家不能與之相媲美的民主政治形式。如古希臘的民主制盡管是特定時期的曇花一現,但依然成為后人所津津樂道的政治佳話。
民主政治也許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比起專制政治有它的優越性,并且在歷史上也確實沒有出現過比民主政治更好更理性的政治形式。“民主政治之所以成為政治公正的制度安排,是通過其核心理念和原則體現出來的。一是人民主權思想;二是三權分立思想;三是代議制原則;四是普選制原則;五是多數裁定原則;民主政治還包括任期制、分權制、政治監督、法律監督、全民公決、彈劾和罷免等種種具體的實現形式。”[2](32)民主政治建立在一種所謂“多數決定少數”的理性邏輯之上,即多數人的正義觀總比少數人的正義觀更正義,多數人的智慧之和總能勝過少數人的智慧,多數人的合意總比少數人的專斷更理性,多數人的利益總要優先受到保護等。這種民主原則是一種功利性原則,雖然不是絕對地正義,但卻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權宜之計。民主體現了政治公正與平等,決定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列寧說:“民主意味著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3](257)因此,我們國家領導人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是強調社會主義政治應該是民主政治、多數人的政治,由民主政治所決定的社會主義法律也應該是民主的法律,是強調人人平等、公平正義的法律。
民主政治之所以是一種文明的政治制度,并且在目前條件下能夠盡量消除法律身份對社會公平的沖擊,是因為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政治人格的平等之上的,而強調政治人格的平等就必須反對法律身份的不平等。與傳統的專制政治制度下法律極力維護等級秩序的合理性不同,民主的法律提倡人天然是平等的,這種平等體現在政治上就是任何人都具有平等享有政治權利、參與政治活動的資格,盡管享受政治權利、參與政治活動的能力不一致。不可否認,我們每一個人并非具有平等的能力,也并不具有平等的條件,并不實際處于“無知之幕”中,我們對我們所處的現實差別非常清楚。但是如果因為上帝的不公平而繼續延續甚至人為地擴大這種不公平,人也就和動物沒多大的區別了。盡管弱者在自己的弱勢方面達不到強者所具備的能力,但他們希望如果得不到特殊保障的話,法律至少給予自己平等競爭的機會,并通過自己努力改善自己的命運,渴望法律至少將自己置于一個公平的環境中與他人賽跑,盡管這種機會并不一定能改變自己弱者的命運。對于強者,公平同樣是他們所希望的,因為一個人的強勢或弱勢只是相對而已,而且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未來的不確定性會使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被保護的對象。公平的規則在保護他人的同時也保護了自己,最終保護了不同地位的所有的人,因而也就成了每個人所希望維系社會活動的較好的法則。因此,我們希望通過政治制度的形式從根本上保障法律公平地分配政治權利,把法律身份理想化為一種職業的區分而不是成為不平等的被等級化了的身份標簽。法律身份唯一合理的存在就是非等級性和非歧視性,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制度設計的平等性和公平性。
二、法律身份的政治歧視及其表現
法律身份的政治歧視,指的是法律通過對具有不同身份的人規定了不同的政治權利,從而讓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享有某些政治特權而排斥其他身份的人享有這些待遇或給特殊身份的人的政治權利多于或優于其他的人,而不具有合理性的差別法律對待以及對特殊政治主體的保護優于對其他主體的保護而不具有合理性的差別法律對待。從絕對意義上講,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后,沒有哪個國家不是在實行法律政治歧視,因為法律規定始終把政權交給特定的強勢階級并嚴格禁止或限制其他階級掌握政權或參政,而且這些權力的傳遞一般具有身份繼承性。國家的階級性和人性的復雜性注定不可能實現全民民主、全民掌權。但是民主與專制的區別就在于掌握政權的少數人是社會選民普選產生的而不是自封的或世襲的,政權的行使具有代表性,即代表選民行使國家權力,而且即使是普選產生的個別人掌握政權,民主的政治也應該是向全民參政、議政和監督提供一個平等的平臺,即使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被民主的形式所掩蓋、否定而無法實現,也不應該剝奪少部分人參與政治、發表意見的資格。
身份性政治歧視不僅在古代社會大量存在,而且在新中國成立后相當一段時間內仍十分突出。李強教授用“政治分層”這一概念來闡述當時的身份性政治歧視現象。“政治分層是1949年以后中國社會的一種特有現象,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前,那時所謂政治分層是指根據人們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場、政治觀點,將人們分成高低不同的社會群體。例如,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革命干部、革命軍人等,這些都是政治地位比較高的群體;而地主、富農、資本家、反革命分子、右派等這些都是政治地位很低的群體。”[4](34)雖然在改革開放后,純名譽性的政治地位式的身份差別有所減弱,但身份的社會影響仍然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對省、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自治州,縣、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鄉、民族鄉、鎮的代表名額基數、代表總名額最高限度、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都規定了不同的標準,這是典型的以地域為身份標簽差別分配政治權利的法律規定。其實,城市與農村、大城市與小城市、上一級行政區劃和下一級行政區劃內的公民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他們參與政治權利的資格不應該差別對待,公平的分配名額應該是按照一個代表代表多少人或多少人當中選舉產生一個代表這樣的標準來確定名額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法律一方面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又為一些特殊身份的主體開了不受刑法管轄之門,如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的刑事責任不適用于刑事管轄原則。而且,刑法中有因主體不同而對其權利進行特殊保護的“身份犯”。(在此“身份犯”不同于刑法中的特殊主體的人犯罪,而是指為了特殊保護特殊身份主體的利益而對相同的犯罪行為進行不同量刑的犯罪)當然,刑法中的絕大多數“身份犯”是正義的差別對待,是為了限制特殊主體濫用權力而規定的,如對司法人員犯偽證罪、銷毀證據罪的從重處罰。但是在刑法中卻有因主體的身份不同而對其法益的保護也特殊保護的法律規定。如刑法第二百七十九條規定:“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招搖撞騙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搖撞騙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從重處罰。”欺騙的形式多種多樣,其共同點都是采用虛假的事實,但為什么同樣采用虛假的形式行騙卻會引起三種不同的法律處罰呢?一般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的警察三種不同的身份在刑法中出現了不同的保護,很明顯體現了法律身份的不平等性。法律中對政治性群體、權力性主體的特殊保護是政治制度不平等的體現,這種政治制度的不正義必然以強制的形式體現在法律中,并借助于通過政治權力的手段賦予標榜正義化身的法律來維護和“正當化”。用法律保護和強化政治身份,用法律壟斷和強化政治權力,用法律擴大和強化政治人與非政治人的差別待遇,這不正是法律的政治歧視嗎?這不正是政治歧視在法律中的體現嗎?
身份的政治歧視不僅僅體現在穩定的法律中,在一些臨時出臺的規劃、指令、政策、命令中更能體現區域性的、階段性的、階層性的、身份性的政治差別待遇,如不同地區地方權力的大小差別、不同地方政府對本行政區劃內居民政治待遇的差別等。而且在我們國家,雖然超過一半的人口在農村,但政策的傾向一直是向城市傾斜。這些地方性或行業性政策雖然不像法律那樣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但歧視性泛濫卻比法律更突出。況且在我國這樣一個行政權力范圍廣、勢力大的國家,行政決策往往比法律更具有強制性和效率性,政策的出臺也沒有法律那樣民主、規范,很可能是個別人或個別利益集團維護本集團利益的需要而抹殺大部分人的政治權力。法律雖然也存在政治性歧視,但這種歧視仍然是在“光明正大”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歧視,我們可以根據法律的穩定性能夠做到法律將對我如何的預期,因為我現在的身份和法律對此身份的規定是比較穩定的;而且只要身份相同的人法律也會一視同仁。但政策卻不同,政策就像普羅米修斯的臉,神秘莫測、變幻不定、說變就變。況且在我國,政策缺乏統一性、延續性、穩定性,不同的領導上臺有不同的政策,有時領導之間為了搞個人攻擊而相互否定對方的政策,政策的不穩定性給老百姓的生活增加了不確定感和不安全感。
法律和類法律的政治性差別對待如果缺乏合理性,這對和諧、公平、民主、秩序、發展是一個極大的威脅,我們一定要采取措施阻止這種不公平現象的繼續蔓延,改進法律制度,把每一個公民都當做平等的政治公民來對待。
三、法律身份的政治歧視影響了社會公平
許多學者注意到政治公平在社會公平中的重要地位。如黃秀華老師強調政治公平在社會公平實現中的價值核心地位,并提出“政治公平是現代社會民主政治的基礎和前提”;“政治公平是社會公平的核心調節器”;“政治公平是社會穩定的價值軸心”。[5](19~22)法律身份性的政治歧視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公平。首先,法律關于身份性的政治歧視剝奪了特定身份主體的政治權利。罪犯作為一個特殊身份的主體,他們的政治權利有些被法律明文地剝奪了,如剝奪政治權利本身即是一項剝奪他們政治權利的刑罰;有些被特殊的服刑環境而現實地剝奪了。在現實中,服刑人員既不能親自表達自己的政治愿望,也沒有代表他們表達自己政治愿望的人,他們是地地道道的既是作為沒有政治權利資格的人而被政治權利所遺忘的人,又是作為政治的敵人而要受到政治管制的人。罪犯也是人,作為社會的人,其政治權利是不應該被剝奪的,比如說選舉權、言論權等,盡管有些政治權利由于現實原因而不可能行使,但不應該對他們的資格進行剝奪,名義上的政治權利依然具有存在的必要,最起碼這種保留說明了我們的法律是對任何人平等的法律,是保障人權的法律而不是剝奪人權的法律。其次,法律身份性的政治歧視是社會歧視的根源。為什么社會對一個罪犯投以異樣的眼光,為什么有些罪犯服滿刑后走向社會很難找到工作,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法律身份的歧視性標簽已經烙印在社會人們的心里,人們像法律一樣對他們冷漠、無情和歧視。政治身份是一個人社會身份的標志,政治身份越高其社會身份也就越高,反之則社會身份就越低。因此,被剝奪政治權利的身份主體被社會已經世俗化地降格為權利缺失、劣跡斑斑的人,當然也就無法得到社會的公平對待。再次,法律身份性的政治歧視也使受歧視者在以后的生活中難以公平地得到其它社會資源的分配。有些政治歧視不僅僅代表了過去,還為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難以抹去的陰影。有些以檔案記錄的形式跟隨著受害者一輩子,在許多場合可能會舊賬重翻,比如說社會保障方面就會把有過政治劣跡或違法記錄的人予以排斥和拒絕,甚至連銀行貸款、商品交易、接受教育等方面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和排斥。
四、剔除法律身份,消除政治歧視,實現政治平等,促進社會公平
面對政治化、法律化、世俗化的身份歧視給社會造成的不公,我們該如何采取措施來消解甚至根除法律身份所帶來的政治不公呢?筆者提出了下列解決問題的思路以供參考。
(一)構建權利本位的法,以權利限制權力
一部法是良法或是惡法,其主要的區別在于它是以保障社會權利為主還是以保障國家權力為主,前者稱之為權利本位的法,后者稱之為權力本位或義務本位的法。法律語境下的不同身份主體對政治資源的特殊占有和對政治權利的特殊享受是政治權力特殊化、特權化甚至扭曲化的表現。這種政治不公平更多的原因是以政治資源特殊存在為前提的。“政治資源是指國民運用合法政治權力所能獲取和享用的政治待遇和政治機會,是政治權力的實施所取得的結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治資源的使用首先要服務于人們對自身福利的獲取、處置、追索和保護的全過程,是現代社會人們生存、發展所不可缺少的保障條件。”[6](68)國家只是一個抽象的存在,而社會是一個由一個個個體所組成的具體的實體性存在。國家存在必須以個體性存在為前提并且以個體性存在為目的因個體性存在而有意義。“雖說任何人都無一例外地是某個共同體的成員,但‘集體’只是一個中介,其存在應以組成它的‘個人’為核心和目的并為個人提供堅實的力量來更充分地享有和行使人權。”[7](88)作為保障個體權利的法律當然應該以社會權利為主,而法律中對國家權力的規定應該建立在“為權利服務”的宗旨之上并且應當受到社會權利的問責和限制,否則,一切將是本末倒置。以權利限制權力,具體可以表述為以權利限制對抗權力、以私權限制對抗公權、以社會權限制對抗國家權等。
(二)規范國家權力,強化權力責任,轉變權力的身份意識,削弱政治身份在法律中的特殊性
政治身份無疑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身份,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國家以法律的形式賦予了享有者一定的政治和非政治特權,它可以堂而皇之、理所當然地行使其他社會主體所不享有的權利,這種權利不一定是天賦權利但更甚于“天賦權利”,不一定是理性使然但以“理性”的形式道貌岸然地表現出來。因此,政治權力以“合法”的外衣進行“非法”侵害的事件在歷史上比比皆是,以權威者甚至家長式的形式任意發號施令或強制侵權的事件在現實中屢屢發生。我們在此不必追問賦予這種身份和權力的法律是否理性、民主,即使是最民主最正義的法律所賦予特定身份主體的權力如果沒有相應有效的約束和限制,都會出現權力濫用、權力腐敗的現象。因此,要使權力不會發生法律之外的異化,就得使法律在賦予權力主體以權力的同時規定其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強化權力者的責任意識,在觀念上削弱其身份意識的特殊性和優越感而增強身份主體的一般性和服務意識。這樣,不僅限制了權力的濫用,而且也使社會其他主體具有和權力主體平等的意識,不再畏懼權力或權力主體,最終使全社會普遍認為,權力主體或國家機關不過是像超市里的服務員一樣是社會顧客的服務者,他們身上不具有對顧客更多要求的權利而是承擔著對顧客更多的義務和責任。對權力主體而言,要充當好服務員的角色,他們當然要增強服務意識和責任義務觀念,降低對自己特殊身份優越感的認同。甚至認為自己不過是充當社會公眾的仆人而已。例如,我們該如何看待公務員這一特殊的身份,是從權力的掌控者還是從社會服務者的角度去看待,這不僅是一個權利義務責任如何分配的問題,也是一個主體意識和社會觀念的問題。“公務員”這樣的稱謂我們應當從職業的角度去定位而不應從身份的角度去理解。公務員是一種職業,一種拿著公共資源為人民服務的職業,從理論上講是人民所信賴的被人民推上崗位為人民謀福利或實行社會管理的職業,他們拿著穩定的高出一般人水準的薪酬,過著比一般人富裕的生活,理應履行比一般人更多的義務,遵守比一般人更高的職業要求。他們不必貪,因為工資足以養活自己和家人;也不該貪,因為他們是國家和人民所信任的人,而且手中掌握的是社會的公共資源而不是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私有資源。當然,現在事實上所看到的是貪污橫行、腐敗叢生,其原因就是如果沒有制度的約束,其不必貪和不該貪都是軟弱的說教。制度性法律性的約束才是真正做到不能貪的關鍵。健全的法律制度會使你想貪但沒有路徑、渠道、辦法,只能是望貪而興嘆,徒勞而無功。因此,就如以制度賦予特權一樣也需要以制度設置特殊義務、特殊責任,不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規范權力、根除腐敗的關鍵。
傳統權力身份的優越性意識增強了權力主體的特權專橫,拉開或拉大了權力主體與普通公眾身份差別的距離,導致了社會歧視的社會化和身份矛盾的尖銳化,從而踐踏了社會公平,損害了社會和諧。當官者不僅在權力、經濟、地位等方面具有特權,而且就連日常生活、走路、服飾、日常用品、婚姻選擇等方面與普通百姓都有嚴格的區別,普通人見了當官的要回避或跪拜,士農工商等級森嚴、身份有別,更甚的是這種身份的不平等影響還會在子孫后輩身上遺傳。今天,我們倡導人權、倡導人人平等,而要實現這些,需要全社會有一個人格平等的共識并付諸于消除歧視、消除身份差別的社會行動,這其中需要國家政治的導向作用和權力主體的帶頭作用。
(三)從理性差別出發,確立合理的法律身份
“身份”一詞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在無歧視的語境下使用,譬如,當說到一個人有幾種身份,如社會身份、家庭身份、職業身份等時并不包含歧視或不平等的意思,而是指一個人在不同的環境或職業中所承擔的不同的社會角色。這時的“身份”就是為了避免一個人所具有的多重角色間相混淆而有必要進行的角色區分。在現行法律中,也確實存在著規定父母子女、夫妻之間等有關權利義務不對等的身份法。身份法是進行子女撫養、監護、父母贍養、遺產繼承、承擔特定基于身份關系的法律義務和享有法律權利的必要的法律規定,它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就在于非歧視性。而且,社會的分工只能使一個人擔任一種或少數幾種重要的社會角色,每種社會角色也只能由能夠勝任它的部分人擔任,政治權利的分配也不例外。“每種政治體系都必定通過某種方式選用人員在政治結構中擔任各種角色。當專門的社會角色出現后,即使在愛斯基摩人村落那種僅有祭司和首領角色的非常簡單的結構中,也必定會有某種方式來選擇特殊的人擔任這類職務,并要求他們按照所期望的方式行事”[8](127)概括地講,不管法律中有沒有身份規定,不管法律中有多少身份規定,也不管以后法律對身份如何規定,法律身份的存在一定要建立在合理的基礎之上,這種合理性具體表述為平等性、非歧視性、對所有人的有利性。合理的身份必須是平等地對所有人開發,給所有人提供了平等和選擇的機會。就如權力是對所有人平等地開放,即錄用程序的公平,但最終只能由一部分人所擁有一樣,這種只能由一部分人擁有的政治權力之所以是正義的,是因為它的錄用前提是公平的。因為這種身份具有平等性和開放性,所以也就具有了非歧視性。法律對特定的主體賦予更多的權利或規定更多的義務是為了公平而不是為了歧視,是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不是對個別人的利益,因而這種身份也就具有了公平性和合理性。
平等并不意味著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完全相同,完全相同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正義的。讓弱勢群體享有更大的生存或生活保障權其實就是為了實現更大的公平,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公平的最高境界就是整體的公平感、正義感和安全感,一個人的未來具有很大的不可預知性,人人都有可能成為弱勢群體,就如人人都有走向死亡的一天一樣,每個人都有可能因遭遇疾病、車禍等天災或人禍而由強者轉變為弱者,每個人在自然面前非常渺小就如個人在整體面前非常渺小一樣。但自然是自為的而社會是人為的,社會可以借助集體的力量保護每一個人而最終保護所有的人。如果在任何人遭遇災難時能得到集體的、大多數人的幫助,每個人對未來都會充滿希望,對他人心存感激,對國家抱有信心。因此,對弱勢群體的特權就是對每個人的特權,對弱勢群體的關愛就是對每個人的關愛,對弱勢群體的特殊對待也是對每一個人的特殊對待,這是社會的最大平等也是最大公平。
就如對弱勢群體的特殊保護是建立在合理基礎之上一樣,對特殊人的特殊義務也應建立在合理的基礎之上,如官員的責任、軍人的責任等。他們背負了一般人所不背負的責任,這是合理的,因為它們的失職或犯罪將會使大多數人甚至所有的人遭遇災難和痛苦。公務員收入公開甚至家庭成員也要曬賬本在西方國家已經成為慣例,但在我國依然是社會要求、民眾呼吁但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避、推辭甚至以“特殊國情”作辯解。每種職業都有自己特殊的職責,這種職責是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表現,你能做甚至只有你才有這樣的特權做,這是你的權利;你必須做,并且嚴格按照規定做而不能懈怠或瀆職,否則就會追究其責任,這是你的義務,這種特有的權利和特有的義務不是不公平的,而是出于職業的特殊性而設置的合理要求。當然,你可以選擇不去從事某一職業,但如果你選擇了上崗你也就選擇了服從這種職業所規定的特殊義務。
總之,我們過多地在其它領域內大談特談公平、正義,但對這些問題的根即政治制度的公平問題缺乏系統的研究。政治權利是政治動物的第一權利,正如生存權利是自然動物的天賦權利一樣。社會歧視的根源在于政治不公,而政治不公的根源是等級性的身份制度,法律以制度化的形式把人劃分為三六九等式的政治不公是社會不公的禍根,因此,我們要消除歧視性法律身份,倡導政治民主、政治公平,從源頭上為實現社會公平而努力奮斗。
[1][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2]霍秀媚:《制度公正與民主政治》,《探求》,2003年第2期。
[3][蘇]列寧:《列寧選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4]李強:《政治分層與經濟分層》,《社會學研究》,1997年第4期。
[5]黃秀華:《政治公平在社會公平實現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論探討》,2008年第2期。
[6]何深思:《論我國政治資源的公平分配與合理共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5年第2期。
[7]韓經超:《國家政治公正視角下的人權發展》,《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
[8][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
D922
A
1002-2007(2011)04-0072-06
2010-08-20
河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法律身份的公平研究”,項目編號:S2010104。
李壽榮,男,北華航天工業學院文法系講師,研究方向為法理學。(廊坊065000)
[責任編輯 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