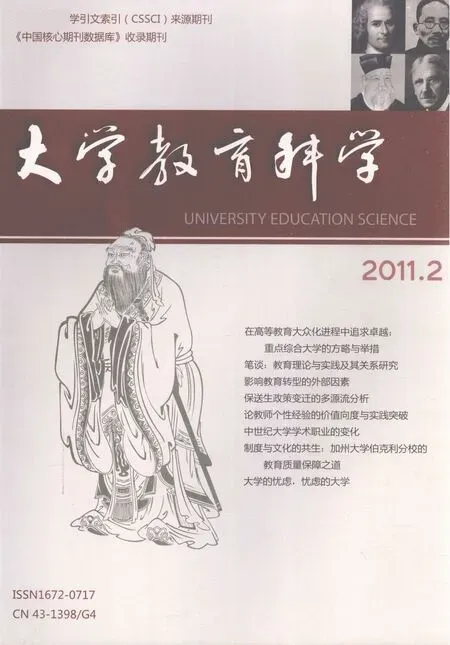以教師為主導:搭建農村終身學習“立交橋”*
唐松林,朱菲菲,唐麗玲
(1.湖南大學 教育科學研究院,湖南 長沙 410082;2.湖南大學 金融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以教師為主導:搭建農村終身學習“立交橋”*
唐松林1,朱菲菲1,唐麗玲2
(1.湖南大學 教育科學研究院,湖南 長沙 410082;2.湖南大學 金融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農村教師在傳承鄉土文化、捍衛鄉村精神獨立、建設鄉村民主等方面,可謂舉足輕重。搭建農村終身學習“立交橋”是克服農村知識貧困的根本出路。農村教師是農村終身學習“立交橋”的核心力量。教學社區是農村終身學習“立交橋”的組織形式。
農村教師;終身學習;教學社區
我國農村之地廣博深厚,承載了幾千年豐饒的華夏文明,是中華大舞臺的主角。然而,“世界市場對個人消費和生活方式日益增長的影響,不斷增長的地理流動性,以及人們的信仰與全球信仰相聯系[1](P155)”等事實日漸侵襲農村骨髓,鄉土文明顯現了徐徐蠶食之像,變成了“與生活在其中的人群的不相關者,民族性正在走向衰落”[1](P156)。與此同時,在農村的各種教育資源(如科研機構、圖書館、博物館等)與城市的相比,存在很大差距的現狀之下,農村教師比城市教師更多地承擔了知識分子的責任,他們在傳承鄉土文化、捍衛鄉村精神獨立,建設鄉村民主等方面,可謂舉足輕重。如何以鄉村教師為主導,搭建終身學習“立交橋”[2],使農民成為新型的知識勞動者,由此提高生產效率,改變農村社會結構,左右人們生活質量,提升農村文化精神面貌,是當前農村面臨的最大挑戰。
一、終身學習“立交橋”:克服農村知識貧困的根本出路
美國當代社會學者山龍在其《閱讀貧困》中分析西方社會貧困時指出:“扶貧包含著某種政治意識,扶貧的概念與方式是體現這種政治意識的,貧困個體或家庭在政府的每一次扶貧行動中,其生活不是出現轉機而是出現惡化,并且這種惡化是伴隨各種機構的扶貧行動出現的,這些行動幾乎沒有使貧困者真正走向開發自我潛力與自身創造財富的正途。”[3](P54)“從某種意義上說,窮人沒有拋棄經濟,而是經濟拋棄了窮人,政府與機構提供了許多機會,雖然這些機會足以讓窮人達到中產階級收入水平,但是窮人卻缺乏獲取這些機會的能力”[3](P67)。山龍這里揭示了兩個普遍性問題:一是過去關于扶貧的概念與方式大多是體現某種政治意識或是政治需要,在解決貧困的具體措施上選擇了經濟補償策略,沒有從根本上從長遠上解決貧困問題。某些人在追求政治績效與經濟 GDP的功利情緒中,更多地選擇了投機主義與形式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思考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導致農村貧困的根源;二是在解決經濟貧困的制度安排中,表面上看,雖然在形式上體現了機會上的平等,即所有的機會與價值面向了包括貧困地區在內的所有人群,但是,窮人卻因出身的差別(包括后天環境、文化傳統與經濟地理的差別),缺乏獲取這些機會的能力。所以,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對窮人表示了極大的憐憫之心,為了平等地對待所有人,提高真正同等的機會,社會必須堅持“博愛、補償與互惠”原則,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賦較低和出生于較不利的社會地位的人群。
我們看到今天的中國,對于農村與城市的不均衡,更多地是采取經濟補償策略。這雖然對農民的經濟生活與國民的社會心理有一定積極意義,但從城鄉貧富差距來看,各種扶貧政策與措施似乎杯水車薪,未能使情況有根本改變,甚至使人們始料未及的是,城鄉貧富懸殊因制度變遷而越發嚴重。人力資本理論早就揭示,貧困者之所以收入低下,根本原因在于他們缺乏對人類基本知識、能力和權利的認識和擁有。這就是說,農村貧困的根源是知識與能力的貧困,及其對擁有知識的能力和權力的意識。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斷言:“改善窮人福利的決定性生產要素不是空間、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質量的改善和知識的增進。”[4]世界銀行1998年題為《知識促進發展》的年度報告認為,落后國家要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知識差距,就必須有效地提升獲取知識、吸收知識和交流知識的能力。“窮國區別于富國、窮人區別于富人,不僅由于缺少資金,更由于缺少知識”[5]。因此,“現存社會分層的一個重要準線是社會成員所接受教育水平的有與無、高與低。接受教育時間越長、接受教育的等級越高,則一個人或一個人群在社會層級結構中所據的地位就越高,因為現代社會中個人或群體所能夠掌握的各種社會資源(如發展機會、資信占有、相當收入與相當職位等)的能力與受教育水平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比關系”[6]。因此,從某種意義而言,知識貧困是導致農村經濟貧困的決定性因素。
終身學習是擴展人的知識,提高人的能力,消除貧困的工具。《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搭建終身學習“立交橋”,構建體系完備的終身教育,促進各級各類教育縱向銜接、橫向溝通,提供多次選擇機會,滿足個人多樣化的學習和發展需要,促進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學有所成,學有所用[2]。由此可以證明,終身學習“立交橋”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獲得了廣泛認可,并且已經納入國家教育決策的宏觀視野,它正在成為一種新興的教育形式,代表我國教育的變革和發展方向,是推動教育與社會、教育與社區有機結合、協調發展的基本途徑和有效手段,是發展終身教育、建設學習型社會的切入點和有效載體。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一個以全民學習、終身學習和學習型社會為基本標志的現代社區教育,正在取代工業社會時代的制度形態的現代學校教育。它承認杜威所倡導的“以民主的理念為共同的明確生活意識”的觀念,有別于實利主義和權力主義,“目的是發展社會的態度和敏感性,他們希望創造最小的社區和團體方案,在這一學習型社區中,學習者可以分享興趣,尊重多元化,追求共同目標,并參與重要社會議題和非正式討論”[7]。它為現代農民提供基本知識、能力和權力,農民在共同學習與群體互動中,不僅形成反思的實踐的經驗系統,形成現代農業科學知識技能,而且明確共同解決問題的責任、義務與意識,從而探尋擺脫貧困的必要手段與行動策略,以此提供在貧困環境中人的發展機會,促進農民的事業成就與人生幸福。
二、農村教師:農村終身學習“立交橋”的核心力量
農村教師自古以來便是農村地區的知識分子,不僅向學生“傳道、授業、解惑”,還開啟民智,反思社會,傳承文明。《呂氏春秋·尊師》中說:“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圣,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古往今來,無論在民間還是官場,幾乎一直存在一個共識,那就是,教師的社會地位與國家存廢、民族盛衰密切關聯。農村教師是作為農村知識分子的代表,不是單純的知識傳播者,也是農村經濟社會與鄉土文明發展的精神動力。他們除了身負教書育人的職責之外,還有建設鄉村社會的擔當,斷不能“獨善其身”,置身于新農村建設之外,不說“兼濟天下”,至少要肩負農村這重要一隅,站在知識分子的角度對鄉村文化和現狀進行反思、批判和指引。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說,“大家以為先國家好,才得農村好,這實在是種顛倒見解。其實要農村興盛,全個社會才能興盛;農村得到安寧,全個社會才能真安寧。設或沒有農村的新生命,中國也就不能有新生命,我們只能從農村的新生命里來求中國的新生命,卻不能希望從中國的新生命里來要求農村的新生命”[8]。
但當今農村社會,農村教師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很多教師僅從個人利益、學校利益出發,無視農村建設的大局,缺乏對鄉村教育及鄉村文化的反思及批判精神,誤入了一條單一的知識傳播的教育道路:不僅離終身學習、全民學習和學習型社會十分遙遠,而且背離了農村教育“在農”、“為農”、“興農”的軌道,使農村社會缺乏學習的根基,無法培養出振興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人才。農村學生疏遠了他們自己的土地,并感覺在農村自身智力和物質方面的抱負難有實現的可能。同時,城市人則掌握了教育的主動權利,使農村教育處于被動地位,并淪入追趕城市教育的艱辛旅程,這無疑是一種知識暴力。皮特·泰羅尖銳地批判現代教師與社會脫離的現實,“雖然他們(教師)具有專家的能量,但是他們一直是局外人”[9](P359)。這一敘述也適合當前我國農村教師與農村社會的關系——農村教師受到升學主義與證書主義的強烈束縛,他們身處農村卻做著與農村不相關的事情,脫離了農村經濟與文化的基礎與傳統。《禮記·學記》中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也”。農村教師如果缺乏與農村環境的互動關系,如果忽視自己與農民合作的集體智慧,就使自己缺乏智慧的源泉與發展的根基,從而也使農村社會發展缺乏知識動力與精神支撐。因此,農村教師之于農村,已經不是傳統意義的教書匠角色,我們應該看到農村教師的公共性和社會責任。她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及農民生活息息相關,為那里創造財富,開創文明之先進風氣,及時表達政府意愿與黨的政策,增強民族自信心與凝聚力,塑造一種新的農村精神。
在農村實現終身學習,必須重新喚醒農村教師的公共意識,實現現代知識與鄉土社會的聯結。當前農村教育表現出來的“離農”、“背農”問題,不能說和現在的農村教師毫無關聯。皮特·泰羅在論述美國大學教師與社區的關系時說道:“我們應該相信鱷魚在水中的力量。”[9](P358)。教師離開農村環境,就如同鱷魚離開了水,他們的力量難以發揮。這是因為,文化是一張由自己編制的意義之網,在西方式的現代知識體系之外,還存在著各種各樣從未走上過課本和詞典的本土文化知識。農村教師只有堅守地方性知識,去發現個人和族群的獨有精神品性,從儀式的象征解釋中去把握特定社會秩序的再生產,才能真正實現自身價值與社會意義。教師應該在“為社會應該做什么,為學生應該做什么”等方面進行反思,正確引導學生成長,在不斷向城市輸送優秀智力資源的同時,也要注重培養新農村建設的創新型勞動者。尤為重要的是,要“培養農村學生熱愛家鄉、服務家鄉的意識,使他們即使走出這塊土地,也魂牽夢繞這塊土地,為改造這塊土地出謀劃策,出錢出力;使沒有走出這塊土地的人也能安心地扎根奉獻于此”[10]。這是一個農村教師最重要的職責,也是農村教師作為農村主要知識分子的良知。
三、教學社區:農村終身學習“立交橋”的組織形式
教學社區是以鄉村教師為主導,以農村學校為基地,包括家庭、社區內公共機構等共同參與的終身學習組織形式;是一種具有自由、生活、對話、互惠、開放與合作等特征的最基本的終身學習模型;是社區全體成員共同學習、交流、相互團結的場所和各種科技與文化信息的聯絡中心。其職能主要是整合普通教育、農民教育與繼續教育,擴大社區中人與人的交流,提倡農村高尚娛樂,激發村民求知欲望與致富思維等等。在這里,既可以充分利用學校與鄉土文化資源,傳承鄉土文明,保護民族歷史文化特色;又可以提供以衛星、電視和互聯網等為載體的遠程開放繼續教育及公共服務平臺,促進現代文明與本土文明的聯結與融合。總之,它為學習者提供自由、方便、靈活、個性化的學習條件;它不僅依靠農村學校的力量,而且需要家庭以及村落團體分工合作,協同共進,促進新農村建設的多個目標的實現。教學社區在農村的建立,不只是一個純粹的行政命令下的按部就班的理性程序,而是取決于現代文明與鄉土文明深刻的互融與對話才能實現的。它需要激發農村教師的知識分子的引導作用,使農村教師與農民的互動對話,達到精神的融通,然后才能有效行動。
教學社區的形成,需要強化農村教師對農村文化的身份認同,即需要農村教師重新認識自身與農村所有成員之間的相互責任與義務關系,及與其在文化、心理、民族性上實現真正的心理認同與精神融洽。正如當代英國政治哲學家米勒所說的:“民族不是被身體特征或文化特征區分開來的人的集合體,而是依賴于相互承認的共同體”[1](P23)。“它的存在依賴于其成員彼此歸屬并希望繼續一起共同生活的共同信念。”[1](P23)這就是說,農村教學社區實質上是一個生活信念、社會正義與對他人義務的共同體。在這里,農村教師、學生家長與社會工作人員承認有義務滿足彼此之間的要求,保護彼此之間的基本利益;在這里,教育對象與受教育對象均已擴大,學習內容在傳承傳統文明中不斷豐富創新,學習方法呈現為日常生活、學習與勞動一體化的混沌內容,學習者在對話、反思、體驗與實踐中完善自我。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說,“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學生、先生也可以更多起來,因為在這樣的辦法下,不論校內校外的人,都可以做師生的”[11]。所以,“教育并不僅僅存在于課本、教室以及學校這一狹窄的空間之中”[12]。它關注周圍的變化,時代的發展,推動人與社會協調發展。總之,教師是教學社區的主導者,學校是教學社區文化的中心。
為何要建立一種農村學校、家庭與社區內公共機構一體化的教學社區?這是因為,教學社區作為農村終身學習“立交橋”的組織形式,不是一種強制性的理想,而是一種自生自然的生活形式。農村教師由于其“土生土長”的特質,他們與鄉土及那里的人群有著深厚的連自己也不知道的、根深蒂固的情結或依戀。這種依戀的情結既沒有理智的依據,也很少利害關系,它使自己與鄉土文化混為一體。正如羅曼·羅蘭所描述的那樣,“羈糜人心的乃是從上智到下愚都有的一種潛在的、強有力的感覺,覺得自己幾百年來成了這塊土地的一分子,生活著這土地的生活,呼吸著這土地的氣息,聽到它的心跟自己的心在一起跳動,象兩個睡在一張床上的人,感覺到它不可捉摸的顫抖,體會到它寒暑旦夕,陰晴晝晦的變化,以及萬物的動靜身息。而且用不著景色最秀美或生活最舒服的鄉土,才能抓著人心;便是最樸實、最寒素的地方,跟你的心說著體貼親密的話的,也有同樣的魔力”[12]。所以,讓學校教育回歸自生自然的生活狀態,可以讓教師、學生、家長與社區工作人員在那或引人入勝或單調沉悶的空氣中,在那或許平淡無奇卻一切都令你割舍不得的土地之中,共同體驗與創造那種鄉土文化自有的魅力和深沉的甜美。
雖然說教學社區是一種自生自然的生活形式,但它作為一種非個人的共同體,就必須承擔一定的責任,履行一定的社會義務。由此,它應該遵循一定的理性原則,生成一定的學習制度,形成教學社區的基本結構,否則,教學社區只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烏托邦。筆者在此拋磚引玉,提出關于教學社區的如下理性原則,以期引起大家對教學社區的理性思考:一是面向大眾。教學社區作為農村終身學習“立交橋”的重要特征在于學校是沒有圍墻的,課堂是一種開放課堂。在教育對象上,不應僅僅局限于學校學生,還包括所有農民。通過社區成員的“學習小組或集體協力加強整體性與相互聯系,以便加深我們對事物的理解,使個體間的智慧達到進一步的凝聚,進而達到更高層次的整體性和密切聯系,形成共同創造的能力”[14]。二是基于鄉土。農村教育要與城市文明平等對話,不能一味復制模仿,要聯系農村特有的歷史文化優勢,注重傳承農村獨特的風俗習慣,形成獨特的鄉土文明。這是農村終身學習的原動力與基礎。三是關照實用。致富是農民的根本目標訴求,教學社區要千方百計地了解與滿足農民需要,使他們獲得許多人生實用知識、致富的方法和道德行為的訓練,使教育跟著農民致富方法走。這就需要教學社區充分利用農村教育資源,為農民提供多樣的、實用的農業科技、動物飼養、家政實務等方面的知識。同時,要集思廣益,在集體智慧的交流碰撞中,尋找改良促進農村建設的新道路。四是共享經驗。教學社區的教學過程,也是教師、家長、學生與農民之間的交流、對話與互動過程。他們在活動中互為榜樣,互相暗示,相互激勵,自我體驗,共同發展。
[1][英]戴維·米勒.論民族性[M].劉曙輝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2]教育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EB/OL].www.gov.cn/2010-07-29.
[3]Patrick Shannon,Reading Poverty.Heinemann Portsmouth,NH.1998.
[4]葉茂林.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7.
[5]胡鞍鋼.知識與發展:21世紀新追趕戰略[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2.
[6]陳振明.政策科學——公共政策分析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60.
[7]項亞光.營造學習型社區教育策略和規劃探析[J].外國中小學教育,2006(10):12.
[8]馬秋帆.梁漱溟教育論著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7.
[9]Peter Taylor.Where crocodiles find their power:learning and teaching participation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Vol 43 NO 3 July 2008.
[10]俞曉婷.“為農”的農村教師角色內涵及實踐[J].現代教育管理,2009(9):65.
[11]徐明聰.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M].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9:58.
[12]傅書紅.文化研究在教育領域中的價值——亨利·吉魯的文化研究教育思想[J].比較教育研究,2007(4):36.
[13][法]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M].傅雷譯.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679.
[14]甘永成,祝智庭.虛擬學習社區知識建構和集體智慧發展的學習框架[J].中國電化教育,2006(05):27.
Take the Teacher as the Leading Factor:Building the Multi-Level Crossing Bridge of Lifelong Learning in the Countryside
TANG Song-lin,ZHU Fei-fei,TANG Li-ling
(1.School of Education,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2,China;2.School of Finance,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2,China)
The rural teach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heriting the local culture,guarding the village independent spirit,and constructing the village democracy and so on.The lack of knowledge in the countryside can be eliminat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level crossing bridge of lifelong learning.And the building processing needs the countryside teachers as its key forces,and needs the teaching-learning community as the organization form.
rural teacher;lifelong learning;teaching-learning community
G656
A
1672-0717(2011)02-0064-05
(責任編輯 黃建新)
2011-02-20
全國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重點項目“鄉村教師為主導的村落學習型組織研究”(DFA070175);湖南省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重點項目“以學校組織社會:村落學習型組織研究”(XJ K05AZ008)
唐松林(1962-),男,湖南澧縣人,教育學博士,湖南大學教授,主要從事教育哲學與教師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