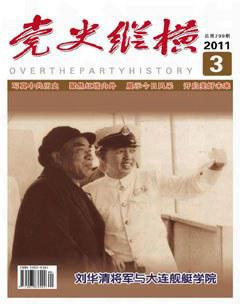革命老人陶承和她的家人
楊鑫潔
陶承(1893—1986)女,湖南長沙人。1927年參與革命,先后在長沙、上海、重慶、延安等地我黨的重要部門里負責掩護工作,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先后任職于政務院、內務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著有《祝福青年一代》、《我的一家》等,其中《我的一家》被改編成電影《革命家庭》。陶承一家為我黨的革命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她的丈夫歐陽梅生和兒子歐陽立安、歐陽稚鶴先后壯烈犧牲,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了對黨許下的忠誠諾言。
陶承是個孤兒,1911年由干娘做主嫁給了體弱多病的歐陽梅生,歐陽梅生也是孤兒,比陶承還小一歲,當時正在長沙第一師范讀書。夫婦倆生活比較清苦,歐陽梅生雖然在外教書,但收入微薄,陶承有時也給別人做些刺繡,以維持著全家的生活。盡管生活清苦,但夫婦倆關系很好,從未吵過架。多年后陶承回憶起這段往事還是充滿著甜蜜。但是平靜的日子并沒有維持多久,很快一股革命的思潮在長沙涌動,歐陽梅生很早就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對革命充滿斗志,在他的影響下陶承也受到感染,開始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事業之中。歐陽梅生雖是舊社會的讀書人,但他認為“一個人還有社會責任,不應該一生陷在家庭的圈子里”。1923年他離開長沙老家,和幾個朋友去四川辦學校,雖然最終失敗了,但他在這幾年的歷練中感受到了革命的氣息,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把心“都交給革命了!”北伐戰爭期間,梅生作為革命積極分子,負責籌備湖南省總工會,并擔任秘書長,組織工人們協助前線運送彈藥物資,抬傷病員,夜間他還承擔起教書任務,給糾察隊的隊員們上課,將自己的滿腔熱血投入到革命的事業中。
1927年許克祥叛變革命,湖南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和所有的民眾團體及黨校機關都被劫掠一空,長沙一夜之間被恐怖的大幕籠罩。歐陽梅生因是革命積極分子被通緝,不得不撇下家人逃離長沙,前往武漢。陶承追隨梅生,帶著孩子們踏上開往武漢的渡船,夫婦二人并肩戰斗在敵人的咽喉之地。不久,黨組織決定讓歐陽梅生和張浩、龍大道等幾個人,在漢陽成立縣委機關,負責組織這一帶的工作。這時陶承有了自己的革命任務,即以主婦的身份在漢陽縣委機關負責掩護,保護這個大家庭的安全。在當時,采用這種家庭的形式作為掩護,保證黨地下活動的安全是很常見的。真正參與到革命中的陶承對這個任務很投入,她感到自己可以切切實實地為革命盡一份力,而不再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了。“同志們睡了,替他們望風。深夜里聽見可疑的腳步聲,我馬上爬起來,先檢查收藏密件的地方,再到屋前屋后,轉上幾遭。哪個同志出外,我要等門。不回來,就坐到天亮。就是洗衣,做飯,也覺得有了新意義、新內容:‘這是干革命!”
1927年湖南省委決定組織一次暴動,梅生和張浩等人連夜制定暴動計劃,準備奪取電燈公司、電報局,同時攻打軍警機關,還準備偷運武器和自制炸彈。由于革命形式變化,省委下達命令取消暴動計劃,但是這次行動已經暴露,反革命勢力開始大肆搜捕革命黨人,還在報紙上捏造種種事實,污蔑革命,革命一時遭到了嚴重的挫折。梅生和張浩、龍大道等人立即對當時的嚴峻形勢進行了商討,決定由梅生向省委寫緊急報告,以決定下一步革命行動。1928年春,由于過度疲勞,加上本來就體弱多病,嘔心瀝血的梅生積勞成疾,就在這份給省委報告寫完之后去世了。丈夫的離去對陶承來說是個巨大的打擊,她看著梅生遺留下來的毛筆,“毛筆如匕首,直向敵人投。接君手中筆,挽袖畫宏觀!”這個堅強的革命斗士并沒有失去生活的方向,在黨的關懷下,她更加堅定了自己跟黨走的信念,堅定了為革命繼續奮斗的決心!
1929年陶承被派到上海,負責上海工會聯合會的機關掩護,一個月后,調至共青團中央秘書處,這個秘書處設在英租界卡得路樹德里,是一幢兩層小洋房。陶承的工作是收藏和分發文件,在開會時擔任警戒,博古和王明有時也會來這里辦公,她還負責做飯和放哨。黨的中央機關在這段時期由于叛徒的出賣經常遭到破壞,很多同志不幸遇難。在這種局勢下,黨內就對秘密機關制訂了更為嚴格的規定,要求負責掩護的人員要使自己的行動符合自己的合法身份。“住家就要象住家,商店就要象商店,寫字間就要象寫字間。住家要夫婦二人,女的要象家庭主婦,買菜、燒飯、洗衣等等。住家多開會不行,進進出出的人太多也不行。商店進出的人就可以多一些。”因為負責機關的重要性,陶承更是不敢掉以輕心,她所在的機關掩護工作很細致,對出入都有嚴格的規定。她的對外身份是軍人眷屬,丈夫是第九軍顧祝同手下的副官,常年駐防外地。為了掩人耳目,她特地在墻上的信袋里裝上幾個軍事機關的大信封。每天不僅要防“包打聽”,還要防綁匪、盜賊,怕他們把她當成富家太太,偷走黨的重要文件,暴露了黨的組織。由于她工作細心謹慎,兩年來秘書處都未曾遭到敵人的破壞,也沒有搬過地方。
1931年的上海局勢愈加艱難,革命氛圍也愈加緊張。此時的陶承被調到中央國際事務團,仍舊擔任掩護工作。這個機關設在張家花園的一個三層小樓里,她的對外身份是商務印書館林股東的太太。但是僅僅工作了一個多月,就因為有交通員叛變而暴露了。陶承帶著孩子雖然順利逃脫敵人的魔掌,但卻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在當時地下斗爭的年代里,為了找黨,她四處奔波流浪,一邊靠做雜工養家,一邊打探消息,一遇到自認為有把握的人就千方百計的去打聽,但幾年過去始終沒有與黨取得聯系。在夫死子喪又失去黨的庇護的日子里,陶承并沒有消沉,她獨自帶著孩子艱難度日,始終相信總有一天會找到黨,正是這種對黨的無限忠誠支撐著她一定要活下去,是這種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支撐著她繼續奮斗,是這種對革命事業終將勝利的信心支撐著她繼續堅持!
八一三事變后,陶承母子三人進了難民收容所,隨著難民群,從上海乘船經香港、廣州到了武漢,終于找到了八路軍漢口辦事處。在黨的號召下,兒子歐陽應堅和歐陽稚鶴光榮參軍,隨部隊前往延安,她則服從組織安排,只身到重慶,負責保護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重要文件,不久被安排去四川璧山的第五保育院,與孫炳文的夫人任銳同志并肩戰斗在那里。在保育院工作期間,陶承除了完成好自己的革命任務外,還堅持讀書學習,她沒有正式上過學,僅是以前跟著歐陽梅生學過一些字,但她知道知識的力量是無窮的,所以一有空就看書學習,常常半夜起來一個人在油燈下讀書練字,字典都被她翻得又破又舊了也不舍得丟掉。陶承不僅自己刻苦努力,還和任銳同志一道幫助保育院的孩子,給他們講革命道理,講革命故事,還設法從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搜集一些革命書籍給孩子們看,使這些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園,受盡生活折磨的孩子們也能感受到黨的溫暖,感受到革命勝利的曙光。當孩子們唱著“我們離開了爸爸,我們離開了媽媽,我們失去了土地,我們失去了老家。我們的大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他的軍閥。我們要打倒他!打倒他,才可以回到老家,打倒他,才可以看見爸爸媽媽,打倒他,才可以建立新中華!”的《兒童保育院院歌》時陶承欣慰地笑了。
1943年陶承調往延安,本想母子團聚,卻不幸得知小兒子歐陽稚鶴犧牲的消息。她強忍親人離去的悲痛,堅持工作,并在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陶承夫婦共育有六個孩子,除兩個幼年夭折外,其余幾人都在父母的感召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大兒子歐陽立安受革命思想的影響最早,14歲時在長沙修業學校讀書時就擔任糾察隊第一隊的隊長,帶領著學校的孩子們上街巡視,禁止攔街賭博,救濟災民。后隨父母來到武漢,因為年紀小,不引人注意,成為一名地下交通員,承擔起送報的任務。每天陶承都會把折成小長條的《大江報》圍在他的褲腰間,用繩子捆結實,再蓋上棉襖,小立安就負責把他們送到五里路外的漢陽鸚鵡洲黨的機關那里。梅生過世后,他追隨何孟雄投身革命,并在黨的哺育下,光榮的加入共產黨。1930年夏,隨劉少奇帶領的中國工會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8月又參加了少共國際代表大會和蘇聯十月革命十三周年紀念活動。歸國后擔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委員,兼任上海總工會青工部部長。這時國內的局勢也更加險惡,蔣介石開始對中央蘇區發動猛攻,而黨內以王明為首的一部分人,對局勢進行了錯誤的估計,黨內斗爭相當復雜。1931年1月,歐陽立安和何孟雄等人準備召開會議商討抵制王明的對策,但是由于消息走露,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會同租界巡捕房,先后搜查了他們集會的東方旅社三十一號房間,天津路中山旅社六號房間以及虹口、提籃橋、楊樹浦等有關處所,前來開會的歐陽立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龍大道、胡也頻、馮鏗、伍仲文等人不幸全部被捕,其中二十四人英勇就義(亦有二十三烈士之說)。這個烈士的后代在獄中表現得十分勇敢,面對敵人的屠刀,他慷慨激昂的喊道:“中國革命一定要勝利,國民黨反動派遲早要滅亡!我是共產黨員,就是筋骨燒成灰,也還是百分之百的共產主義者!我為主義、為人民而死,死而無怨!”為革命事業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小兒子歐陽稚鶴15歲時在延安抗大學習,并光榮入黨。畢業后,分配到三五九旅政治部任青年股長,還是部隊的文藝骨干。1940年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圍剿陜甘寧邊區五個縣城,三五九旅奉命由敵后回到邊區保衛黨中央,在行進途中遭遇埋伏,年僅16歲的稚鶴不幸犧牲。
另一子歐陽應堅和一女歐陽本紋也都從事革命工作,為新中國的成立和建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正如馬識途所言,“每個人都要走上自己的生活道路,而生活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崎嶇的。”對陶承來說,她所承受的磨難和痛苦是巨大的,但她是堅強的,正如她自己所說:“每當我懷念親人和孩子們的時候,我總是督促自己,要鼓起勇氣來,路還遠得很,絕不能停下來。”因為她深深的明白,“如果說,我的家庭曾經遭受了若干不幸,那么,敵人又毀滅過多少個這樣的家庭!孩子們付出生命,這是為著更多的母親不再失去自己的兒女。黨撫育了他們,教導了他們,他們并沒有辜負這個時代。”
是啊,在革命的歲月,陶承一家不過是千萬奮斗犧牲的革命家庭的縮影,正是這千千萬萬的犧牲,才使我們贏得了最終的勝利!在革命的道路上,“一個人倒下去,千百萬人站起來!”也正是因為有這些革命先烈的披荊斬棘,英勇無畏,才會有我們今天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