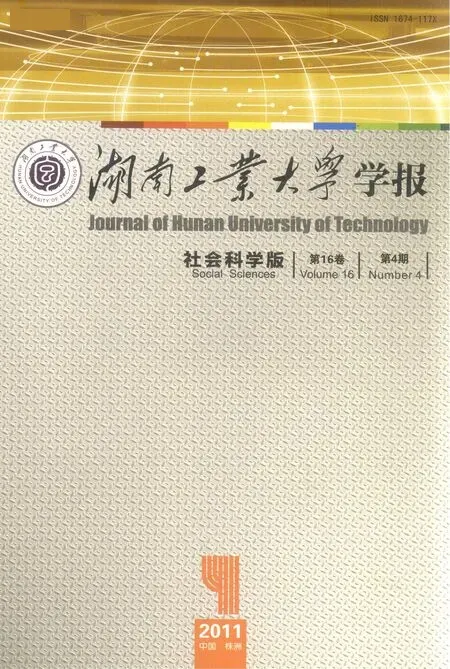個(gè)體身份認(rèn)同與鄉(xiāng)村歷史敘事
——王青偉《村莊秘史》中的鄉(xiāng)村歷史敘事探析*
陳嬌華
(蘇州科技學(xué)院人文學(xué)院,江蘇蘇州215009)
個(gè)體身份認(rèn)同與鄉(xiāng)村歷史敘事
——王青偉《村莊秘史》中的鄉(xiāng)村歷史敘事探析*
陳嬌華
(蘇州科技學(xué)院人文學(xué)院,江蘇蘇州215009)
王青偉的《村莊秘史》以不同人物個(gè)體身份認(rèn)同的艱難和失敗的故事,呈現(xiàn)了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頹敗和崩潰,隱喻和折射了當(dāng)下中國(guó)鄉(xiāng)村社會(huì)在現(xiàn)代化和城市化進(jìn)程中的尷尬、失落處境及其所面臨的嚴(yán)峻迫切的身份認(rèn)同問(wèn)題,體現(xiàn)了作者對(duì)鄉(xiāng)村與城市、本土化與全球化以及中國(guó)與西方等關(guān)系問(wèn)題的深刻思考。
《村莊秘史》;身份認(rèn)同;鄉(xiāng)村歷史敘事;寓言寫作
以文學(xué)形式演繹鄉(xiāng)村歷史是20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重要傳統(tǒng)。王青偉出版于2010年的《村莊秘史》承續(xù)了這一傳統(tǒng),以對(duì)個(gè)體生命身份認(rèn)同的艱難和失敗經(jīng)歷,呈現(xiàn)了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頹敗和崩潰。透過(guò)這部作品,我們或許可以撩開新世紀(jì)鄉(xiāng)村歷史敘事帷幕的沉重一角,窺探到鄉(xiāng)村社會(huì)崩潰背后作者的深重文化隱憂,及其對(duì)全球化語(yǔ)境中鄉(xiāng)村與城市、本土化與全球化、中國(guó)與西方等問(wèn)題的深刻思考。
一 個(gè)體身份認(rèn)同
巴爾扎克曾說(shuō):“小說(shuō)是一個(gè)民族的秘史。”《村莊秘史》標(biāo)題中就含有“秘史”兩字,但是與《故鄉(xiāng)天下黃花》《白鹿原》《秦腔》等鄉(xiāng)村歷史敘事不同,它不是以家族之間的恩怨情仇、個(gè)人之間的欲望紛爭(zhēng)及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日常場(chǎng)景描寫等來(lái)直接演繹鄉(xiāng)村秘史;而是敘述了鄉(xiāng)村——老灣眾多個(gè)體生命的身份找尋和認(rèn)同的故事。《村莊秘史》中幾乎都是身份可疑的人物,他們或者企圖抹去自己曖昧或不光彩的歷史,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來(lái)處,因此無(wú)法追溯自己的歷史;而在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他們也是身份模糊、紊亂之人,不能恰當(dāng)?shù)卦诂F(xiàn)實(shí)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而也無(wú)法確證自己的身份。作品主要以三組人物故事,從社會(huì)政治身份、性屬身份及倫理身份等方面,演繹和凸顯了個(gè)體生命對(duì)身份找尋和求證的艱難經(jīng)歷。
首先,是章大和章一回的政治身份的認(rèn)同與求證。章大也叫章抱槐,黃埔軍校出身,參加過(guò)北伐戰(zhàn)爭(zhēng),并加入中共組織。但在被捕中寫了脫離組織的悔過(guò)書。抗戰(zhàn)期間,加入國(guó)民黨敢死隊(duì),參加淞滬戰(zhàn)役。如果那時(shí)死了,“他的生命就可以在那個(gè)瞬間得以永恒,他留在世界的最后履歷就會(huì)寫著革命連同他以敢死隊(duì)督戰(zhàn)官的身份死于淞滬戰(zhàn)場(chǎng)載入史冊(cè)”。[1]55但他活了下來(lái),作了國(guó)民黨縣長(zhǎng),不久被革職回家。解放后,在一所中學(xué)做歷史教員。他試圖抹去那段不光彩的歷史,重新開始生活。但弟弟章小說(shuō)他是“歷史上有過(guò)污點(diǎn)的人”,教歷史不合適,應(yīng)該改教化學(xué)。[1]69章大于是成了“一個(gè)沒(méi)有歷史的人”,“一個(gè)不能開口說(shuō)歷史的人”,“只能活在現(xiàn)世”。[1]69而一個(gè)人沒(méi)有歷史也就無(wú)法確認(rèn)現(xiàn)在。因此,他決心尋找那些他歷史上幾次閃光點(diǎn)的當(dāng)事人來(lái)證明自己的存在。但至死也沒(méi)有找到,這是一個(gè)永遠(yuǎn)被排拒在主流歷史之外的無(wú)身份的人,死亡是其必然的命運(yùn)歸宿。章一回剛好相反。他成功地抹去了自己曖昧的歷史,成了極左年代“上面”的化身。“誰(shuí)也弄不清為什么章一回竟然成了上面的化身。開始本來(lái)有人質(zhì)疑過(guò)這件事,后來(lái)那幾個(gè)人分別被章一回找去談話,被談了話后他們就一個(gè)個(gè)沉默了,再也沒(méi)有了質(zhì)疑聲。”[1]199但即便如此,最終還是有人對(duì)章一回的最高法庭表示質(zhì)疑;更可怕的是,當(dāng)章一回的臉越來(lái)越年輕而內(nèi)心越來(lái)越蒼老時(shí),他在恐懼中希望通過(guò)懺悔、審判來(lái)確認(rèn)自己身份,因?yàn)橹挥羞@樣,他才能把自己恰當(dāng)?shù)胤湃肽嵌翁厥鈿v史中去,才會(huì)有國(guó)族、身份、村落等的認(rèn)同感和歸屬感,但這一切都被拒絕。由于恐懼、惶惑無(wú)法確證自我政治身份,章一回轉(zhuǎn)向血緣倫理身份認(rèn)同,希望退回母體子宮確認(rèn)自己。他甚至“覺得葉子就是他的母親”,于是退化成嬰兒,“縮在葉子的懷里……”[1]191最后死在樟樹上,成為樟樹子宮里一個(gè)黑點(diǎn)。
其次,麻姑與蒲月的性屬身份認(rèn)同與堅(jiān)守。“性屬”(Gender)又被譯為社會(huì)性別,指從社會(huì)文化層面對(duì)人類性別進(jìn)行界定。女性作為個(gè)體在社會(huì)文化層面的身份認(rèn)同有兩種情形:一是作為主體自我,通過(guò)尋找性別群體的傳統(tǒng)來(lái)確認(rèn)自我身份;二是通過(guò)認(rèn)同已有男性中心社會(huì)給予女性的角色規(guī)范來(lái)確認(rèn)自我身份。因?yàn)椴⒎敲總€(gè)女性都有獨(dú)立的主體性,不少女性的身份更多是通過(guò)認(rèn)同男性中心社會(huì)的角色規(guī)范(母親、妻子、女兒)來(lái)確認(rèn)自己。從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說(shuō),麻姑屬于前者。她來(lái)歷不明,跨越千山萬(wàn)水來(lái)到老灣,目的是要跟章順生一個(gè)女兒。因?yàn)橛辛伺畠海涂梢詭е畠汉退呐畷黄鹑ふ宜膩?lái)處、家園——千家峒。她相信她來(lái)自千家峒,千家峒就是她的家園。她不停地書寫像螞蟻一樣的女書,就是為了保持對(duì)家園的記憶和抗拒現(xiàn)實(shí)的遺忘。當(dāng)所有有關(guān)家園、歷史和記憶的女書化為灰燼后,她就再也回不去了,瘋了。相反,蒲月屬于后者。她的來(lái)歷很清楚,是紅灣“那個(gè)男人”的婆娘。章得因?yàn)槊詰偎男Γ阉兂勺约旱钠拍锒鴼⒘四莻€(gè)男人。蒲月聽從那個(gè)男人的勸說(shuō),為了救兒子,來(lái)到老灣給章得做婆娘,卻再也沒(méi)有笑過(guò)。因此,要認(rèn)同新的社會(huì)身份——做章得的婆娘對(duì)她來(lái)說(shuō),相當(dāng)困難。當(dāng)章得真的把再娃當(dāng)自己兒子,計(jì)劃著要買宅基地,蓋房,為再娃娶媳婦時(shí),蒲月笑了,從內(nèi)心開始認(rèn)可和接受這個(gè)男人和這個(gè)新的社會(huì)身份。然而,蒲月的生命也隨之消失,她化成了“一只碩大的血蝴蝶”飛向紅灣,飛回自己的來(lái)處、根部。
最后,章義和再娃的血緣倫理身份的認(rèn)同與求證。與章大相類似,章義也是一個(gè)失去政治身份的人。他跟隨章小一起參加革命,得到的卻是“把腰彎到地上去了”的結(jié)果。特別是做了美國(guó)人俘虜后,“他所有的出生入死,十幾年的血戰(zhàn)沙場(chǎng)都因后來(lái)變成了戰(zhàn)俘而抹殺掉了。”[1]138當(dāng)個(gè)人歷史被輕易抹去,社會(huì)政治身份的認(rèn)同便成為問(wèn)題。失去政治身份的章義轉(zhuǎn)向血緣倫理身份的確認(rèn),希望通過(guò)血緣生命的延續(xù)來(lái)確證自己的歷史。但兒子章春“你不是我爸爸!”“你是個(gè)俘虜”的話語(yǔ),[1]152把他內(nèi)心強(qiáng)烈的身份認(rèn)同企望擊得粉碎。回到老灣,家鄉(xiāng)人也不承認(rèn)他的身份,“他們懷疑這是另一個(gè)章義,那個(gè)真正的章義應(yīng)該早就死了。”[1]154“章義徹底掉進(jìn)了一個(gè)虛無(wú)的陷阱,因?yàn)樗莻€(gè)沒(méi)有身份的人。”[1]156他只好奔走于曠野尋找兒子,以確認(rèn)自己的身份歸屬。相比章義而言,再娃是幸運(yùn)的。再娃是章得殺害的那個(gè)男人的兒子。剛開始,章得看到蒲月和再娃就恐懼。但當(dāng)拒絕不了他們時(shí),只好接受這一現(xiàn)實(shí)。他忍受著巨大痛苦,實(shí)施“血脈勾連工程”,為再娃再造血緣,重塑身份。再娃慢慢地對(duì)章義產(chǎn)生依戀,兩人“就像親生父子一樣”。然而,當(dāng)“血脈勾連工程”進(jìn)行到只剩下最后一只蟬蛹時(shí),精血的滴澆卻使它變成“蝴蝶花”飛走了。再娃生命中固有的根性拒絕完全同化,特別是他異于老灣人的思維方式和行事方式,以及死后化成蝴蝶飛回紅灣,都體現(xiàn)了認(rèn)同的艱難和失敗。
總之,上述三組人物關(guān)系中,不論是前者(即章大、麻姑和章義),他們被排拒于現(xiàn)存社會(huì)秩序外,內(nèi)心充滿惶恐、虛無(wú),乃至絕望,因此竭力渴望重新回到秩序中,以確認(rèn)自己的歷史經(jīng)歷和現(xiàn)實(shí)身份;還是后者(即章一回、蒲月和再娃),他們成功地被現(xiàn)存社會(huì)秩序所接納和認(rèn)同,但他們內(nèi)心仍固守自己的最初來(lái)處和血脈本性,屬于生命個(gè)體本身攜帶的或原初固有的本質(zhì)東西始終殘存著,強(qiáng)硬地抗拒外在人為的任何同化和塑造。他們最終以死亡或者發(fā)瘋,宣告了認(rèn)同的失敗。這種一致性的認(rèn)同艱難和失敗結(jié)局,昭示了個(gè)體身份認(rèn)同、文化認(rèn)同過(guò)程中的艱難,以及完全同化的不可能,體現(xiàn)了作者對(duì)文化認(rèn)同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二 寓言寫作與鄉(xiāng)村歷史敘事
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逐步實(shí)施與推廣,中國(guó)社會(huì)發(fā)展快速地匯入世界范圍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在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等方面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至新世紀(jì)初的全球化語(yǔ)境中,中國(guó)社會(huì)的現(xiàn)代化和工業(yè)化步伐更是不斷加速,但是廣大農(nóng)村社會(huì)卻并沒(méi)有與整個(gè)現(xiàn)代化和工業(yè)化融為一體,而是呈現(xiàn)出“斷裂”現(xiàn)象:廣大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由于無(wú)法跟上國(guó)家現(xiàn)代化步伐,“被甩在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的過(guò)程之外”,[2]4-11大量勞動(dòng)力被迫涌進(jìn)城市,而進(jìn)城的“農(nóng)民工”也被排斥在城市主流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之外,不能享受城市的社會(huì)保障和社會(huì)福利,面臨著位置和身份的雙重尷尬。農(nóng)村社會(huì)發(fā)展和農(nóng)民生活改善在失去適當(dāng)?shù)馁Y源支持和體制保障后,與城市的差距越來(lái)越大。這一狀況不僅引起廣大社會(huì)學(xué)家的關(guān)注和思考,也引起了許多作家的關(guān)注和擔(dān)憂。
中國(guó)作家內(nèi)心郁積著的濃厚鄉(xiāng)土文化情結(jié),也促使他們承續(xù)五四以來(lái)新文學(xué)作家對(duì)鄉(xiāng)土社會(huì)的情感經(jīng)驗(yàn)和書寫傳統(tǒng),密切關(guān)注著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變化發(fā)展與盛衰榮枯,書寫著那一塊土地上的人們的生活狀態(tài)、道德情感和價(jià)值觀念等。賈平凹就說(shuō):當(dāng)下“農(nóng)村出現(xiàn)了特別蕭條的景況,勞動(dòng)力走光了,剩下的全部是老弱病殘。原來(lái)我們那個(gè)村子,民風(fēng)民俗特別醇厚,現(xiàn)在‘氣’散了。”[3]李銳談到《太平風(fēng)物》的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時(shí)也說(shuō):“農(nóng)村,農(nóng)民,鄉(xiāng)土,農(nóng)具等等千年不變的事物,正在所謂現(xiàn)代化、全球化的沖擊下支離破碎、面目全非。億萬(wàn)農(nóng)民離開土地涌向城市的景象,只能用驚天動(dòng)地、驚世駭俗來(lái)形容。”這些都使得“衣不蔽體的田園早已沒(méi)有了往日的從容和寧?kù)o。所謂歷史的詩(shī)意,早已淪落成為謊言和自欺。”[4]某種意義上可以說(shuō),費(fèi)孝通所說(shuō)的“中國(guó)都市的發(fā)達(dá)似乎并沒(méi)有促進(jìn)鄉(xiāng)村的繁榮。相反地,都市的興起和鄉(xiāng)村衰落在近百年來(lái)像是一件事的兩面”這種現(xiàn)象,[5]在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的中國(guó)鄉(xiāng)村社會(huì)已然成為觸目驚心的現(xiàn)實(shí)。一方面是鄉(xiāng)村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物質(zhì)文明建設(shè)被城市的現(xiàn)代化和工業(yè)化所擠兌和日趨邊緣化,被甩在貧困、破敗的境地;另一方面,鄉(xiāng)村原有的倫理道德和文化精神等也在城市文明的滲透和侵蝕中逐漸走向敗落和消亡。鄉(xiāng)村社會(huì)在國(guó)家整個(gè)現(xiàn)代化和工業(yè)化格局中的位置,如同那些漂泊、游離在城市里的“農(nóng)民工”一樣,陷入了“城不城,鄉(xiāng)不鄉(xiāng)”的尷尬處境,崩潰、頹敗成為其必然的歷史宿命。它再也無(wú)法像以往承載無(wú)數(shù)文人夢(mèng)想的詩(shī)意田園那樣,成為現(xiàn)代作家知識(shí)分子漂泊、孤寂靈魂的理想寓所;也不能“通過(guò)對(duì)農(nóng)業(yè)的規(guī)模經(jīng)營(yíng)實(shí)現(xiàn)農(nóng)業(yè)的產(chǎn)業(yè)化,并以產(chǎn)業(yè)化的農(nóng)業(yè)與整個(gè)工業(yè)化的經(jīng)濟(jì)融為一體”,[2]4以擠乘上現(xiàn)代化的快車。當(dāng)下中國(guó)鄉(xiāng)村社會(huì)同樣面臨著嚴(yán)峻而迫切的身份認(rèn)同問(wèn)題。
因此,書寫個(gè)體生命的身份認(rèn)同不是《村莊秘史》的主要?jiǎng)?chuàng)作意圖,僅是通往作品深層文化寓意和精神內(nèi)涵的象征喻體。事實(shí)上,這從作品開篇“祖先的秘密”中對(duì)老灣的祖先與神秘歷史的追溯,以及“尾聲”中對(duì)鄉(xiāng)村社會(huì)現(xiàn)狀的呈現(xiàn)也可以看出:
……幾乎所有的老灣人都在那邊建起了新房。他們把祖祖輩輩生活過(guò)的老院拋在了這里,任由它荒蕪和坍塌。……每到雨水季節(jié)風(fēng)雨過(guò)后,就會(huì)轟然倒塌一座久不住人的老房子。因此,現(xiàn)在的老灣一眼望去,全是斷墻頹垣和搖搖欲倒的老屋。[1]284
這其實(shí)就是當(dāng)下中國(guó)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鄉(xiāng)村社會(huì)頹敗、崩潰的一個(gè)典型縮影。作者要書寫的正是中國(guó)當(dāng)下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頹敗和崩潰。但較少挽歌式的感傷情調(diào),更多的是冷峻、嚴(yán)肅的現(xiàn)實(shí)思考。雖然作者沒(méi)有、也不可能給出一個(gè)類似新時(shí)期鄉(xiāng)土小說(shuō)那種樂(lè)觀、明朗的答案和前景預(yù)示;但是作品結(jié)尾:那執(zhí)著居住老灣舊村梳理和書寫“族譜”的老人,或許正是作者對(duì)當(dāng)下鄉(xiāng)村社會(huì)處境、命運(yùn)和前景的一個(gè)不甚明晰的思考與暗示。城市化和工業(yè)化是當(dāng)今世界發(fā)展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shì),“要不了幾年,老灣的所有房子就會(huì)全部倒塌,唯有那部著作將長(zhǎng)久地留贈(zèng)給永遠(yuǎn)的老灣人。”[1]285古老的、落后的物質(zhì)形態(tài)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或許會(huì)在現(xiàn)代化的歷史潮流中慢慢頹敗、衰亡,但是,鄉(xiāng)村文化精神及倫理價(jià)值傳統(tǒng)將永遠(yuǎn)沉潛在我們活著的鄉(xiāng)村人身上,并將代代相傳,永遠(yuǎn)承續(xù)和發(fā)揚(yáng)光大下去。這是一種文化本能,也是與生命、血脈相貫通的文化根性,更是文化認(rèn)同中的客觀規(guī)律,這也是作品中再娃和蒲月死后都化為“蝴蝶”飛回紅灣所呈現(xiàn)和喻指的。由此可見,《村莊秘史》中個(gè)體身份認(rèn)同的艱難和失敗境況,折射了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崩潰、頹敗的中國(guó)鄉(xiāng)村社會(huì)在現(xiàn)代化、城市化進(jìn)程中的尷尬、失落處境。同時(shí),由于“從基層上看去,中國(guó)社會(huì)是鄉(xiāng)土性的”。[6]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現(xiàn)代化處境、命運(yùn)何嘗又不是當(dāng)今全球化資本主義潮流中中國(guó)處境、命運(yùn)的象征喻示?體現(xiàn)了作者對(duì)鄉(xiāng)村與城市、本土化與全球化,以及中國(guó)與西方等關(guān)系問(wèn)題的深刻思考。這些問(wèn)題貫穿了整個(gè)20世紀(jì)中國(guó)社會(huì)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也是一個(gè)多世紀(jì)以來(lái)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一再思考和執(zhí)著探索的重大問(wèn)題。盡管20世紀(jì)不同歷史時(shí)期,這些問(wèn)題或輕或重、或隱或顯地被作家知識(shí)分子所涉及和探討過(guò),但從來(lái)沒(méi)有像今天這么嚴(yán)峻而急切地?cái)[在作家們面前,也從來(lái)沒(méi)有像今天這樣錯(cuò)綜復(fù)雜和曖昧難辨,難以進(jìn)行價(jià)值判斷。從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講,如果說(shuō)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以前,文學(xué)作品中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是知識(shí)分子啟蒙情懷、詩(shī)意理想的寄寓地,或者是改革開放奇跡與神話的見證;那么新世紀(jì)鄉(xiāng)村社會(huì)則成為作家知識(shí)分子思考和探索當(dāng)下中國(guó)社會(huì)思想文化和精神狀態(tài)的探測(cè)器,成為他們審視和思考全球化語(yǔ)境中中國(guó)處境、命運(yùn)與前景的出發(fā)地。
《村莊秘史》的故事時(shí)間跨度大,內(nèi)容豐富駁雜,革命與愛情,生與死,個(gè)人恩怨,村落沖突,階級(jí)斗爭(zhēng)等交織一起,頗似時(shí)下盛行的某些新革命歷史小說(shuō)。作品以不同人物個(gè)體的身份認(rèn)同串聯(lián)起20世紀(jì)半個(gè)多世紀(jì)的中國(guó)社會(huì)風(fēng)云變化,依稀可見不同歷史時(shí)期的鄉(xiāng)村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面貌,如北伐革命、抗日戰(zhàn)爭(zhēng)、反右、“文革”及新時(shí)期等。然而,這些都是作為模糊的背景存在,凸顯于作品前臺(tái)的,主要是一些魔幻、夸誕事像。《村莊秘史》的最初寫作構(gòu)思產(chǎn)生于1985年,那是一個(gè)文學(xué)觀念、方法及技巧追新逐異的黃金年代,“尋根文學(xué)”正式登場(chǎng)文壇,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風(fēng)靡一時(shí)。從作品實(shí)際情形來(lái)看,作者創(chuàng)作顯然深受當(dāng)時(shí)“尋根文學(xué)”及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影響。
因此,《村莊秘史》不是反映或再現(xiàn)式仿真寫作,而是一種寓言寫作。張清華曾把寓言寫作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刻意的夸誕,二是刻意的瑣細(xì)。《村莊秘史》顯然屬于前者。它“越出了通常的寫真邏輯而變得寓言化了”,“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對(duì)當(dāng)代社會(huì)生活的反映,而是對(duì)深層的文化病癥、心理痼疾與精神危機(jī)的洞燭與探微。”[7]不論是散落于作品各處的荒誕、魔幻、變形的情節(jié)和事像,如老灣樟樹林里小矮人跳舞的幻境、試圖抹去不光彩歷史的章抱槐在魔鏡中與真實(shí)自己的相遇、蒲月和再娃的死后化成蝴蝶飛回紅灣等;還是每章故事開頭所敘述的章一回“變形”的故事,都可以看到魔幻、變形、荒誕、寓言的重重魅影。這些與個(gè)體身份認(rèn)同故事很好地交融一起,不僅使作品魔幻、現(xiàn)實(shí)與歷史,寫實(shí)、想象與傳奇等交織一體,在藝術(shù)審美方面呈現(xiàn)出獨(dú)特奇異的個(gè)性風(fēng)采;而且也使作品主體故事,即個(gè)體身份認(rèn)同與鄉(xiāng)村歷史敘事有機(jī)相融,成功地實(shí)現(xiàn)了借個(gè)體身份認(rèn)同故事,思考和探索現(xiàn)代化和工業(yè)化進(jìn)程中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以及全球化資本主義進(jìn)程中中國(guó)社會(huì)的命運(yùn)與境遇等重大問(wèn)題的創(chuàng)作用意。總之,《村莊秘史》是新世紀(jì)一部思想性與藝術(shù)性俱佳的優(yōu)秀鄉(xiāng)土歷史敘事作品。
[1]王青偉.村莊秘史[M].長(zhǎng)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孫立平.?dāng)嗔?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的中國(guó)社會(huì)[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4.
[3]賈平凹,郜元寶.“秦腔”和“鄉(xiāng)土文學(xué)”的未來(lái)[N].文匯報(bào),2005-04-10.
[4]李銳.太平風(fēng)物:農(nóng)具系列小說(shuō)展覽前言[M].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6:3-7.
[5]費(fèi)孝通.鄉(xiāng)土重建[M].上海:上海觀察社,1948:17.
[6]費(fèi)孝通.鄉(xiāng)土本色[M]//費(fèi)孝通.鄉(xiāng)土中國(guó)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8:6.
[7]張清華.存在之鏡與智慧之燈——中國(guó)當(dāng)代小說(shuō)敘事及美學(xué)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111-112.
Individual Identification and Country Historical Narrative——Analysis of the Country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Mysterious History of Village by Wang Qingwei
CHEN Jiaohua
(School of Humanities,Suzho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Suzhou,Jiangsu,215009,China)
With difficult and failure stories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individu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Mysterious History of Village,Wang Qingwei presented the decadence and collapse of the rural society,and reflected the embarrassed and desperate situ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rural society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and their serious and urgent identification issues.Furthermore,it also reflected profound thinking on the relationship problem,such as rural and urban,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e Mysterious History of Rural Village;Identification;country historical narrative;fable writing
I207.425
A
1674-117X(2011)04-0015-04
2011-06-10
陳嬌華(1969-),女,湖南郴州人,蘇州科技學(xué)院副教授,文學(xué)博士,主要從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
責(zé)任編輯:黃聲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