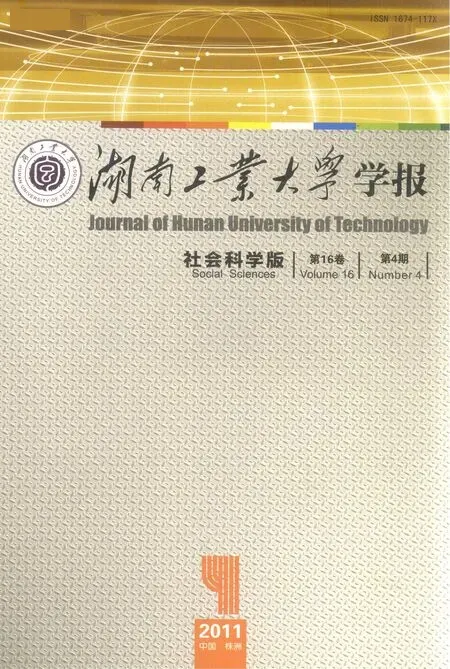論陶淵明“雅”“俗”并容的審美人生境界*
段幼平
(湘南學院中文系,湖南郴州423000)
論陶淵明“雅”“俗”并容的審美人生境界*
段幼平
(湘南學院中文系,湖南郴州423000)
“雅”和“俗”,這一對看似矛盾的審美特質卻在東晉詩人陶淵明身上得到了最和諧的統一。他儒道調和的價值取向,安貧樂道的生活方式,吟詩、品酒、彈琴、讀書的生活藝術,以及關注田園,追求沖和自然的詩文創作風格,無不在質樸中透顯高雅,在超遠中浸潤平俗,形成了他別具一格的“雅”,“俗”并容的審美人生境界。
陶淵明;“雅”;“俗”;審美人生
陶淵明可謂晉宋之際最為獨標一幟之人,他既是品質高尚的雅士,又是躬耕畎畝的俗客;他也曾未能免俗地投身于仕途洪流,卻又難耐身心拘役,辭官歸隱;他飲酒作詩,辭無詮次,卻“詞采精拔,跌宕昭章”[1]。陶淵明無論是其精神追求、生命選擇,還是人生情趣、詩文創作,無不在尋常質樸中透顯高雅韻致,在飄逸超遠中浸潤平俗沖和。“雅”和“俗”看似矛盾的審美特質,卻和諧地統一于陶淵明一生,形成了他別具一格的審美人生境界。
一 退仕歸隱,儒道調和:高拔凡俗的價值取向
傳統儒家和道家對于個體生命價值的判定是大相徑庭的。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2],“朝聞道,夕死可以”(《里仁》)。儒家認為“道”是個體生命價值所在,強調個體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和對功名事業的追求。儒家在重視個體“志于道”外在實現的同時,也強調對內在道德修養的把握:“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孟子·盡心上》)[3]。道家也強調“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103只不過這里的“道”指的是一個無所不在、無所不為、超越時空的無限實體,是“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物我相融,進而達到自我超越的最高境界。所以,道家對個體生命價值的衡量更多的是強調個體生命與宇宙精神的契合、對真誠淳樸人生的向往和對個性自由的追求。
陶淵明生活的東晉朝廷偏安江左,沒有將收復中原作為奮斗目標,而是在“王與馬,共天下”[5]的政治格局中,尋求寬和、偏安,這使得士人們淡忘了亂亡的心理威脅,喪失了奮發進取精神。再加之東晉玄風煽熾,士人重虛誕,輕實務,對國家民生毫無責任感,只求自全。士人個體意識的崛起帶來了人性覺醒,對生命的崇拜使得士人更在乎當下的生命感受,尤其是對肉體感官快樂的把握。這種極端享樂主義、縱欲主義、利己主義的價值取向讓士人在奢靡的生活狀態中虛耗人生。
面對俗世紛擾和精神領域中的此消彼長,陶淵明的人生價值取向則體現出儒道調和的人性光輝。他曾說:“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他渴望像曾祖父陶侃那樣有所作為,鼓勵自己即便功名未就,也要“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直至晚年,還慨嘆“有志不獲騁”。但那個時代并沒有為他提供一個實現理想的舞臺,偏偏他又深契于老莊哲學,質性自然,追求精神的超越和自由,因此,在世人奔波竟逐仕宦名利之時,他卻選擇了“擊壤以自歡”的隱逸生活。晉宋之際,有許多人打著隱逸旗號,標榜著高雅脫俗的風致,卻難守內心的一方凈土。只有陶淵明真正放棄了俗世的種種利誘,恪守堅貞不屈的獨立人格。朱熹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晉、宋人物。”[6]
由此可見,陶淵明從“仕”到“隱”的人生選擇,是從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道德規范的循規蹈矩到道家人格的心靈追求的一次精神飛躍,是他“兼濟”受挫,失去了外在肯定之后轉向對“獨善”內省的自我認可。陶淵明在歸隱之后,沒有像許多士大夫那樣神情沮喪,意志消沉,而是用“羈鳥歸舊林”的喜悅面對躬耕生活的清貧和辛勞,這都是因為他巧妙地將儒家的現實精神與莊子“天人合一”的人格理想融合在一起,使他的人生擺脫了莊子人生哲學的純理性和對人性的冷漠,而飽含著對質樸人生的眷念與熱愛。陶淵明把尋常人生提煉為高雅脫俗的生活藝術,他的人生價值取向也成為中國的一種文化代表。
二 躬耕自資,安貧樂道:平俗隨順的生活方式
儒家一直鄙視農業生產,孔子認為君子要“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道”是第一要義,經世致用是人生的根本目的。兩晉士人談論玄理,游山玩水,吟月賞花,視農耕稼穡為俗務,以不染事務為高雅。但陶淵明偏偏要步入這“俗”流,不但身歸田園,還親自耕種,這無疑與當時所謂的心懷塵外高韻,不諳粗作之士形成鮮明反差。陶淵明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中說:“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他對獨立于物質之外去追求純粹的禮樂道德的行為表示了懷疑,認為“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衣食當須記,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個體生命只有立足于踏實、勤奮的春耕秋收才能變得切實而充盈。這些認識在“恥涉農商”的魏晉時期無疑具有劃時代意義。
陶淵明不是圣人,對生活的認識也和普通人一樣經歷了從膚淺到深刻的過程。例如對農耕,在歸園之初,陶淵明認為:“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勞動是陶淵明內在精神返歸自然的一種外在行為體現,是他保持完整人格,堅守自然人生態度的一種方式。因此,此時的親耕壟畝更多帶有一種審美趣味。但是,隨著田園成為他勞動的主要場所,農耕成為維系家計的唯一手段時,他對勞動的認識就有了轉變。“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陶淵明親眼目睹了田園的凋敝,經歷了從小康之家到家徒四壁的人生變故。如果他被生活的困苦、平庸和瑣碎磨蝕了志向而變得怨天尤人的話,那么他與那些滿口玄理,貌似超然俗塵,實則向往富貴利祿的假名士又有何區別?如何才能身處俗世又不溺于俗?陶淵明的方法就是用審美觀照讓世俗生活“脫俗”,努力從世俗生活中品嘗出超塵脫俗的韻味,獲得高雅享受。
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陶淵明從孔子的遺訓中汲取了生活的智慧,當人面對生活困苦時,就應該像顏回那樣用內心“道”的充盈消除現實中窮困和欲望的羈絆,這樣就可以具有包容萬物的博大心胸和廣攝深遠的眼光,捕捉到凡人忽略的生活之美和人生情致。在陶淵明的筆下:“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農耕生活雖然艱辛,但他從中獲得了“但使愿無違”的精神滿足,領略到了“山澗清且淺,遇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雙雞招近局”的人生樂趣,同時也獲得了“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的人間至情。山光水色、方宅茅舍、雞鳴犬吠、風土人情讓陶淵明心境沖和閑淡,任性自得,忘懷得失。他用返歸人性真淳的心態消弭了世俗中的一切丑惡和困頓,“用審美的態度對待衣食住行,以藝術家的眼光打量著身邊細事,將其‘詩化’、藝術化,從俗世中辟出一片清幽淡雅的意境,體悟出一點玄澹高遠的意趣。”[7]
三 吟詩、品酒、彈琴、讀書:玄澹高雅的生活藝術
陶淵明在肯定了衣食住行世俗生活的合理性之后,并不像普通人那樣僅僅滿足于物質生活的需要,又不像兩晉某些名士為一味攀附風雅過著所謂閑云野鶴的生活,他不是強作風雅的人,但他無論是飲酒吟詩、賞菊觀云、彈琴讀書、都有別于時人,而足見他的古風高韻。
魏晉士人大多嗜酒,張季鷹認為:“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畢茂世也說如能“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8]。飲酒行為從最初人的簡單飲食之欲逐漸成為名士標榜脫俗,展現個性,對抗名教的工具,直至最后又陷于單純生命享樂的庸俗泥澤。陶淵明卻不同,顏延之說他“性樂酒德”,他的飲酒并不為滿足單純口腹之欲,而是具有高潔出俗的特質。陶淵明曾在九月九日詩中寫到:“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九日閑居》)。重陽飲菊花酒,這種傳統的民間風俗,通過陶淵明的詩作被賦予了一種酒關人生憂患,菊顯人格品質的豐富文化內涵。他喝醉了,在自家便說:“我醉欲眠,卿可去”,在別人家便“曾不吝情去留”。陶淵明飲酒時絕棄偽飾,張顯真率之情的人格風神,又豈是世俗那些用酒精麻醉人生之人所能相提并論的?
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說陶淵明“情不在于眾事,寄眾事以忘情也。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焉”。[1]2463在蕭統看來,陶淵明的飲酒志趣是不同于一般人的,而是將酒與人生思考、與詩聯系起來,酒已成為他人生藝術化的媒介,飲酒行為本身也就有了一種詩性的超越。
《晉書·隱逸傳》記載:陶淵明“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一張沒有弦徽的素琴,又如何能彈出美妙的樂聲呢?琴作為一種古老的樂器,因為其取材制作清雅,加之伯牙、子期高山流水話知音的優美故事,常常被視為文士抒發個人情思的最佳工具。伴隨著魏晉以來人性的自覺,琴的社會功用也從早期儒家推崇的“皆反中和,以美風格”(馬融《長笛賦》)的道德教化逐漸顯示其“宣和情志”(嵇康《琴賦》)陶冶情性的娛樂作用。陶淵明說自己“少學琴書”,“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歸隱之后“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琴書成為他娛情悅性,寄托情志的一種高雅方式。甚至到了晚年,他還“欣以素牘,和以七弦”(《自祭文》)。與琴書相伴的生活讓陶淵明平息了內心波瀾,忘懷世事功名,體會到田園生活的悠閑和歡娛。至于陶淵明是否“解音”,琴上是否有弦,倒不必過于追究。《禮記·樂記》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9]從本質上看,音樂是直接從心生發出來的,而無需客觀外物的介入。老子也說:“大音希聲,大象無形”[4]171。所以陶淵明的“無弦琴”追求的是在彈撥琴弦的過程中獲取的人生至理,是一種超越了具體聲音形跡的更為深廣的審美追求。
四 關注田園,追求沖和自然:清新脫俗的詩文創作
在東晉南北朝,陶淵明的詩文創作一直沒能得到足夠的重視,劉勰《文心雕龍》對陶淵明無一字涉及;蕭子顯《南齊書·文學論札》歷評自古而今的五言詩人,惟獨沒有陶淵明,甚至沈約在《宋書·陶淵明傳》中也沒有論及他的詩文創作,原因何在呢?
《文心雕龍·時序》曰:“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余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10]、“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10]49(《明詩》)。在這樣的文學風氣影響下,許多詩人熱中闡釋玄虛哲理,刻意雕琢藻飾,形式重于內容。顏延之是當時文壇巨擘,其詩“尚巧似,題材綺密,情喻淵深”[11],如“錯彩鏤金”,且能“垂范后昆”。可見,陶淵明詩文在當時被忽視就是因為詩文的美學特征與當時的文學風氣和時人審美期待視野難以契合。但在遭遇短暫的冷遇后,陶淵明詩文1 500多年來一直受到后世詩家的頂禮膜拜。宋代蔡正孫《詩林廣記》卷一引范正敏語云:“淵明趨向不群,詩采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明代何孟春認為陶淵明是“自兩漢以還為第一等作家”;[12]王國維更是認為“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后世仿陶詩更是數不勝數。陶詩從被冷落到被推崇,這說明陶淵明詩文的生命力,也證實了在晉宋綺密華靡的模式化創作中,“陶詩開辟的是一條與俗迥異的道路。”[13]
(一)田園題材的開拓。盡管在陶淵明之前已存在田園詩的濫殤,但田園和農耕僅是作為農業生產生活的背景出現,是襯托主體活動,表達主旨的媒介,不具有獨立審美作用。隨著魏晉詩人自然思想的逐漸成熟,山水和田園成為他們關注的對象,也逐漸走入他們的詩文創作。但由于政治權勢、門第出身、經濟基礎和審美風尚等因素的影響,上層貴族文人多寫名山大川、亭臺池苑,而鄙寫稼穡,“這種情況也就決定了他們的身心不可能進入鄉村田園,不可能發現平凡的景物之美。”[14]而陶淵明卻寫田園竹籬茅舍、狗吠雞鳴、炊煙山嵐、春種秋收等普通農家生活,打破了以往寫田園只言農家苦的陳舊模式,盡情謳歌了田園寧靜、和諧、清新、樸野的審美特質,在中國詩歌史上開創了新的審美領域。
(二)開創了沖淡自然的詩歌風格。建安時期,中國文學的美學特征是以三曹等人為代表的慷慨蒼涼之美,西晉是是以潘岳、陸機等人為代表的綺麗之美,而陶淵明卻開創了沖淡自然的美學新天地。
陶淵明心念丘山,厭鄙官場,向往真純人性的自然生活,因此身歸田園,平居澹素。再加之以默為守,涵養既深,委運順化,與自然冥和,自然就看淡了人間悲喜,他的詩正如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所概括的:“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荏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脫有形似,握手已違。”[15]這種沖淡之美在《和郭主簿》(其一)中體現得最為鮮明,詩人不用典故,不施藻飾,既無比興對偶,也不渲染鋪排,只是真情流露,就營造了一種“沖淡”的藝術境界。
自陶淵明之后,“沖淡”作為一種詩歌美學風格受到了詩家大力推崇。例如,蘇軾在《評韓柳詩》中說:“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明代李東陽也說:“詩貴立意,意貴遠而不貴近,貴淡而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可與知者道,那與俗人言。”(李東陽《懷麓堂詩話》)從詩人創作角度看,一切詩文創作皆因“質性自然”的真情流露,不是刻意追求,理、事、情、物等人的生活中一切物質的與精神的都真實存在,詩人將這些真實存在如實地呈現出來;從讀者的角度看,“自然”風格下的詩文給人的感覺是泯滅了人為雕琢而以本色呈現,就“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給人以至美享受。
(三)樸實無華“田家語”的運用。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詩賦欲麗”,陸機在《文賦》中也提到“詩緣情至于綺靡”。詩歌語言的“麗”與“情志”相配合,已經成為魏晉時期詩人們對文學創作的一個認識,以至于后來過于追求藻采、駢儷、用典,“鋪采摛文”以達到“麗”的效果,導致了“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的后果。陶淵明詩歌大多描寫的是田園樸實生活,平淡的景色不宜濃抹雕飾,所以他開創性地運用了樸素無華的“田家語”來再現生活的本色,這也是陶淵明在身心回歸到“自然”后,語言也回歸到一種毫無人為雕飾、去除鋪金疊繡、典麗新聲的語言自然狀態。如: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歸園田居》其一)
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酬劉柴桑》)
夏日抱長饑,寒夜無被眠。(《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陶淵明的詩歌無論是在題材、內容還是語言、風格都給人以樸素自然之美,仿佛是從珠光寶氣的貴婦堆中走出的一位荊釵布裙的村姑,讓人不禁為她清新脫俗的風致所折服。
在傳統的審美心理中,“雅”是以突出個性,不以追隨時尚俗好為特征的,因此“雅”是陽春白雪,難免曲高和寡;“俗”是以當時的大眾審美心理為目標,強調通俗、平易,所以“俗”是下里巴人,難免粗野簡陋。可是在東晉,士人卻將追隨玄思、沉溺玄理,縱樂服藥,綺麗浮華詩風等所謂“雅致”當作士林風范加以推崇,反而遺失了自我,落入庸俗的窠臼;陶淵明卻能堅守躬耕田畝的“俗行”,固窮守節,老死丘園,以脫落世故,縱浪大化、委運隨順的態度洞悉生命本質,體味人生百態;用平淡沖和的田園詩風,彰顯其傲岸拔俗的精神氣韻、平俗隨順的生活態度,以及不同流俗的審美視野。他用藝術審美的心態觀照生活,從而使他的人生平俗不失高雅,詩歌清淡,高遠又平易,通俗,較好地做到了“雅”“俗”的調和和平衡,形成了他別具一格的“雅”“俗”并容的審美人生境界。
[1]蕭統.陶淵明集序[M]//梁昭明太子文集:卷四.[出版地不詳].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
[2]孔子.論語[M].程昌明,譯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81.
[3]楊伯峻,楊逢彬.十三經今注今譯:下[M].長沙:岳麓書社,1994:2149.
[4]朱謙之.老子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4.
[5]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2554.
[6]朱熹.論陶三則[M]//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75.
[7]韋鳳娟.悠然見南山——陶淵明與中國閑情[M].濟南:濟南出版社,2004:100.
[8]張萬起,劉尚慈.世說新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8:730.
[9]錢玄,等.十三經今注今譯:上[M].長沙:岳麓書社,1994:887.
[10]劉勰.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479.
[11]鐘嶸,周振甫.詩品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8:67.
[12]何孟春.陶靖節集跋[M].[出版地不詳].明嘉靖癸未重刻本.
[13]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M].濟南:齊魯書社,2002:39.
[14]杜景華.陶淵明傳論[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175.
[15]司空圖,袁枚.詩品集解續詩品注[M].郭紹虞,輯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5.
Combination of Elegance and Vulgarity in TAO Yuanming's Aesthetic Life Realm
DUAN Youping
(Chinese Department,Xiangnan University,Chenzhou Hunan 423000,China)
The most harmonious unity of elegance and vulgarity,two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aesthetic idiosyncrasies,has been presented in the life of TAO Yuanming,a famous poet in Eastern Jin Dynasty in ancient China.TAO Yuanming resigned and returned to his rural life which is composed by his harmonious and Confucius value orientation,feeling of contenting in poverty and devoting to things spiritual,life arts of reading,poem and music,poetic writing of rurality and nature.All of these represent TAO Yuanming's special aesthetic life realm where simplicity implies elegance,vulgarity embodies overpass.
TAO Yuanming;elegance;vulgarity;aesthetic life
I206.2
A
1674-117X(2011)04-0074-04
2010-12-20
湖南省教育廳基金資助項目“生態思維視境下的東晉詩歌研究”(10c1218)
段幼平(1971-),女,山西太原人,湘南學院中文系副教授,碩士,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責任編輯:衛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