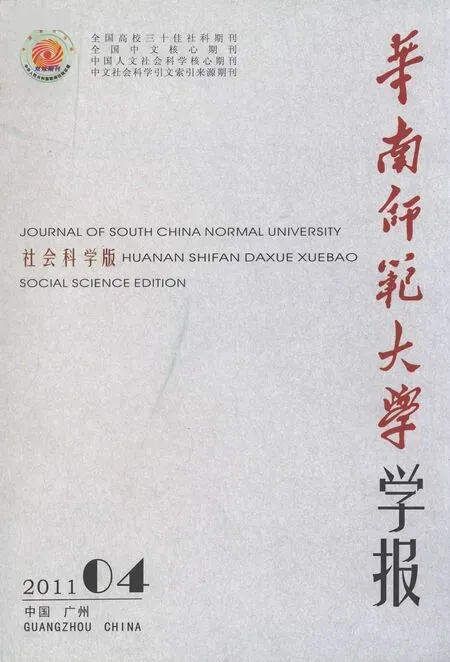論魏晉文派
馬茂軍
(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論魏晉文派
馬茂軍
(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魏晉文派的意義不僅僅是一個駢文派。魏晉文派是中國古典散文史上的浪漫派、重情派。它作為中國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個重要傳統而存在,是蘇軾小品文、明代公安派、現代小品文的活的源頭。
魏晉文派 浪漫派 重情派 隱傳統
魏晉玄學作為中華文明史上的一次思想大解放運動,作為中國哲學思想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已經為大家所認識。而魏晉文章的價值和光輝,至今未能為我們所認識。雖然論者認識到了六朝文章對純文學、對美文性格的追求,但這還是遠遠不夠的。本文認為魏晉文章是中國古典散文的浪漫派、重情派。它作為中國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個重要傳統而存在,是蘇軾小品文、明代公安派、現代小品文的中國傳統和活的源頭。我們對魏晉文章應該給予足夠的認識。
一、近現代學術史上的魏晉文派
一般以為魏晉文派的創論者是阮元。阮元作有《文言說》《文韻說》,提倡魏晉駢文。筆者認為魏晉文派應該始于魏晉名士和魏晉文章。蕭統編選的《昭明文選》和《文選序》可以說是魏晉文派的宣言。《文選序》強調選文的對象是“能文為本”。能文是指辭藻、對偶、音律、用典等語言技巧。選文重視文學的娛樂性:“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具為悅目之玩。”選文強調“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藻”,強調文學的形式美。《文選序》可以說是文學覺醒的宣言,是純文學、美文學的宣言。
與經學家、史學家、政治家以經史為文的觀點不同,《文選》公然把經、史、子等學術性著作排除在文學作品之外,顯示了與后代唐宋古文家、桐城派截然不同的文章觀。《文選》在后代不僅僅作為一部文學作品集而存在,而是作為一個影響深遠的文選學派而存在,作為一種重文學的文學傳統而存在,作為一個與古文派分庭抗禮、針鋒相對的文學勢力而存在,直至五四運動還要費力地打倒“選學妖孽”,可見其根深蒂固的影響。
早期駢文派是通過編輯傳播六朝作品來宣傳自己的文學主張的。明末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即有提倡六朝文章的用意。清初陳維崧、吳綺以駢文著名。相傳陳維崧撰有《兩晉南北朝集珍》和《四六金針》。《四庫總目提要》稱《集珍》:“采南北朝故實,各加標目,蓋即以備駢體采掇之用。前有自序,作于康熙丙辰。”乾隆嘉慶之際,駢文作者輩出,胡天游、汪中最為著名,又有“駢文八大家”之說,大有與古文爭奪文壇正統的味道。李兆洛(1769-1841),江蘇陽湖人,嘉慶進士,主講江陰書院,曾編《駢體文鈔》,宏揚六朝駢文,按文體分類,與姚鼐《古文辭類纂》相對峙。其序言說“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繼承《文選》和六朝駢文傳統。
從理論上樹立駢文派旗幟的是清代儀征學派阮元。阮元針對桐城派質木無文的局限,援引六朝文筆“有韻為文,無韻為筆”之說,主張把駢文作為文學正宗,貶低古文為筆,作有《文言說》(《研經室三集》二)、《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后》、《與友人論古文書》,其子阮福有《文筆對》。阮元認為有對偶才有文,又引《易經》中的《文言》加以申述。他推崇六朝駢文成就,以《文選》為寶典,信從蕭統《文選序》中“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藻”之說,在《文韻說》中提出:“凡為文者,在聲為宮商,在色為翰藻”,重視文章的聲韻。阮元官位顯赫,又熱心文教事業,加上同時期汪中等人的煽動,對清代中世之后文風的改變發生過很大作用。
民國年間,作為儀征派后學的劉師培,繼起發揮阮氏學說。劉師培撰《廣阮氏<文言說>》,又援引載籍,考之文字,以為“文章之必以彣彰為主”。他在《文章源始》中推闡阮氏之說,強調“駢文一體,實為文體之正宗”。這種爭正宗的思想,實與當時的學術思潮沖突有關,與桐城派和《文選》派的斗爭有關。清未民初,桐城派最后幾位大師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和林紓等人先后在京師大學堂及其后身北京大學任教,桐城派占據了教席。其后章太炎門人黃侃、錢玄同、沈兼士、馬裕藻及周氏兄弟等先后進入北京大學(章氏論文,重魏晉而輕唐宋),后劉師培以擁護袁世凱稱帝失敗,也進入北京大學任教,主講六朝文學,一時魏晉文派取代了桐城派的勢力。姚永樸在北京大學講授桐城派理論,著《文學研究法》,黃侃講《文心雕龍札記》,是代表桐城派與《文選》派的兩部文論名著,又暗含針鋒相對之意。①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黃季剛先生〈文心雕龍札記〉的學術淵源》,第2頁,周勛初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劉師培《文章源始》探討文學源流,揚駢文貶古文:“明代以降,士學空疏,以六朝之前為駢體,以昌黎諸輩為古文,文之體例莫復辨,而文之制作不復睹矣。近代文學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為文章之正軌,由斯而上,則以經為文,以子史為文。由斯以降,則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②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第33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劉師培又作《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宣傳六朝文章,一時六朝文派大盛。
清代對六朝文的發明系統而全面,不過仍然不脫駢文傳統意義。至近代民國章太炎等一批在日本接受西學的人士加入,六朝文派才煥發了青春。周作人師徒開創了現代六朝散文派。這是一種新的文體觀:六朝文主要指六朝散文,而六朝駢文降為六朝散文的一體而已。
因此魏晉文的概念,一是大量成功的駢體文,二是為我們忽視的非常成功的散體文,成功的標志是有一流作家和作品。
歷代文學史家皆貶低六朝散文,唯鄭振鐸1932年之《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二十一章,列舉了眾多“六朝的散文”的實績;章太炎也專門推崇適合表達義理的六朝散體文章,如酈道元的《水經注》、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顏之推的《顏氏家訓》,而成就最高的是《世說新語》。《世說新語》是散文,而不是小說,筆者另有《論筆記散文》,茲不贅述。
筆者以為,六朝散文無論作家陣容、名篇名作,還是思想價值、藝術價值都可以媲美“唐宋八大家”,成就遠遠高于秦漢派、唐宋派、桐城派,是中國古代文學主要的思想、藝術資源寶庫。
二、魏晉文派與唐宋文派的現代闡釋
前人研究魏晉文派已多有發明,而缺陷在于主要還是將它看作一個與古文派對立的駢文派而存在,文體意義大于文派意義,而文筆之辨也未高于魏晉時人的理論水平。就學術而言,駢文派、文選派以純文學的觀點,以文筆之辨來將唐宋八大家排除在文學之外也是偏激的,是囿于魏晉一代、駢文一派的觀點。筆者認為魏晉文派的價值不僅在于它是一個文派,更在于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生發性和延伸性。它代表了一種被我們所忽視和遺忘了的散文浪漫派、重情派的傳統。我們可以將唐宋八大家散文—秦漢派—唐宋派—桐城派看成是一條線上的傳統:唐宋文派的傳統。過去我們把這看成是中國古典散文的唯一傳統。實際上,中國古典散文還應該有魏晉文派的傳統。它的文統是莊子—魏晉文派—蘇軾—明代小品文(或曰公安派、竟陵派)—現代小品文。這個傳統具有現代指向性和延續性,而唐宋文派的傳統則是斷裂的,作為桐城謬種被埋葬了。
從現代理論視野上看,唐宋文派的性質是古典主義流派,而魏晉文派則是浪漫主義流派。古典主義的特點是以古為典,崇尚古代經典。唐宋古文運動者將秦漢散文奉為經典,并加以模仿;秦漢派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明代唐宋派則透過“唐宋八大家”來學習秦漢派,而桐城派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唐宋派、秦漢派。
古典主義的另一個特點是崇尚理性。古典主義者強調理性寫作,強調控制作家的情感。這種理性既是思想的理性,又是寫作的理性。它要求強調文體的純潔性及其各自的規定性格調。
唐宋古文運動強調文以載道,反對駢體文風,就是這種理性主義寫作的表現。唐宋古文運動一方面反對佛教盛行、儒教淪亡、理性喪失的思想界;一方面又批評駢體文追求雕琢辭藻、嘩眾取寵,批評缺乏理性、耽于感官刺激的文壇。在純凈文體方面,古文派以古文為正宗,以秦漢文為最純凈的文體。真德秀《文章正宗》甚至為每一種文體制定了純凈的度量和標準,規定了文體范式,強調文章的格調,制定文體規則。追求典雅是古典主義散文家的重要使命。
而魏晉文派則與之不同,它是散文中的浪漫派。它盡量突破儒家的思想一統,打破傳統文壇規則,追求自由的思想與自由的抒寫。
三、魏晉文派的三大特點
(一)魏晉文派的散文體現了魏晉名士追求自由和反叛禮教的精神
魏晉政治的動亂沖破了兩漢的禮法統治和綱常教條,涌現出“竹林七賢”等一大批狂狷之士。狂狷成為時代精神和風尚,成為反叛者的偶像。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第十一講《魏晉玄學的主要課題及玄理之內容與價值》認為“魏晉時代的特殊人物是‘名士’”,“當時的時代精神寄托于名士”,名士清談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價值觀念。①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第17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顧炎武《日知錄》記:“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凡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于洛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②顧炎武:《日知錄·正始》,第1012頁,黃汝成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棄經典是對古典主義的蔑視,蔑禮法是反判傳統與現實,崇放達則是追求精神的自由。
作為魏晉精神直接表述的魏晉散文則是更直白地表達了這種自由和反叛精神。魏晉散文以它特有的深度表達、明晰推演、邏輯論證和哲理闡發表達了魏晉名士們的反叛,表現了“竹林七賢”們對精神自由的浪漫追求。嵇康的《難自然好學論》直白表達了“從欲則得自然的觀點”:“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愿,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這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宣言。這是反叛,反叛的目的是為自由,可以說魏晉士風是一場以情欲沖擊禮教秩序而追求自由的運動。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喊出了“非湯武而薄周孔”的叛教口號,終而見殺。書中言他“不涉經學”,“頭面一月十五日不洗”,“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嘻笑怒罵,以老莊為人生樂趣:“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在嵇康看來,湯武周孔這些圣人和經典已經成為自由和自然的桎梏,成為性情之牢籠,必須沖決。故劉勰《文心雕龍》說:“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
嵇康是這場反抗運動中最剛烈而丟掉性命者。“竹林七賢”除嵇康怒目金剛式的反抗外,余皆放浪形骸,消極避世,采取軟抵抗的方式,屬于消極浪漫主義。他們屬名士,而非勇士。史載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劉伶的方式和阮籍大醉六十日拒絕司馬昭為其子求婚的方式是一樣的。現實中的消極,并不妨礙他們精神上和文學世界中的自由和反叛。他們的散文中最直白地表達了這種追求自由的精神。
劉伶《酒德頌》以酒為德,歌而頌之,描寫一位放浪形骸、脫略禮法的“大人先生”的形象,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牗,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壸,唯酒是務,焉知其余。”弄得縉紳君子“怒止切齒,陳說禮法”。劉伶是“竹林七賢”之一,《晉書》本傳說他“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本傳又說他“嘗為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阮籍《大人先生傳》在幻想的世界中虛構了自己大人先生的形象,是“大而無當”“不近人情”的“神人”“真人”,實則是外順世而內心逆世。現實中是枯木般的人格面具,內心是渴望自由之精神與獨立之人格的火一般激情。他的毀棄禮法、縱酒放誕、好為“青白眼”,足以表現他的反抗。在文體上他以散體為主,駢散結合,又夾騷體,自由、創新,無所法度。
而王羲之《誓墓文》是一篇見真性情的奇文。不愿做官,竟到父母墳上設誓,實是一種別出心裁的沖動,而“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征之”。他在給謝萬的信中慶幸地說:“古之辭世者或被發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仆坐而獲免,遂其宿心,甚為慶幸,豈非天賜!”
除了反抗,我們在魏晉名士身上更看到了一種人格精神之美,甚至連入世派的曹操身上也可見人格精神的宏大壯美。“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步出夏門行》)何等悲壯的人格氣度。“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則是面對死亡所表現出的一種審美的、藝術態度。
(二)魏晉文派是中國散文史上最深情的文派
魏晉時代是一個追求情欲、放縱情感的時代。《晉書·范宣傳》載:“逮晉之初,竟以祼裎為高。”《晉書·五行志》也云:“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散發倮身之飲,對弄婢妾。”而作為孔子二十世后裔的孔融,對血緣關系大放厥詞:“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這是孔門中人宣揚的情欲對教化的反叛。
朱自清《詩言志辨》認為陸機“詩緣情而綺靡”鑄造了一個“緣情”的“新語”,代表了一種個性及真情得到自由表露的新時代新風尚的到來。同時代的典籍也都大量談情,而真情是浪漫主義的核心內核。緣情非理、淡化理性,才有自由和浪漫,重理非情則易趨向古典而僵化。據記錄當時名士風尚的筆記散文《世說新語》記載:“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任誕》)“王(戎)曰:‘情之所鐘,正在我輩。’”(《傷逝》)“孫子荊除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覽之凄然,增伉儷之重’”(《文學》)“庾亮死,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己!”(《傷逝》)這種重情的名士風度反映在文學上則是對“緣情體物”的抒情性的強調,如“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①王筠:《昭明太子衰冊文》,《全梁文》卷六五。。徐陵《〈玉臺新詠〉序》:“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宇文逌《庚信集序》:“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②《全后周文》卷四。李昶《答徐陵書》:“風云景物,義盡緣情。”③《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九。緣情重欲成為一代風尚。
這種重情的時代精神和緣情的文學思想使魏晉散文成為中國散文史上最深情的文派。
遠者就政治人物而言,曹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直白述情,無所矯飾,抑揚頓挫,別具風情。曹丕《與吳質書》則以傷逝為主,追念舊游,哀悼亡友,自傷老大,是一篇著名的書信體抒情散文。曹植《洛神賦》“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無疑是篇幻想的深情的浪漫名篇。諸葛亮以前后《出師表》而名世,其實通過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行為心跡,我們何嘗不能體會他高傲的心情與浪漫主義的北伐行為呢?我們不能茍同他出師北伐是個現實抉擇,無寧說是體現了諸葛亮人格與理想力量的光輝。
向秀的《思舊賦并序》是深摯友情與感傷生命的佳文。李密《陳情表》更以“情”聞名。其“煢煢子立,形影相吊”,“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余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至情真性,不假雕飾,一一從肺腑汩汩流出,動人心弦,催人淚下。王羲之的浪漫情懷,可從瀟灑俊逸的《蘭亭集》序中看出,既有山水之情懷,又有玄遠之意趣。江淹《恨賦》充滿了對生命的感嘆,對抱恨離世者的追問,具有驚心折骨的拷問力度。而《別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更是一句傳唱千古的深情感嘆。丘遲《與陳伯之書》雖說理之文,而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于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實現了一封深情書信降服八千叛兵的奇跡。
(三)回歸自然成為魏晉文派的重大主題
1.魏晉山水美學
英國的浪漫主義是從謳歌自然的湖畔詩人華茲華斯開始的。而中國浪漫主義對山水的熱情比湖畔詩人要早一千多年。山水大滋,當在魏晉時期。隨著儒宗沒落,老莊盛行,生活方式上大莊園的盛行,山水自然終于成為人們的自覺的審美對象,山水詩、山水散文也極大地發達起來。山水的樂趣是與塵世的黑暗痛苦、激烈的社會矛盾、社會政治對士人強大的精神壓力形成對比的。山水成了解放人的工具,成了帶領世人走向自由的另一王國。“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水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④《世說新語·言語》篇,又見《晉書》卷九二本傳。“(綽)居于會稽,游山放水,十有余年。”“統,綽之兄,家于會稽,性好山水。……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務究。”⑤《晉書》卷五六《孫綽傳》。“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曾游東平,樂其風土。”⑥《晉書》卷三四《阮籍傳》。登臨山水,如同劉伶醉酒,阮籍駕車,既是名士放狂,也是彼岸樂土,精神神游。這種風氣下,自有許多浪漫風流的山水名篇,如袁嵩《宜都記》、石崇《金谷詩序》、王羲之《蘭亭集序》、陶淵明《桃花園記》。
2.魏晉文派的山水散文
提到山水散文,我們永遠繞不開陶淵明和他的《桃花源記》。《桃花源記》是魏晉散文中最引人注目、又最引人爭論的名篇。很多名家如梁啟超、陳寅恪、朱光潛、郭預衡、譚家健都對它的原型和所反映的思想傾向有所爭論。筆者認為,從浪漫主義散文的視野來看,其一,它可能有原型,但在哪里并不重要。因為作品中的桃花源是“浪漫化”后的桃花源,其中加入了陶淵明的想象甚至虛構。我們必須分清文本與桃花源之本事的區別。其二,文本中的桃花源是寄托了陶淵明回歸遠古、返樸歸真、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大同社會的理想,它已經不是現實中的桃花源了。其三,它是一篇浪漫主義散文,《搜神后記》和梁啟超將它的著作權拉入小說陣營中是說不通的。①梁啟超《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這篇記可以說是唐以前第一篇小說。”載《飲冰室合集·專集》,第22冊,第17-18頁,中華書局1936年版。以浪漫主義的視野來看,桃花園的現象、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理想、隱士的自傳,無非是一個美麗的謊言,一種對理想的追求,一個經過了藝術處理的現實。理想化意味著想象或夸張,這是浪漫主義的合法性。它對抗著中國古典主義散文的強大正統和壓制,也是創造新的文學的力量。
與大多數人對自然與隱逸的向往不同,陶淵明是一位真正的踐道者、實踐者。他質樸而單純,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他的《五柳先生傳》不同于阮籍《大人先生傳》的大言與荒誕不經:“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沒有高自標榜,“閑靜少言,不慕榮利”。“贊曰: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欽?葛天氏之民欽?”這是上古原始純樸的社會,是烏托邦理想。陶淵明的另一散文名篇《歸去來兮辭》體現了對自由追尋的精神:“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詩人將“心為形役”視為“迷途”、“昨非”,認為真正能帶來身心自由的,是田園:“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陶淵明的田園散文與阮籍嵇康等人的散文不一樣,是一種閑正詳和、安樂舒逸的境界,是身心俱安、體達大道的境界,是真正超功利的、審美的浪漫和超脫。
吳均《與顧章書》:“仆去月謝病,還覓薜蘿。即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于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是篇八十四字的隱逸小品,將隱居的石門山寫成了人間的仙境,充分表達了隱逸之美和快樂。吳均《與朱元思書》為千百年來寫景名篇,為六朝山水小品的上乘之作:“風煙俱凈,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能寫如此美景,緣于詩人熱愛自然的心態,緣于對自然的深刻認識:“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返。”這是一個山水自然派,一個隱者的世界觀。陶弘景的《答謝中書書》與吳均的《與朱元思書》堪稱雙璧,文章雖只有六十八字,而將作者幽棲山林、俊賞妙悟之情趣寫出來了。文章既有“兩岸石壁,五色交輝”的工筆(陶三十七歲退隱茅山四十四個春秋,故有此觀察力與神會),又有“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青林翠竹,四時俱備”的概括傳神寫法;而“實是欲界之仙都”,乃集四十四年心靈之呼喊。
從上文分析中我們可以見出,清人、近人對魏晉文章價值的認識主要是從駢文派立論的,這對弘揚純文學和美文學價值觀念、對古文派的反抗是有價值的。但它的文體局限和文學價值觀的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從現代的視野來看,魏晉文章即使單論文體,也不是駢文獨勝的,像《桃花源記》、《世說新語》這類最精彩的魏晉文章,往往是散文而非駢文;而且,魏晉文章中的記、序、書幾類散文文體成就都很高。從文學傳統而言,魏晉文派浪漫派、重情派的特點始終是作為古典主義唐宋派的對立面出現的,始終是挑戰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的新生力量,是中國古典散文被遮敝的重要傳統,是推進中國古典散文發展的源動力,也是中國現代小品文的根和源。因此我們要特別看重魏晉文派反叛禮教、追求自由的精神、重情的精神和回歸自然的精神。
馬茂軍(1966—),男,安徽滁州人,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教育部社科規劃項目“宋代文話與宋代文章學”(09YJA751029)
2010-11-26
I207.62
A
1000-5455(2011)04-0039-05
【責任編輯:趙小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