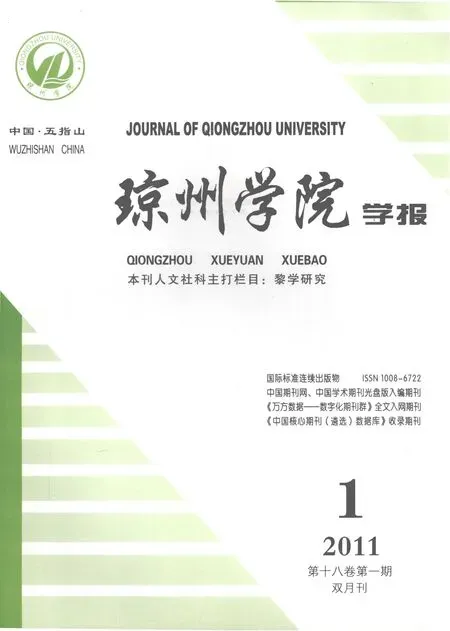索爾·貝婁小說《雨王漢德森》中的生態思想
寧 東
(廣東醫學院外語教研室,廣東 東莞 523808)
索爾·貝婁小說《雨王漢德森》中的生態思想
寧 東
(廣東醫學院外語教研室,廣東 東莞 523808)
本文指出美國著名作家索爾·貝婁的代表性小說《雨王漢德森》自始至終貫穿著強烈的生態意識,是一部充滿生態關注的典范之作。
索爾·貝婁;《雨王漢德森》;生態思想
茉莉·司達克·維亭 (Molly Stark Wieting) 在其論文“索爾·貝婁小說中田園風光的象征功能”(The Symbolic Function of the Pastoral in Saul Bellow’s Novels) 中 認 為 :“正如城市的混亂如鏡子一樣反映了貝婁主人公的個體分崩離析的生活,‘一個田園風光的范式’,借用威廉·安普生的用語,象征著它的另一面—精神的完整,秩序,和平靜”[1](P81)。自然在貝婁的作品中作為相對于城市的美好的存在,作為人的精神的歸宿,這本身便反映了貝婁一種生態主義的立場。當然這種立場在其小說中得到了細化的描述。本文意圖通過對貝婁小說《雨王漢德森》進行分析,揭示該小說作為充滿生態關注典范之作的實質。
一、城市生活的焦慮和非洲生活的自由
《雨王漢德森》的生態意識首先體現為城市生活的焦慮和非州生活的自由的對比上。
在去非州之前,遠離自然的城市生活讓主人公漢德森感到異常的焦慮。在這里物質主義使得人與外部環境的關系變的扭曲與異化。人與別的生物的關系是一種純粹的征服與利用的關系。正如漢德森養豬就是為了賺錢,而這種關系對人本身沒有任何精神上的好處,只是使人更加感到生活的沒有意義。正如漢德森所言:“這些豬被殺死和被吃掉。它們被制成了火腿、動物膠、豬皮手套和肥料。那我又被制成了什么呢?對啦,我想,我大概被制成了象戰利品似的某種東西。象我這樣的一個人,是可能成為象戰利品之類的東西的。”[2](P24)漢德森的養豬業也成了人類對自然一種異化對待的象征。而他自己也被這種關系所異化。根據他的自我觀察,他穿著“豬皮手套和豬皮襪子”[2](P12)而豬成為了他的一部份。這表明了在人與自然的關系異化的情況下,人是很難找到自己的地位和身份的,因為自然這個良好的讓人審視自我的對象不存在了。小說中一個細節提到漢德森想用養豬的手拉小提琴與祖先交流卻怎么也做不到:
我用這雙手趕過豬,把公豬翻倒在地,把它們綁起來,閹了。現在呀,我是用這些手指一心想拉出美妙的樂聲。...拉出來的聲音就像摔雞蛋箱子那么難聽。[3](P34)
貝婁通過這個細節暗示我們:人如果缺乏了和自然的交流,抱著一種征服和利用的態度,人也會失去靈性的。這種沒有自尊,以賺錢為唯一目的,漠視自然的存在的生活方式顯然使得漢德森感到窒息和焦慮。他大聲斥責道:“象我這樣一個丘八式的人物要這么些錢有什么用!”[3](P26)
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必然影響到人與人的關系的不和諧。當人們不關注自然只關注錢和自身的利益和舒適時,爭吵變得不可避免。漢德森與其妻經常吵架,與鄰居的關系也不好。有論者指出“漢德森與陌路相逢的人、鄰居、妻子有意地打架、吵鬧、甚至無理取鬧,似乎在致力于讓人們意識到他的存在”[4](P87)。確實如此,當生命為物利和細節所困時,人對自身的身份會產生強烈的懷疑,此時若又沒有大其心以察天下的自然情懷,沒有效法自然尋求解脫的能力,人就容易走進思想的死胡同。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漢德森在非洲的生活。在這里人與生物的和諧相處給漢德森一種自由的感覺。在阿內維(Arnewi)部落,人們養牛愛牛,把牛當成他們的家庭的成員和孩子。正如漢德森所描述的那樣:“阿內維人對牛的情況非常重視,他們并不把牛視為家畜,而是或多或少地把它們當親屬看待。這里是禁食牛肉的。他們放牛不是一個娃子看一群,而是每條母牛都有兩、三個放牛娃跟著。一旦牛受了驚,娃子們就追上去,哄它一番。大人們就更愛護生畜了。”[3](P54)在這個對自然的關愛無所不在的地方,漢德森與別人的交往也顯得容易和親近。他的身體的潛能在自然的環境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與伊特羅親王的摔跤中,他展現了自己的力量和美德,贏得了對方的尊敬。而與該部落威拉塔女王的見面則是漢德森向自然學習的一個難得的機會。在漢德森眼中,部落的女王如同大地之母一樣偉大,漢德森說:“我深信女王只要愿意,肯定可以給我指點迷津,這時她好像隨時都可能張開手掌,給我指出事物的實質及其原因。”[3](P87)而見到超凡脫俗的女王,漢德森覺得“一切煩惱、焦慮、不安和傲慢似乎都從我身上消失了。”[3](P88)
二、阿內維部落之旅的啟示:人應與自然和諧相處
漢德森在阿內維部落的最大收獲是他學的了人與自然應該和諧相處的生態思想。
這種思想首先體現在他與阿內維部落的女王對話中。女王首先談了人與世界的關系。女王說:“世界對小孩來講是陌生而新奇的”[3](P93)。這句話的含義是人應用一種童真的心態來面對世界和自然。對自然應有一種包容和和諧共處的態度。而以往漢德森是一直想征服和利用世界,把自然當一種敵對的力量來對待,顯然是錯誤的。大人們想征服自然,然而人的死亡乃自然的規律,是不可戰勝的,人因此而恐懼。正如漢德森所言:“世界對于小孩來講,也許是陌生而新奇的,……小孩只會感到驚奇,而成年人則主要是畏懼.為什么呢?這是因為有死亡。”[3](P93)因而,從死亡的恐懼中解脫出來,必須要有兒童的心態,要善待自然。不要把人與自然之間的斗爭看做你死我活的斗爭,也無須把死亡當做生命的終結。而應該在有生之年去體會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從小我走出來,達到精神的升華。其次,女王談了一個基本的道理“人總是要活下去的”[3](P94)人要珍視自己的生命,因為生命乃自然的禮物。漢德森先前的悲苦的根源乃是在由于他的思考被物欲所困。當人的思考為物欲所困時反而漠視了生存的可貴。因而老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人應把注意力由物欲轉移到發現生存本身的可貴上面來。因為人的生存是依賴于整個自然的恩澤的,活著人便要學會感恩。在女王的教導下,漢德森的心靈得到了解脫,在阿內維部落,他感覺“腳下有一股超人的強大力量”[3](P111)。
這種人應與自然和諧相處思想還體現在漢德森炸水塘的事件中。因為阿內維族的池塘里有一群青蛙,阿內維族出于對水中動物的尊敬沒敢去碰池塘里的青蛙和水,導致了部落的牛沒水喝。漢德森沒有意識到人和自然和諧的重要性,沒把青蛙看作自然界中無害的與人類平等的生物,貿然地想用自制炸彈炸死青蛙來拯救部落的牛,結果是把青蛙炸死的同時也炸壞了阿內維人賴以生存的水源,引起了災難性的后果。漢德森親眼目睹了這一凄慘的情景:“不過幾分鐘,我就看到(真叫人難受!)水塘底露出的黃泥和沉在塘底的一些死蛙。對青蛙來講,死亡只不過死剎那間的事,一下子就完了。可是當地的老百姓、不樂意走開的牛群,卻為那池流失的水而悲傷!”[3](P120)這件事讓漢德森牢牢地記住了自然的教訓。他后悔莫及:“‘天哪,這是怎么回事啊?’我對他們說。‘這是大破壞。我一手造成了這一場災難’。”他對該部落的伊特羅親王說:“伊特羅,殺了我吧!我只剩這條命可以用來抵償啦……”[3](P120)。最終漢德森帶著自然的教訓離開了阿內維部落。
三、瓦利利部落之旅的啟示:人應效法自然
在瓦利利部落漢德森學到了人應效法自然的生態主義思想。
人應效法自然首先是自然有著人的理性所無法理解的奧秘。這是漢德森在幫助瓦利利人求雨的過程中學到的。一開始漢德森根據他在文明社會得到的知識判斷瓦利利族人求雨是白費功夫。當瓦利利族人在準備求雨儀式時,他跟達孚國王打賭天不會下雨。他滿懷信心地向達孚國王指出:“太陽在天上還是亮光光地照著,而且一絲云彩也沒有。”[3](P195)國王向漢德森指出大自然是神秘和不可預測的,從表面人永遠無法把握自然的本質。他說:“你的觀察,從各方面看都是正確的。我不同你爭論。不過嘛,我曾經看見過在各種希望都落空的時候,就象今天這個樣兒,天卻下起了雨”[3](P195)。為了反駁他的觀點漢德森開始采用科學的解釋來談論雨的問題,引用《科學的美國人》的幾種關于下雨的觀點,認為“在下雨的問題上,我是在行的”[3](P196)。而事實證明漢德森是錯的。雨最后在漢德森搬動云彩女神后如洪水一般傾瀉下來。而且在搬動云彩女神的一剎那,漢德森便感到了自然的神秘。他感覺到“她身上散發著一個有生命的老年婦女的氣味。說真的對我來說,她是個活人,而不是偶像”[3](P212)在搬動云彩女神像后,他感覺到了莫名的快樂,他感覺到“我的精神復蘇了,它迎來了新生”[3](P213)。
人應效法自然其次還因為人有自身的不足,需要向自然學習來彌補。這是漢德森在與瓦利利族的達孚國王的交往中學到的。達孚國王認為,人的精神和肉體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肉體影響思想,思想影響肉體,然后反過來又影響思想,再次轉而及于肉體”[3](P261)。而人的精神和肉體是離不開大自然的。他認為“大自然是一個奧妙的模仿者。由于人為萬物之靈,所以人是適應環境的大師”[3](P261)。一個人要成其為偉大就必須模仿自然改善自身的不足。他向漢德森指出:“你的意識傾向于自我隔絕。這就使你極度緊張和萎縮不前。”[3](P292)他鼓勵漢德森去模仿獅子,在精神上向大自然學習,以便變得更有勇氣。他認為人應融入自然,方可改善自身。他指導漢德森放開心胸去體察自然:“現在你是一頭獅子啦。思想上要想象著自然環境。天空、太陽和叢林中的生靈萬物。你和這一切都密切相聯。那些小蠓蟲都是你的堂表兄弟。天空是你的思想”[3](P294)。在達孚國王的引導下,在向獅子的學習過程中,漢德森的內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學會了獅子的吼叫之后他開始便得更有勇氣和樂觀起來。他認為“我的思想正促進著另一個新人的成長”[3](P302)。
雖然由于達孚的死漢德森不得不離開非洲,無可否認的是他正是在非州完成了對外部世界的全新認識,而非州之旅是一趟生態發現之旅。正如他在小說最后所悟出的道理一樣:“四季、星辰那一套,還有潮汕……你都得和它們和平相處,因為如果它來找麻煩的話你是斗不過它的,你不可能戰勝它。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永遠如此。”[5](P360)而人只是整個生態系統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什么是宇宙啊?很大。那我們又是什么呢?很小。”[5](P359)
從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雨王漢德森》自始至終貫穿著強烈的生態意識,是一部充滿生態關注的典范之作。
[1]Gloria L Cronin,L.H Goldman.Saul Bellow in the 1980s[M].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
[2]Saul Bellow.Henderson the Rain King[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59.
[3][美]索爾·貝婁.雨王漢德森 [M].諸曼譯,章綺偉校,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4]修立梅.從“我要”出發試析雨王漢德森的精神危機[J].國外文學,2003, (4) .
[5][美]索爾·貝婁.雨王漢德森 [M].毛敏渚譯,張子清校,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Abstract: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which is a representative novel of Saul Bellow who is a famous American writer,describes the anxiety of city life which is far away from nature and the freedom of the trip in Africa which is close to nature.There is a deep sense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novel and the novel is typical in ecological concern.
Key words:Saul Bellow;Henderson the Rain king;ecological thinking
Ecological Thinking in Saul Bellow’s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Ning Do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Dong Guan 523808)
I06
A
1008—6772(2011)01—0087—03
2011-1-13
寧東(1974-),男,廣東湛江人,廣東醫學院外語教研室教師、文學碩士,研究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