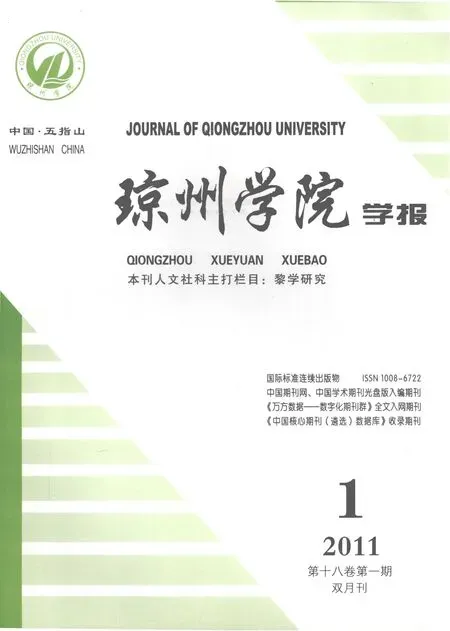從原型—模型翻譯理論看典籍英譯的意義
趙聯斌
(山西長治學院外語系, 山西 長治 046011)
從原型—模型翻譯理論看典籍英譯的意義
趙聯斌
(山西長治學院外語系, 山西 長治 046011)
本文的研究表明,典籍英譯的標準其實是適合與忠實,這種翻譯標準給譯者在英譯典籍過程中的權限提供了很大的空間,譯者并不是被動模擬,而是基于忠實基礎上的主動模擬。
原型—模型翻譯理論;模擬;典籍英譯
在原型—模型翻譯理論中,譯者的翻譯行為被界定為模擬行為,這一模擬行為不是任意的,而是以忠實于原語文本(即原型)為基點,以適合于譯語文本(即模型)讀者為目的的主動行為。(趙聯斌,劉治,2009:253)
一、典籍英譯的本質屬性
《辭海》對“典籍”所下的定義是:典籍,國家重要文獻。《盂子·告示下》,“‘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受宗廟之典籍。’趙歧注:‘謂先祖之法度之文也。’亦統稱各種典冊,書籍。”(《辭海》,1997:667) 著名翻譯家汪榕培先生指出,典籍翻譯是一項高投入、低產出的事業。(汪榕培,1997:120) 高投入,是由典籍英譯本身的特點決定的。首先是“理解”的困難,中國文字言簡而意豐,中國古代的思想博大精深,有的則是深奧玄妙,甚至妙不可言,如《周易》、《道德經》等,這就給當代譯者正確的理解原著的意旨帶來諸多困難。其次是“表達”,我們用現代漢語翻譯這些作品時,如果想表達原著的神韻和語言的優美都存在許多不易,何況是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字之間進行轉換,其難度就更大了。很顯然,典籍翻譯是對譯者要求極高的藝術,使一些意欲從事典籍英譯的許多譯者望而卻步。所以,如果不是出于某種目的,譯者很少加入翻譯典籍的行列,也很少愿意為此付出沒有意義的勞動和身心投資。低產出,是因為當今翻譯作品市場上,多為迎合大眾口味的作品,極少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典籍譯作,因為讀者群太小,其讀者僅局限于研究翻譯的一些學者和一部分外國讀者。因此,有的典籍作品經過譯者嘔心瀝血翻譯出來,卻很少有出版社問津,從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典籍英譯者的積極性。譯者因此即便介入翻譯典籍,也是為了滿足研究翻譯的學者和部分外國讀者的閱讀和研究需求而去做的,而這些讀者恰恰對譯語文本有很高的要求,任何不忠實于原語文本的翻譯行為都會削弱中國典籍的研究力度和宣傳力度。因此,典籍英譯的本質屬性是譯者對中國典籍的一種以適合于某種讀者群為目的的基于忠實的模擬行為。
中國的典籍具有濃厚的本國文化的底蘊和色彩,它們能否如實的移譯到“他者”的文化之中而不失其氣韻和神采,一直是典籍英譯的焦點問題,與之相關的則自然是可譯性的問題,既然文化與文化之間存在著巨大而不可逾越的異質性,對典籍這種濃縮著一族文化精華的文本是否具備翻譯的可能性便提出了質疑。
由中國典籍本身固有的屬性所決定,典籍英譯本質上是中國典籍的模擬者基于某些讀者群的需求,在忠實于中國典籍這一原型的基礎上,對中國典籍進行的一種模擬,試圖產生適合于譯語讀者的模型。典籍英譯的本質屬性是模擬性,譯者的行為在典籍英譯中實際上表現為一種模擬行為,譯者所遵循的翻譯標準實際上是一種模擬標準,即是以忠實于中國典籍為基礎,以適合于譯語讀者為翻譯目的。
二、典籍英譯的翻譯策略
在原型—模型翻譯理論看來,原文與譯文的關系,既是傳統翻譯理論所主張的“模式-復制”的關系,又是互補的關系。按原型—模型翻譯理論的說法,是一種“共存”的關系。原型—模型翻譯理論與傳統的翻譯理論一致,都是以“原文-譯文”相對應為理論構架的,但卻不否認“原文”與“譯文”的區分。原型—模型翻譯理論關于翻譯問題的討論主要是圍繞著翻譯的模擬本質展開的。在這一理論中,趙聯斌提出了“原型—模型“的概念。盡管這一概念是首次用于翻譯理論研究,趙聯斌卻希冀在翻譯理論研究中能找到這一理論運用的普遍性。即譯者的行為是通過對原型的模擬產生模型。“模擬”,作為翻譯的本質屬性,他認為:“原型—模型論認為,從本質上看,各民族的基本語音組織形式也都是對人類呼吸的自然韻律的模仿,即模型。但是,這種模仿又是在各民族的邏輯-心理結構的調控下進行的。因此,各民族語言的基本語音組織形式又各有不同。”(張今,1997:18;張今、羅翊重,2002:559)
張今這一概念的提出為可譯性提出了理論根據,因為盡管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模仿方式,但仍然可能模仿同一個事物,可以借助翻譯互相溝通。其實早在張今之前,在三世紀的圣哲羅姆(Saint Jerome) 時代,哲羅姆本人以及許多基督徒就已認為人類的所有語言都來自于一種原初語言(Ur-language)。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30年代初期,德國的浪漫派作家和文論家就提出了與張今的理論極為相似的“無限相融”的翻譯主張。德國的浪漫派打破了將藝術分類的做法,認為應該把詩歌、哲學、文藝批評乃至自然科學彼此融合起來,抹去它們之間的界限,還其“無限相融”的本質狀態。按照這一原則,真正意義上的語言是沒有內容的純形式,(即張今所說的“思維結構的模仿”)。由于各個文藝學科的界限被打破了,便構成了“普遍可譯性”,在這一狀態下,詩便是將自然語言轉換成藝術語言的一種翻譯。而所謂的藝術語言,則是以形式為第一的語言,它通過對一般客觀語言原貌的“疏離”,改變人們對它的感覺方式,使之獲得一種新的、陌生的詩意效果。這一主張以及張今的“模擬”理論給我們的啟示就是,翻譯,尤其是蘊涵著豐富文化符號的典籍翻譯不應糾纏于“意譯”或“直譯”的狹隘語際翻譯之上,而應該從文化的視角看重作品的內在本質、意義和氣勢。“模擬”理論所鼓吹的不僅是單純的模仿,而更要有所創造。
因此,在典籍翻譯中,最高的境界應是追求將自然語言轉換成藝術語言的一種嘗試,翻譯策略應力求挖掘作品的隱含意義和藝術內涵,而不僅僅是單純停留在語義層面上的模仿,只有通過詩意的自由的創造,才能擺脫單純“轉換翻譯”的束縛,使漢語語言文化滲透到他者文化之中,并與之相互融合。
三、典籍英譯的操作方法
典籍英譯與其他任何翻譯在操作層面上都涉及具體的方法論問題。傳統的方法不外乎圍繞著“意譯”或是“直譯”,各執一詞,爭論不休。然而譯者若借鑒“模擬”的理念,把焦點放在原型語言的內涵上,而不是字詞的意義上,或許能對上述兩種極端完成一次方法論上的超越。趙聯斌認為(2009:260) 翻譯是關于模擬的實踐。但他所指的模擬不是文本語義層面上的模擬,而是文本擴大讀者群的生命意義的延長;翻譯是模擬、共存,目的是從多種語言形式中尋求更多的讀者群。倘若按照“直譯”與“意譯”的原則,譯者在翻譯時所懼怕的是什么東西應當保存,什么東西應當丟失的問題,而趙聯斌的看法卻不同,她認為我們所懼怕的應是文本是否能在其他多種語言中存活,這才是“翻譯”在詞源學上的原初意義。一個生命體能在新的環境中重獲新生,它自然與從前的狀態有了脫胎換骨的差異,這是不爭的事實。
威克利夫(Wycliffe) 翻譯的英文版《圣經》對Enoch的描述就在延續生命、適應新環境的意義上使用了“translate”一詞:
Bi Feith Enok is translatid,that he shulde not see deeth,and He was not founden,for the Lord translatide him.
在這段中,“to be translated”就意味著“生命的延續”,是從地球“translated”到天堂,也就是又一次新生。這一轉變是巨大的,不僅是生理的,而且也是地理時空的,也就是原本存在的X,如今又開始適應新的環境,而變成了Y。
雖然我們今天只保留了“翻譯”一詞從一種語言轉換為另一種語言這一個層面的意義,但其原初的意義仍在我們的潛意識中起著作用,那就是“一個事物越過一個鴻溝,……到達一個它從未存在過的地方。……(翻譯一詞)的意思雖已被‘精神化’,……但客體或地理上的分離仍是潛在和隱含的”(參見趙聯斌,劉治:2009)。
既然翻譯是前往“一個從未存在過的地方”,詞對詞、字對字的翻譯就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手法,因為此地之詞、字,乃至句子在彼地未必“存在過”,硬是生硬地“遷移”過去,浸染彼地文化的人未必能接受,反而會達到拒斥和不知所云的效果。桑塔格同原型—模型論觀點相似,所倡導的顯然是文本的“再生”、傳播和延續,而不是構建文本之間的語義轉換機制。當然不可否認,這種轉換機制肯定是存在的,否則文本就無法完成向“不存在的”彼地的遷徙。
既然文本的“再生”和延續被提升到首要的位置,那么原型—模型翻譯理論認為翻譯操作方法就是多元互補,而不僅僅限于語義層面的似與不似。在原型—模型翻譯理論中,翻譯的本質是模擬,模擬的必要性驅使譯者必須采用適合于譯語讀者閱讀風格但又必須忠實于原型的翻譯方法。譯者的模擬手法之一是“氣質模擬”(General Imitation),即譯者的任務是提取原型的內涵實質,避免模型的不忠。這在典籍英譯的初級階段極為重要,其前提就是在啟蒙、澄清的基礎上,文本還將面臨著未來的重譯。氣質模擬未必一定是全譯本,也未必在詞義上銖兩悉稱,其意圖旨在引發興趣,為以后大規模的翻譯傳播做準備。
原型—模型論提出的第二種模擬手法是“改造模擬”(Adaptative Imitation),“改造”不僅僅是指靈活的使用語言追求“神似”,而是有意識地模擬出另一種文本(version)。其實在古英語中,“versionist”的意思就是“翻譯者”,可見翻譯中的改動也是可行的一種方案,尤其在翻譯詩歌方面,歷史上諸多中外詩人都不愿受到“準確性”標準的限制,因此不使用“翻譯”一詞,而更愿意使用“改編”或“版本”的說法。原型—模型翻譯理論認為“模型”大概是對“改造”結果最好的詮釋,倘若美國詩人羅威爾(RobertLowell)來做翻譯,他所譯的“版本”(version)肯定是一首新的、有價值的、由他而“創作”的詩作模型。
原型—模型翻譯理論的第三種模擬手法是“定型模擬”(Conclusive Imitation)。原型—模型翻譯理論認為這是“改造模擬”翻譯的結局階段。從翻譯效果的角度來看,它是模擬翻譯的終極結果。波德萊爾對愛倫·坡詩歌的翻譯就大大豐富了愛倫·坡詩歌的美感和內涵。二戰之后的幾代德國學者也都公認施萊格迪克(Schlegel-Tieck)翻譯的莎士比亞比原著要優美得多。
四、結論
原型—模型翻譯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在全球化的消費時代,任何文化產品(包括中國的典籍) 的生產必然無法擺脫商品的運作規律。文化交流的主旨首先在于要使自己的產品(典籍)最廣泛地讓他者文化中的讀者所接觸,這樣才能給予典籍以“再生”的生命,使其延續擴散開來。為此,傳統意義上的僅局限于“直譯”、“意譯”層面上的翻譯模式已不再能適應當今社會的需求。典籍英譯的重心應從文本轉換技巧轉移到如何使文本在西方市場上吸引最大量的讀者群、從而獲得“再生”的戰略之上。出于這一考慮,在具體翻譯策略上就應采取多元互補的手法,而且把反復重譯作為必然的目標。“十年磨一劍”、追求絕對完美譯文的思維定勢只是一種烏托邦的理想,一種已被原型—模型翻譯理論所顛覆的追求中心意義的本體論范式,為此,典籍英譯工作應努力超越這一范式,使自己的產品優質而快速地進入跨國資本文化的流通之中,達到弘揚中國文化的目的。
[1]郭建中編著.當代美國翻譯理論 [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2]趙聯斌,劉治著.原型—模型翻譯理論 [M],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Abstract: The study of essay shows that the criteria of the classics translation is in fact“Faithfulness and Fitness”,which gives a large room for the translator.The behavior of the translator is not passive but activ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The aim of the classics translation i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target text readers’.
Key words: Prototype-Model Translation Theory;imitation;Classics Translat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lassics Translation from the Point of Prototype-type Translation Theory
Zhao Lian-bin
(Foreign Department of Changzhi University,Changzhi Shanxi 046011)
H059
A
1008—6772(2011)01—0112—03
2011-1-6
趙聯斌(1976-),男,山西黎城人,長治學院外語系講師、碩士,研究翻譯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