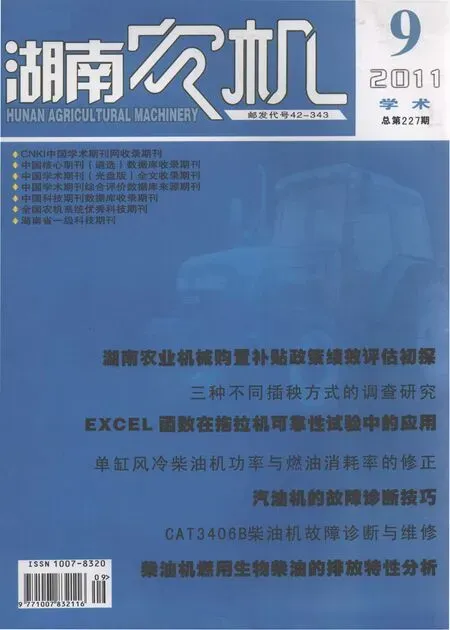以對話的視角淺析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沖突
蔣一扉
(四川現代職業學院 法律系,四川 成都 610207)
1 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
傳統的國家法讓我們通過法律去看社會,而民間法的提出可以讓我們反過來通過社會去看法律,使我們深入到法律內部去洞察它的本質問題。當然,在這其中,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問題是無法回避的重要方面。民間法與國家法的緊張關系,集中體現并主要爆發于各地各級法院法官的辦案過程中,即民間法與國家法在不同區域間、不同民族間的調控力量的對比關系,主要通過各地各級法院法官在處理各類民事、刑事案件中對法律方法的運用而得以實現。民間法與國家法二者之間的沖突,實質上就是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也就是中西法律文化在歷史與現實中的沖突。國家的控制能力再強,甚至即使每個社會成員都成為國家這架機器上的 “螺絲釘”,也不能徹底銷蝕社會自治力量的客觀實存。
《馬背上的法庭》這部影片真實記錄了我國西南邊陲少數民族地區的糾紛處理方式以及當地極具特色的風俗習慣。筆者在這里就順著影片的思路繼續開始列舉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少數民族的案例。
四川涼山彝族。在債權債務關系方面,由于當地彝族的社會契約觀念不發達,租佃、借貸一般采用口頭方式,即使是重大交易,也是多采取由第三人在場的方式,很少用書面形式。在婚姻家庭方面,根據彝族當地的習慣法,訂婚是婚姻成立的必經程序,標志著婚約成立,對雙方均具有嚴格的法律約束力。另外,彝族人對于沒有明確證據或無法決斷的疑難案件,如重大的偷盜案件未能當場抓住竊者或沒有其他物證,或者糾紛通過其他手段無法解決的,則交由畢摩(彝族掌管宗教事物的神職人員)主持,通過神明裁判解決。
云南布朗山布朗族。布朗族的村社頭人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當許多家族聚在一起組成一個村社之后,為了便于管理公共事務,村社成員共同推選出幾個頭人作為村社內外事務的管理者和代表者,村社的日常事務都由頭人管理,對內對外的重要事情由頭人會議做出決定。大會所做的決定,村社成員都不得違抗。另外,當村社接受新遷入戶或同意遷出戶時,都必須通過村寨頭人達曼和其他頭人的同意方可生效。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布朗族各層次的頭人之間以及他們與普通族人之間都初步形成了等級關系,并根據自身職權所確定的地位不同,產生一定的從屬關系,這樣會在某些方面造成特權主義以及利益沖突關系。
貴州苗族。苗族在歷史上是沒有文字的,傳統的議榔規約沒有文字記載,但是盡管這樣,大量的習慣法還是長期存留在當地人們的記憶中,規范著人們的日常行為。這些習慣法是依靠苗族特有的被稱為“理詞”的一種口傳形式傳承著。根據其傳誦的內容,可以分為佳和理兩部分。佳是人們在日常生活、生產勞動以及處理人際關系、判斷是非曲直的重要依據;理是行為規范,是從一些公眾認可的傳統樸素的倫理道德、禁忌及生產和生活習慣中總結出來的規范,它通過寨老組織的強制和社會輿論的監督得以實施。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在少數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若出現了糾紛和矛盾,他們的解決方式往往是獨到的,甚至有時是與國家現行法律相沖突的,基于血緣關系、地緣關系,生活在“小傳統”中的民間法,它在鄉民長期的生活與勞作中逐漸形成,并在鄉土社會中調整著鄉民之間的關系和鄉村之間的秩序。民間法常出于自然,人們在生活中甚至都沒有認為那是一種來自“法”的約束,因為這些鄉規民約已經慢化為人們生活中的組成部分,當他們發生糾紛時,會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這些規則、范例。“山西之煤窯、四川之鹽井、浙江之漁業、嶺南之沙田、華北之平原、閩南之山地、兩湖之丘陵、江南之水鄉,各有其法。”究竟這其中的原因和解決對策分別是怎樣的,筆者將試以建立二者對話的角度從生存土壤、發展脈絡、形成傳統、知識結構、主體需求、實施成本等幾方面進行分析和考察。
2 沖突發生的緣由:“對話”的缺乏
(1)生存土壤——“對話”產生的根本。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的,反映著統治階級(即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意志的規范系統,這個定義在某種意義上僅指國家正式制定法這一領域,在人們的認識中甚至會將其歸置于法律條文這一更加狹小的范疇之中。這就注定國家法的生存土壤是普適而具有權威性的,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一表述,就極具威懾力和統一性。
與國家法不同,民間法的生存土壤顯得更為復雜。我們同樣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條文來舉例,總綱中第四條第三款、第四款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從這里的表述我們可以看出,少數民族地區是有其特殊性的,國家制定法在這些地區中實施時應考慮其相應的民族習慣和風俗,同時尊重當地民族自治的一些問題。
國家制定法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一步一步建立和完善起來的,代表著國家法治的動向,是對國家法治進程的表述。國家制定法往往都是進過嚴密論證后確切表述出來的,無論從書面還是實踐方面都具有其科學合理性。民間法產生于民間,發展于鄉土,穩定于人心。民間法是一定范圍內的人們在長期生活中約定俗成的行為規則的總稱,它的生存空間更多的是在于鄉土社會中,它是人們社會實踐和生活秩序的客觀需要,在特定區域對一定的人群和組織具有制約效力,同時,民間法主要依靠人們的情感認同與價值取向來發揮效力,從而調節人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正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孕育國家法與民間法的土壤是不同的,它們帶給我們對法律的理解角度也是不同的,從這一點上說,這是國家法與民間法產生沖突的根本之所在。
(2)發展脈絡——“對話”的外在表現。國家法從較為嚴格的意義上來追溯是上個世紀法學精英們構建起來的一個概念,是在西方法學家唇槍舌戰中產生的,也是一種新的法學理念的表現形式。作為從傳統法律秩序向現代法律秩序過渡中的我國來講,國家法的產生和發展是離不開國家強制力和政府系統的規制的。國家法是現代法治的重要體現,誠如我國法治十六字方針中所說的“有法可依”,國家法是法治建設中不可或缺的前提要件,同時也是時代發展的產物。
而作為民間法,它首先是源于民間,是民間習慣、風俗等的聚合體,它代表著某一地區鄉規民約的方向,它的發展是建立在對其不斷發掘、整理以及繼承的過程中的,不像國家法是在社會推進以及國家需要中建立和發展的。在這里,筆者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如國家法的修訂工作,之所以會不斷產生各部門法的修訂草案,是因為國家法在不停地迎合社會需要,并且是盡力去保障整個法治進程的有效推進,而民間法并沒有更多的修訂工作,因為它是在長期積累中約定俗成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將其印入腦海,并且將其固定下來形成一個地區普遍認可的規范去遵守。
國家法與民間法不同的發展脈絡,前者是在時代需求中發展,后者是在約定俗成中穩定,這可以說是國家法與民間法兩者在其表現形式方面的沖突原因。
(3)形成傳統——“對話”的淵源基礎。美國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在其著作 《農民社會與文化》中提出了大小傳統的概念,所謂大傳統主要是指以城市為中心的、由社會上少數上層人士、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而小傳統則是指存在于農村社會中,以農民為代表的文化,是一種具有地方社區和地域性特色的文化傳統。謝暉先生將大小傳統的概念帶入了國家法與民間法的研究領域,將國家法引申為大傳統,而把民間法比作為小傳統,進而論述了大小傳統間沖突的必然性:這種沖突的必然性取決于大小傳統各自所依賴的主體——國家與社會、所代表的利益——權力與權利、所表達的人性——社會性與個體性之間的對立。也許就是因為這大小傳統的緣故,國家法與民間法從淵源上來講就是有沖突的,國家法出于倡導一體、統一與權威的大傳統,而民間法出于帶有濃厚地方特色的小傳統。國家法主要來自于各部門法的一個聚合,因而國家法的表述方式側重于嚴格精準,而民間法主要來自于鄉土民間的習慣、約定、風俗等,它則更偏向于通俗易懂。
傳統不僅僅代表著過去,它更多地也指向了現在,傳統在我們的腦海中是一種過去式的固化,然而它深刻的內涵告訴我們并非如此,它是活在我們身邊的,是在不斷吸收與借鑒中發展的,從這一方面講,民間法受此影響較之國家法會更大一些。民間法中很大一部分是一種對古代“禮”的新詮釋,這就與民間法由來已久的“鄉土本色”的傳統是分不開的。費孝通先生說過,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在鄉土社會中大家從熟悉中得到了信任,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在這樣的環境中,如果一味去追逐國家法的腳步,似乎就很無情地抹煞了人與人之間的那種質樸的情感,從而也會讓本不屬于這片土地的“陌生感”生根發芽。
“禮”與“法”的傳統在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中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在大小傳統的各自呼吁下,國家法與民間法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國家法彰顯著一個國家“法治”的理念,而民間法多了一份“人性化”的魅力,可以說兩者發生沖突的淵源基礎就在于形成傳統的不同。
(4)知識結構——“對話”的主觀要求。“對法律的理解,更多地取決于一個人對生活的體驗,而不是對法律條文的熟悉程度。”“法律知識是通往認識法律之路,而非理解法律之橋。”尹伊君先生這兩句話真切地道出了理解國家法與民間法的不同之處。國家法作為正式制定法出臺,它是國家權威的象征,若要準確認識它的內涵與外延,要求認識主體應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否則只會停留在對其法律條文表面的閱讀,而無法洞察其本質所在。而作為認識民間法的主體,相應的條件要求則沒有如此苛刻,因為民間法本是一種“民間記憶”,是一種地方性秩序的表征,這與奧地利法學家埃利希筆下的“活法”不謀而合,他要求人們不要把法律僅僅視為國家的官方機構發布的規則,應把法律看成是由社會團體創制,并從那里獲得了相應的權威。埃利希的法社會學要求人們研究社會本身,“無論是現在或者其他任何時候,法律發展的重心都不在立法、法律科學,也不在司法判決,而是在社會本身。”所以當真正要去認識和理解民間法時,認識主體應當具備更多的社會經驗和更為扎實的社會閱歷,而不單單是專業的法律知識。
基于認識主體的知識結構不同,有些人較為偏重于對專業法律知識的修養,有些人則重視社會經驗的積累,他們在認識和理解法律時就會發生主觀接受的側重點不同,久而久之在研究國家法與民間法時就會有其不同的主觀意識滲入,從而形成不盡相同的觀點與態度,這是國家法與民間法產生沖突在主觀認識方面的原因。
(5)主體需求——“對話”的主體利益。國家法作為“國家之法”,民間法作為“民間之規”,它們在主體需求上也是不同的。國家法隨著時代的變遷,更多的是側重于對現代的需求,故而多了一分法律的理性;民間法因為生于民間長于民間,它較為偏向于對傳統的保留,我們可以說它更多地是被賦予了一些感性,就像弗里德曼曾說過的:“違反大家感情和道德愿望的法律很難執行。”
國家法因其權威性的保證和形式嚴格性的要求,還有近來國際社會中全球一體化理念的沖擊,它需要跟隨時代的腳步,與其他國家的法律進行交流,然而在交流中相互滲透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加之其自身的國際化要求,國家法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種極具現代性的發展狀況。民間法作為一種自給自足的本土資源,基于民族語言文字的特殊性和尚有差異的經濟發達程度,它在特殊的地區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它的地區性和民族性并不能完全融入國家法這條“準繩”之中,使它只能“占一地之優”,而無“顧全大局之力”。盡管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人類文明不斷取得進步,人類在與自然的斗爭過程中也對宇宙與自然有不斷提高的認識水平,但仍然存在很多無法破解的東西,尤其是在農村地區,農民的知識素養較為低下,受現代文明的沖擊和熏陶相對有限,因而在認識和理解法律時會受此影響,同時對法律的需求也是僅僅圍繞著自身的利益來談論,這是與現代國家法日益發展的趨勢不相吻合的。
國家法與民間法在主體需求上發生沖突的另一方面是由其各自內部主體的需求沖突所引起的。舉個例子來說明,近些年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于經濟利益的渴求日益增強,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對周邊的法律秩序也就耳濡目染,最現實的例子莫過于農民工工資的問題,他們通過正規的訴訟渠道有效保障了自身的合法權益。這樣當他們結束在城市打拼的生活之后回到農村時,若再發生類似的經濟糾紛,他們腦海中會出現法律的印記,從而運用法律來保護自身的權利,而拋棄了原本對其行之有效的鄉規民約。這就是鄉土民間中的規范在遭遇國家法時在其自身內部發生的沖突,也是源于其主體的需求發生轉移這一現象發生的沖突。
(6)實施成本——“對話”的經濟考究。“訴訟對于有錢人來說是高昂的獎券,對貧窮的人來說是權利的否定”,邊沁這一論述似乎已經道出了訴訟成本的真諦,這也是世界各國訴訟存在的一個現實狀況。嚴格而復雜的訴訟程序,高額的訴訟費用,較長的訴訟過程,這都是我們在訴訟之前要考慮的現實成本問題。
另外,與其他國家不同的還有我國傳統“厭訟”、“賤訟”觀念的影響,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人們訴訟的心理和社會的成本。國家法的實施主要依靠國家強制力的保障,給人們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威懾,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趨于緊張,而且一旦沒有處理好雙方的關系,很可能會出現我們所不愿看到的“冤家”、“仇家”的后果。而民間法作為鄉土民間生活的一種秩序維護,它是鄉民們所了解和熟悉的地方知識,同時也是有著自己的歷史和傳統優勢,它的實施主要依靠民間權威以及民間輿論,可謂是近乎零成本的權益維護體,是鄉民們所易于接受的習慣風俗。就民間法而言,它在國家法進入鄉土民間之前就早已存在,并且一直有效地使鄉村生活處于正常運行之中,這套制度對于正式法律制度來說是不太熟悉的,然而對于生活在其中的鄉民卻是耳熟能詳的,是人們社會交往和解決糾紛的重要手段。
權衡國家法與民間法的實施成本,人們在糾紛發生時會有選擇地偏向于低成本的民間法,而抑制了國家法的強制作用,久而久之就會在兩者之間發生無法回避的沖突。
[1]孫伶伶.彝族法文化——構建和諧社會的新視角[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張曉瓊.變遷與發展——云南布朗山布朗族社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3]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4][美]弗里德曼,李瓊英等譯.法律制度[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