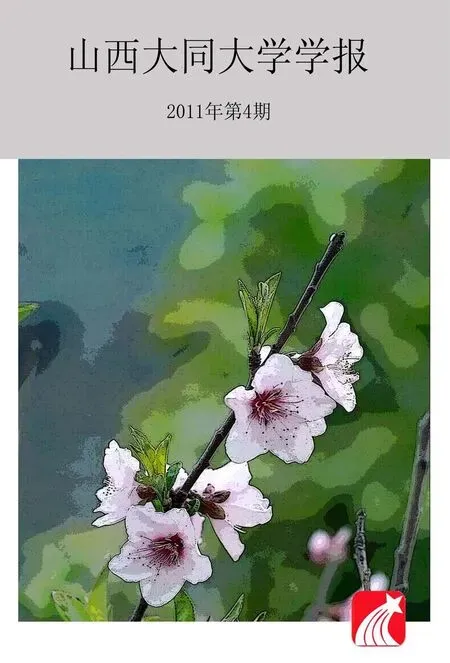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辦學思想及實踐之比較
劉保兄
(河南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河南 開封 475004)
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辦學思想及實踐之比較
劉保兄
(河南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河南 開封 475004)
20世紀20年代中國人被推上了基督教大學的領導崗位。在前途既不易推測,也無所依憑的情況下,各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結合自身成長經歷、所在學校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辦學思想及實踐。但又因他們所處環境的特殊性、時代背景的影響,他們又有著一個共同的奮斗目標,那就是創辦中國的基督教大學。正因為如此,他們推動了基督教大學的中國化發展,為西方教育模式的本土化發展、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辦學思想及實踐
20世紀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爆發以及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將中國人推上了基督教大學的領導崗位。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的新形勢下,應當確立怎樣的辦學目標?在辦學目標的指導下做怎樣的改革與調整?這些問題對于華人校長來說都是未知的。在這種“既不易推測,也無所依憑”的情況下,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通過自身努力,不僅成功地推動了基督教大學的持續發展,并且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辦學思想及實踐。在這各具特色的辦學思想及實踐中,華人校長們又有一個共同的追求目標,那就是創辦中國的基督教大學,積極探索西方教育模式的本土化之路。
一、各具特色的辦學思想及實踐
20世紀20年代中期之前,在華基督教大學無一例外地由外籍傳教士擔任校長,中國人在基督教大學中擔任要職的很少。20世紀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收回教育權”運動,以及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使基督教大學被迫將學校領導權移交中國人手中。為了民族利益,他們毅然擔負起了領導基督教大學中國化發展的重任,不僅維持了基督教大學的持續發展,更在辦學實踐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辦學思想及實踐。
以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為例,陳裕光1922年留學回國之后曾先后擔任北京師范大學化學系主任、教務長、校評議會主席,以至代理校長。1925年,教育部長黃郛有意聘陳裕光擔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但陳裕光志不在此,更愿做一名學有專長的教授,于是離開北京,回到南京,被母校金陵大學聘為化學系教授,翌年,又被任命為文理科長。1927年北伐戰爭中,南京受到沖擊,加以此前收回教育權運動的影響,金陵大學校長包文主動辭職,極力推薦陳裕光擔任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原沒考慮到“近因急需遵照國民政府私立學校規程立案,而立案須先選定校長,鄙人深恐立案問題,因本人之不愿就任,而生障礙,迫不得已,始尤勉力擔任”。[1]從1927年出任金陵大學校長,到1951年辭職他就,陳裕光前后掌管金大24年之久。在辦學過程中,陳裕光積極探索學校發展之策,形成了“教學-研究-推廣相結合”的辦學思想,并將之運用到學校各院系辦學實踐之中。
對于“教學”、“研究”、“推廣”三者之間的關系,陳裕光的解釋是:“三者扎根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卻又絕不是獨立的,很重要的還是三者之間保持著相互通力協作的密切關系。它們磨合修改,彼此補充,相互加強,循環往復,永不停息地向前推進著。我們有時稱之為‘三一制’,因為它們有既是三而又是一的歷程。”[2]在陳裕光看來,通過教學和研究,可以促進推廣工作的開展;而研究及推廣同樣可以充實完善教學內容,促進教學工作的開展;同理,教學及推廣過程中及時發現的問題,反過來也可以推動研究的發展。“三一制”制定后,很快被運用到包括文學院、理學院在內的整個學校教學工作中。在陳裕光的領導下,在正確的辦學方針指導下,金陵大學在基督教大學中始終保持了領先地位,并為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據統計,僅在陳裕光掌校時代求學于金陵大學、后來當選兩院院士的金大畢業生、肄業生就有18位之多。此外如原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彭珮云,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中國柑橘之父”章文才,臺灣原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臺灣著名詩人、散文家余光中等,都是陳裕光時代的金大學生。
再以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為例,他曾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并獲教育學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劉湛恩在美求學時期,正是美國進步主義教育、職業教育、平民教育等思潮興起的時期,其就讀的哥倫比亞大學,也恰是美國進步主義教育思想的圣殿,匯集了杜威、克伯屈、孟祿等當時美國最杰出的教育家。作為孟祿的弟子,劉湛恩受到了美國進步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回國后,他積極組織各地的公民研究團、公民宣講隊、公民演講會、公民訓練班等活動,初步形成了職業教育思想、平民教育思想。1928年劉湛恩被任命為滬江大學校長,時年僅33歲。受此前形成的職業教育思想、平民教育思想影響,就任滬江大學校長后,劉湛恩結合中國社會發展需求及滬江大學所在區域特點,在辦學過程中為學校制定了“聯合社會力量辦學”的思路。滬江大學地處工商業發達的上海,結合地區社會發展需求,劉湛恩為學校制定了“職業化”的發展道路。然而,發展學校職業化特色,需要大量充足經費的支撐。作為獨宗派基督教大學,滬江大學辦學經費一向不太寬裕,為解決這一難題,劉湛恩在辦學過程中逐漸摸索出一條與社會聯合辦學的發展之路。
與社會團體及個人合作,早在劉湛恩上任不久就開始試行。如1931年,滬江大學和時事新報館合辦“新聞學訓練班”,并“以時事新報之辦公室為講學研習之所,以時事新報同人為基本教師”,以養成新聞事業專門人才為目的。[3]滬江大學化學系得到上海化工巨子吳蘊初長期的大力幫助。而1932年創設的滬江大學城中區商學院的創辦更是滬江大學聯合社會力量辦學的典范。作為與正規學校有別的社會辦學方式,城中區商學院自身幾乎沒有專職教師,通常是由合作單位工作人員兼任;辦學經費完全擺脫對美國教會的依賴,而由合作單位籌集基金運作;學制靈活多樣,既有為高中畢業生設置的大學科,也有為中學程度者設置的專修科,以及不限入學資格的選修課。各科都采用學分制,收費按學分計算,學生可根據自己的時間和經濟條件選課,對于成績優秀而家境貧寒的學生,校方通過在社會上募集捐助給予減免學費的獎學金。城中區商學院適應了上海工商業發展之需求,獲得上海工商界的支持,畢業生在各機關團體及中等教育界頗受歡迎。到1936年,滬江大學城中區商學院學生達到600余人,滬江大學成為各基督教大學中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個。
除陳裕光、劉湛恩之外,其他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辦學思想及實踐也各具特色。如華中大學校長韋卓民為保持學校的基督化特色,為自己領導的學校制定了“小規模、高效率”的辦學方針,學校雖然始終保持較小規模,卻是華中地區教育系統的佼佼者之一。福建協和大學校長林景潤在引領學校發展過程中,結合福建協和自身的特點,瞄準福建地方需要,強調“滿足周圍人們的需要”,為福建省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基督化”的不同傾向
“基督化”是基督教大學的本質特征,面對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潮流以及中國政府的限制性規定,如何保持學校“基督化”特色,如何協調“基督化”和“世俗化”矛盾,就成為擺在華人校長面前的難題。面對難題,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選擇了不同的路徑。
一是堅持以基督化為辦學的核心思想,排斥世俗化發展。在他們看來,基督教學校的創辦目的就是服務于基督教精神的傳播,如果學校失去了基督化特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他們認為,“學院是作為中國基督教運動的一部分而創建的,為的是在中國人中傳播基督教,給教堂提供牧師,給教會活動的不同部門安排領導人員,幫助制定明智合理的政策,以便實現中國個人、社會的基督教式生活計劃,促進世界基督教文化發展”。[4](P153)為保持學校的基督化特色,在辦學目標上他們堅持以培養學生“犧牲、服務”的基督化品格為目的;在學校經費來源上,在不與學校基督化辦學目標抵觸的原則下,只接受少量的政府資助和其他捐贈基金,并且時時注意這些基金“無任何減少學校及其工作的基督教特色的附帶條件”;[4](P156-157)在教師的聘用、學生錄取方面,他們努力維持師生中的基督徒比例,并將學生規模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以利于基督教學校“家庭化”氛圍的保持;在課程設置方面,他們排斥世俗化的發展傾向,認為“我們不應再去迎合大眾的口味。我們應當了解基督教會的需要并且努力滿足這些需要”。[5]
二是兼顧中國社會發展之需要和學校的基督化特征,將世俗化和基督化融合一體。此類華人校長一方面有著堅定的宗教信仰,堅信基督教精神是拯救國難的良藥,積極致力于基督精神的傳播,在辦學過程中,無論是辦學目標的設定,還是課程的設置、教師的選聘、校園文化的營造,都強調其基督化特色的保持。另一方面,他們又出于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強調基督教學校當尊重中國政府的政策法規,主張教育發展要緊密結合社會發展需要,應政府要求、社會發展需要調適辦學目標及學校課程設置等。以劉湛恩為例,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對基督教教育在中國的前途深信不疑。他認為:“基督教教義,如日月經天。”[6](P46)在為學校制定辦學目標時,他將其確立為“更基督化”、“更中國化”、“更好的教育機構”。就“更基督化”方面而言,劉湛恩強調,要以“基督化的人格修養”為學校的培養目標之一。他強調“以為一個穩定的新中國可以僅僅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是謬誤的。沒有人格的知識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東西。所有真正愛國者所想看到和擁有的中國,是一個建立在既有知識又有人格上的中國,或換言之,建立在科學與宗教之上。”他聲稱:“滬江大學作為一所基督教學校,就是致力這樣的目標,使中國不但知識發達,而且道德昌明。”[7]在強調學校基督化特征的同時,劉湛恩也重視學校教育功能的發揮。在1928年2月25日的就職演說中,劉湛恩就明確提出,大學的三大使命為:(一)培養人才:培養有真實學識之人才,尤重培養有健全品格之人才。(二)研究學術:整理舊的學術,介紹新的學術,去糟粕,取精華,融合新舊,溝通中外,日取精進。(三)改造社會:學校須社會化,但學校望改造社會,并非視社會惡化。[8]劉湛恩對大學使命的闡述,反映了他對現代大學理念、大學功能的敏銳意識。在1936年制定《滬江大學政策》時他再次強調:“大學首先是一個教育機構,它必須體現真正達到大學標準的自由精神和措施。它必須在中國的各大學中獲一席之地。它所處的地位使它具有體現東西方最佳學術并充分表現人類最崇高的成就和期望的獨特機會。為實現這些目標,它必須運用所有合法手段使之成為最強大的教育中心。”[9]在強調學校教育功能的同時,劉湛恩也注重學校社會功能的發揮,強調學校要適應中國社會生活的需要。他聲稱:“我們想使我們的學校比以往更為切合中國的需要。我們將不是試圖達到某種歐美的水準,而是要達到適合中國的水準。在教學方法和教材上,我們將接受外國最好的東西,但也保持中國最好的東西,使所有的一切適應中國的特殊需要。”[10]
三是淡化學校基督化色彩,以基督精神辦學,以現代教育理念治校。此類華人校長雖然同樣是虔誠的基督徒,但他們的民族責任感遠勝于宗教信仰。在辦學過程中,雖然他們身上同樣體現出了“犧牲”、“服務”的基督精神,但在言論中他們甚少帶基督化字眼,在辦學目標的設置上也極力回避基督化字眼,辦學思想以現代化教育理念為指導,遵循教育規律、社會發展需要辦教育。以陳裕光為例,掌管金陵大學的24年,陳裕光在其辦學思想及實踐中,強調更多的反而是現代辦學理念及中國傳統的教育思想。在談到大學的使命時,陳裕光稱:“研究高深學術與培育偉宏專才,為大學之二大使命;且兩者不可分離,猶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也。”[11]在為學校制定校訓時,陳裕光將蘊含濃郁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誠、真、勤、仁”四字作為校訓,要求師生秉承。此外,陳裕光始終秉持“務以養成切合國情之實用人才為目的”,積極提升學校辦學質量,以期“不但要在學術上與世界各國求平等,我們更要求達到大學教育的最高理想。……我們要同我們國內教育界的同工共同負起我們今后在大學教育上,‘應’與人平等及‘能’與人平等的重大責任,且要從事實上表現出來”。[12]為促進學校學術之發展,陳裕光非常重視國際間的合作,主張積極溝通中西文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他認為,國際合作“對于本校發展頗有關系,況學術研究,本無國界之分,若能掇取得當,不特足資學界借鏡,抑且使一國之文化,更可發揚璀璨。”[13]但值得注意的是,陳裕光的“溝通中西文化”,并不是要全面學習西方,而是有選擇地學習,學習的目的在于“使吾國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備”,“使中國學術地位,有所提高”。[14]當然,作為基督徒、基督教大學校長,陳裕光并非要完全拋棄學校的基督化特色。陳裕光在辦學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犧牲、服務、奉獻精神,本身就是基督精神的體現。但概括而言,陳裕光是以基督精神辦學,以現代教育理念和中國傳統教育思想治校,為金陵大學選擇了一條淡化基督化色彩,又蘊基督精神于自身辦學實踐的道路。
20世紀30年代之后,在世俗化潮流當中,在國民政府的新政令下,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們或繼續堅守學校的基督化特色,或在堅守學校基督化精神的基礎上走世俗化之路以適應社會發展需要,或兩者兼顧,為自己所在的學校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但無論是何種道路,都飽含了華人校長們積極探索基督教大學本土化發展的努力。
三、辦中國的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的共同追求
華人長校前,基督教大學是“外國式的”、“根在外國的”、“西國教會的一部分”,是“在中國的基督教大學”。及至華人掌校,無論其對待學校基督化特色的態度如何,他們一個共同的目標則是將“在中國的基督教大學”辦成“中國的基督教大學”。
早在非基督教運動時期,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就提出貫徹基督教教育之中國化、發揮基督化教育之真精神、宣布科學的各種教育方法、交通中西的各派教育意見等觀點,1925年2月7日至9日,中華基督教教育會高等教育組干事羅炳生(Edwin C. Lobenstine)召集基督教大學中國行政人員舉行會議,征求他們對于基督教教育前途的意見。在該會議上,基督教大學中國行政人員一致通過了5項議案,分別為:(1)基督教大學應多有中國色彩;(2)基督教大學應多有中國教職員;(3)基督教大學應多注重國文;(4)反對強迫宗教教育;(5)贊成向中國政府注冊,[15]表明了他們創辦中國的基督教大學的共同意愿。及至掌校后,華人校長又多次表達了基督教大學中國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1937年召開的基督教大學校長會議上,華人校長又再次強調:“我們相信除非教會大學,能夠成為一種真正對于中華民國有切實服務的貢獻,合他們的需要,滿他們的希望,不求特殊的保護,與人民同甘共苦,同冒險,遵守政府的法令,便不能有長久存在的可能。”[16]
變“在中國”為“中國的”,這存在一個“中國化”的問題。對于何為“中國化”,中華基督教教育界的解釋是,“依教育主權及設施教育,無論內容形式,必合國情之原則”,“行政管理必須逐漸參加中國人,至完全由中國人主持之。除特別情形外,教授應以國語行之。國學及社會學科應特別注重。各級學校應一律立案。所有經濟責任亦逐漸由中國基督徒負之”。[17]概括而言,即:向中國政府立案,接受中國政府的監督和管理;增加中國教師比例及地位,改以西人為教師主體為以中國人為教師主體;調整辦學目標,服務中國社會發展需要;拓展經費來源,漸擺脫對西方教會的依賴;加強中國文化的教學和研究。而在實際的辦學過程中,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也確實在上述諸方面做了努力。
劉湛恩早在1925年就提出教會學校當“向中國政府注冊立案”,并忠告教會學校的中國教職員,“教會學校的改良與否,中國教職員當負全責。”[6](P17)陳裕光在正式擔任校長之前,就曾主動向即將成立的大學院聯系有關學校前途與立案等問題。擔任校長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請立案。他認為“在我國辦校,理應尊重我國主權,立案是刻不容緩的事情”。[18]福建協和大學校長林景潤智慧地解決了學校立案過程中遇到的難題,華南女子大學能夠立案,和校長王世靜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在教師隊伍建設方面,華人校長掌校后均積極擴大中國教師比例,到1934年,除圣約翰大學之外的12所基督教大學教師總數達到888人,其中中國教師599人,占教師總數的67.5%。[19](P68)到1936年變成4:1。在最后階段,由于學校規模擴大,恰好西藉人員減少,這個比例更增加到將近9:1。[20](P107)在辦學目標及課程設置的調整方面,各校也均突出了服務中國社會發展的特點。尤其是加強了中國文化方面課程的教學與研究。到抗日戰爭爆發前,除華南女子大學尚未設中國傳統文化的系科外,其余11所已經立案的基督教大學都設有國文或歷史等專業。從全國范圍來看,除北大等少數國立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的教學和研究居于“領袖地位”外,燕京中國傳統文化的教學和研究已有相當影響;從地區來看,金大、齊魯、嶺南、華西協和等大學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教學和研究在當地省份都有著重要地位。[21]主權的獨立首先在于經費的獨立。對于這一點,華人校長都有深刻的認識。燕京大學校長吳雷川在1925年就提出:“我更深望中國人在人才與經濟兩方面,必能及時謀求自立,不終為外人所輕視。”[22]在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的多方努力下,到20世紀30年代各基督教大學經費來源已經大為拓展。以1934年為例,該年度,東吳、滬江、之江單是學費收入就占學校歲入經費的一半左右;金大盡管學費收入所占比例小,但是其雜項收入達到60.4%;嶺南來自省庫的撥款占到40.3%,加上學費,兩者占總收入的66.7%。[19](P144-145)
對照中華基督教教育界有關基督教學校“中國化”之詮釋,可以說,在華人校長領導下,各基督教大學在“中國化”諸方面均得到了加強。芳衛廉在談到基督教大學立案前后的變化時,寫道:“1920年基督教大學面臨著嚴重的問題,……它們的外國特征、宗教目的和它們保持自身足夠的資源和教育水準的能力。蓬勃的民族主義要求更多地認同中國的生活。基督教大學不得不面臨和克服這種對抗情緒。……但到1930年代中期,前景十分樂觀。在大部分情況下,外國特征不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基督教學校與政府系統的整合令雙方都很滿意。在宗教問題上仍有分歧,但基督教學院和大學已經成為中國高等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大部分都已本土化。”[20](P68-69)從一個外國傳教士的口中,我們不難看出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在創辦中國的基督教大學實踐中取得的成績。
近代中國是多災多難的中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是飽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文化浸潤一個群體。也正因為如此,面對外敵的侵略,面對國內民生的凋敝,中國知識分子紛紛行動起來,積極尋求救國之路。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或選擇科學,或選擇教育,或選擇實業為利器,而基督徒知識分子則選擇了以基督精神為救國之良策。盡管的他們的選擇不同,卻是體現出了同樣的愛國心。正是在這種愛國心的影響下,他們毅然承擔起了引領基督教大學發展的重任,并積極探索基督教大學中國化之路,不僅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更為西方教育模式的本土化發展,為中國教育近代化之發展做出了可貴的探索。
[1]金陵大學舉行歡迎陳裕光校長大會[J].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1927(3):98-99.
[2]王運來.誠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3]潘公弼.滬江大學與時事新報[J].天籟,1936(2):21.
[4]韋卓民.如何成為一所基督教大學[A].馬敏編.韋卓民基督教文集[C].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5]韋卓民.基督教差會在中國的制度化工作[A].馬敏編.韋卓民基督教文集[C].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6]劉湛恩.五卅慘案與教會學校[J].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1925(3):46-47.
[7]王立誠.美國文化滲透與近代中國教育——滬江大學的歷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8]滬大新校長就職[J].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1928(1):76-77.
[9]Policy for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1936[Z].滬江大學檔案,242-1-64.
[10](美)海波士著,王立誠譯.滬江大學[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
[11]陳裕光.序[J].金陵大學匯刊,1943(1):1-3.
[12]本季首次紀念周及開學禮陳校長出席報告[J].金陵大學校刊,1943(3).
[13]陳裕光.學術研究無國界[J].金陵大學校刊,1945(10).
[14]陳校長游美返國后出席首次國父紀念周[J].金陵大學校刊,1945(9).
[15]劉湛恩.反對基督教教育之一般評論[A].中華續行委辦會.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8輯)[C].上海:上海廣學會,1925.
[16]秋 笙.基督教大學校長會議[J].教育季刊,1939(3):2-31.
[17]本刊宣言[J].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1925(1):4-5.
[18]陳裕光.回憶金陵大學[A].金陵大學校友會編.金陵大學建校一百周年紀念冊[C].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
[19]劉保兄.基督教大學中國教師群體研究[D].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
[20](美)芳衛廉著,劉家峰譯.基督教高等教育在變革中的中國(1880-1950)[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
[21]陶飛亞,吳梓明.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22]吳雷川.教會學校立案以后[J].生命,1925(2):1-2.
〔編輯 郭劍卿〕
Pursuing the Same Goals through DifferentW ays: Comparison of Running School Thoughtsand Practicesof Chinese Presidents in Christian Universities
LIU Bao-xi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Henan,475004)
Chinese were appointed presidents of the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fter the mid 1920s.According to their own upbringing and the Christian Universities they work in,Chinese presidents formed distinctive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running schools though they knew less of the future and without any references.Since they were in Christian Universities,they had the common goal that was to establish Chinese Christian universities.Because of the common goal,they promoted the domestic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omestic development of theWestern educationmodel and the developmentof Chinesemodern higher education.
Christian University;Chinese president;thoughtand practice of running school
G529.6
A
1674-0882(2011)04-0076-05
2011-03-20
劉保兄(1974-),河南安陽人,博士,研究員,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