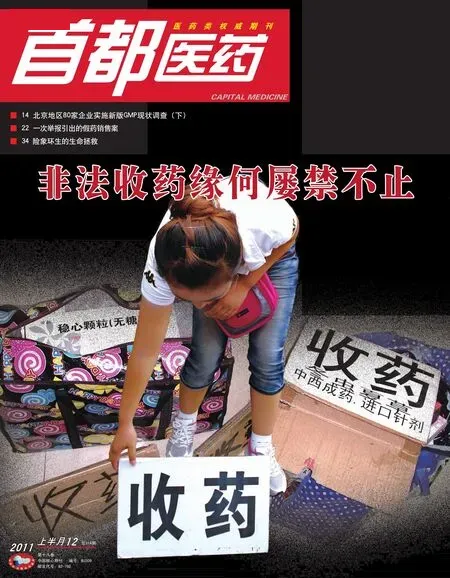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患者被忽視的心理障礙
□文
現(xiàn)今的醫(yī)療環(huán)境有了很大的改變,特別是在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地區(qū),醫(yī)院的硬件設(shè)施越來越完善,越來越先進(jìn)。但醫(yī)院的軟件狀況卻難盡人意,就醫(yī)生而言,某些人的診治觀念還停留在十幾年前的水平,特別是某些基層醫(yī)院的醫(yī)護(hù)人員。如今的醫(yī)學(xué)模式正在從以往的生物學(xué)模式,逐漸轉(zhuǎn)變?yōu)樯?心理-社會醫(yī)學(xué)模式。既往的生物醫(yī)學(xué)模式重點(diǎn)在于臨床醫(yī)生關(guān)注對疾病的診治,而生物-心理-社會醫(yī)學(xué)模式的重點(diǎn)在于關(guān)注罹患疾病的患者。這種關(guān)注不僅僅是疾病本身,而且包括疾病對患者心理、社會功能,生活質(zhì)量等方面的影響。
我在出門診時(shí),時(shí)常會遇到許多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患者,他們共同的特點(diǎn)是曾經(jīng)看過許多醫(yī)生,做過許多檢查,吃過許多種藥,但還是感到病沒治好。我為這些患者做心理量表檢查后發(fā)現(xiàn),絕大多數(shù)患者伴隨抑郁、焦慮等心理障礙,使用抗抑郁藥治療,效果非常好。目前,看神經(jīng)內(nèi)科專家門診的患者,約30%伴隨著心理障礙。這些心理障礙不僅使患者痛苦不已,導(dǎo)致其反復(fù)求醫(yī),重復(fù)檢查,浪費(fèi)大量的錢財(cái),而且還破壞了患者家庭的和諧,甚至導(dǎo)致有些患者走上自殺之路。
一名來自河北省某地的老年腦梗男性患者曾到我的門診,當(dāng)他進(jìn)門時(shí),我發(fā)現(xiàn),陪同的家屬很多。原來老先生半年前曾因“右肢活動(dòng)不靈活數(shù)天”確診為“腦血栓”,在當(dāng)?shù)乜h醫(yī)院住院治療,并經(jīng)歷了輸液、針灸、吃藥等多種治療,肢體活動(dòng)恢復(fù)。但他總覺得病沒有好,平時(shí)總是抱怨不舒服,但做了檢查結(jié)果沒有發(fā)現(xiàn)什么大問題。于是,患者輾轉(zhuǎn)多地求診,做過包括頭部MRI在內(nèi)的多項(xiàng)檢查,檢查結(jié)果為“腔隙性腦梗死”。
由于患者經(jīng)常抱怨家人對他不關(guān)心,因此,家人決定帶他來北京找個(gè)專家好好看看,他便早起掛了個(gè)專家號來到我的診室就診。我問完患者的病史后,為他做了詳細(xì)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查體。檢查結(jié)果發(fā)現(xiàn),患者除了以往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陽性體征外,沒發(fā)現(xiàn)新的問題。于是,我又詢問了他的心理狀況。患者說:“我原來是個(gè)很開朗的人,可這次得病后,怎么也高興不起來。不但睡不好覺,吃不好飯,而且覺得自從得病以后,就不是正常人,身體總不舒服,不是頭暈、頭痛,就是全身沒勁,也不愛見熟人。家人越是關(guān)心我,我就越覺得自己是個(gè)累贅。”
我詢問患者病史及查看體格檢查后,結(jié)合患者既往所做檢查的結(jié)果,初步考慮患者是腦血管病伴發(fā)抑郁狀態(tài)。隨后,我請患者在醫(yī)院神經(jīng)內(nèi)科神經(jīng)心理檢查室做抑郁量表,結(jié)果更確定了我之前的診斷。于是,我決定采用抗抑郁藥物治療,并向患者和家屬詳細(xì)說明了患者現(xiàn)在的情況,以及需要注意的問題。兩周以后,患者的女兒來取藥,她告訴我患者病情有所好轉(zhuǎn),睡眠時(shí)間也延長了,我讓她叮囑患者繼續(xù)吃藥。又過了兩個(gè)月,患者來到我的門診,高興地告訴我,他的病完全好了,不僅睡得比以前好了,吃的也多了,還能與熟人聊天,做些家務(wù)了。
我想以這個(gè)普通的病例,提醒我們的臨床醫(yī)生。臨床上,軀體疾病伴發(fā)抑郁、焦慮等心理障礙的患者很常見,但臨床確診并采取治療措施的并不多見。由于經(jīng)治醫(yī)生的觀念陳舊,大多并沒有真正認(rèn)識到伴發(fā)的心理障礙對軀體疾病的影響。此外,現(xiàn)在的醫(yī)療診治中常常存在著這樣的誤區(qū):醫(yī)生過多地依賴實(shí)驗(yàn)室和影像檢查的結(jié)果,忽略了最根本的臨床基本功。其實(shí)每個(gè)醫(yī)生都應(yīng)該牢記:我們面對的不是冷冰冰的機(jī)器,而是活生生的病人。我們需要做的不僅僅是對疾病的診斷和治療,還需要把握患者的心理、社會功能,要把他們放在社會上進(jìn)行評估,關(guān)注他們的生活質(zhì)量。而且,我們的臨床診斷是基于對患者病情的總體把握,各種實(shí)驗(yàn)室和影像檢查只是為了驗(yàn)證我們的臨床診斷而服務(wù)的,不能將實(shí)驗(yàn)室或影像檢查的結(jié)果凌駕于臨床診斷之上。因此,作為能夠解除患者痛苦的臨床醫(yī)生,應(yīng)不斷學(xué)習(xí)及更新知識體系,并積極應(yīng)用到臨床實(shí)踐當(dāng)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