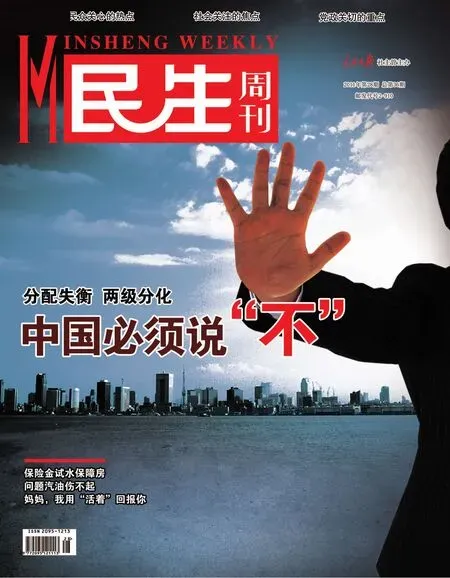“分蛋糕”的考驗
□ 本刊記者 閔 杰
“分蛋糕”的考驗
□ 本刊記者 閔 杰

社會財富的蛋糕怎么切?有人建議:民富優先。圖/CFP
北京,CBD核心區,林遠的工作地點位于國貿三期大樓,這座330米高的大樓是當前北京的最高建筑。作為一家知名網絡公司的全國銷售總監,林遠稅后年薪30多萬元,加上房補、車補、書費、健身費、休假補貼、補充養老保險以及各種臨時性的“福利”,實際收入在50萬元以上。
江西贛州,一座干凈的南方小城,土生土長的江西人彭亮大學畢業后回到這里,成為一家穩定的國有企業的技術員。企業效益不錯,他年收入5萬多元,有房有車,在當地屬于中等收入階層。不過,全家收入的1/3要還房貸,1/3供孩子上學、老人看病,彭亮感覺生活壓力依然不小:“國家說擴大消費,可靠這點兒工資收入,不頂事兒!”
安徽農村,趙剛沒有上完高中就開始外出打工,漂泊多年之后選擇回家繼續務農。天暖種地、養魚,天冷去鐵路打零活,一年到頭辛苦操勞,純收入只有2萬多元。
三個人收入懸殊的現狀,正是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寫照。
國際上常用基尼系數來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這個指數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2006年升至0.496。學界普遍認為,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在0.5左右。
統計顯示,目前總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額僅為4.7%,而總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總收入的份額高達50%。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
古語云:“不患寡而患不均”,面對日益突出的分配失衡問題,中國必須對貧富分化說“不”。
事實上,中央高層在今年年初就釋放出相關信號,并將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作為“十二五”期間的重點任務。
1月8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學習會上指出:“要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加城鄉勞動者勞動報酬,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
緊接著在2月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講話時,亦特別指出,在做大蛋糕的同時,“把蛋糕分好,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避免貧富兩極分化,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是十二五期間的重要民生議題。
管住高收入
一段時間以來,央企“丑聞”不斷:4月初,中石化廣東分公司數百萬元購買茅臺等高檔酒供私人支配被曝光;4月27日,國家電網安徽分公司被曝以“車改”之名,為全系統約300名副處級以上干部配備公務自駕車;5月3日,國家電網安徽分公司被曝光在合肥為職工建豪華小區;5月9日,中海油被曝出人均年薪38萬元;5月20日,國家審計署公布了17家央企審計公告,披露央企諸多問題……
央企不斷“東窗事發”的背后,浮現的是行業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和壟斷行業收入畸高的現實。少數行業的收入遠遠高于其他行業,這是導致城鎮居民內部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主要原因。
根據復旦大學陳釗教授的一項研究,90年代以來,“交通、運輸、郵電、通訊業”和“金融、保險業”這兩大行業相對于其他行業來說,收入越來越高,“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給業”的收入也迅速和其他行業收入拉開差距。
據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壟斷行業收入畸高是導致行業間收入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社會非議最大的誘因。”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
市場價格扭曲導致的行業暴利以及管理部門的灰色收入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我國的生產要素市場發育并不完備,資本、土地和自然資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門,市場價格難以形成,交易價格往往是扭曲的。以低價獲得礦山、土地等要素的企業會輕而易舉地從中獲得高額利潤,而相關管理部門會以尋租等方式,從中獲取大量灰色收入。
除此以外,企業高管的“天價年薪”,也一直是飽受爭議的問題。
2007年度,國內上市公司前十大高薪者中有8人來自中國平安,整個榜單幾乎被包圓,其董事長馬明哲創紀錄的4600萬年薪外加2000萬獎金的總薪酬更是令人咋舌。
在去年國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前十榜單上,金融業又一次毫無懸念地風頭出盡,一共占據6席,并且連續囊括了2006年以來這張耀眼榜單的前三名。2010年排名前三的是廣發證券、民生銀行和中國平安,分別為7209萬元、6828萬元和6820萬元。
面對各種錯綜復雜的難題,如何調節過高收入,成為“分好蛋糕”的重要一步。
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調控。
今年5月13日,國務院出臺意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削減壟斷行業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壟斷,現在國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他說,除了引入競爭機制,還需要建立國有企業的分紅機制,將超額利潤用之于國、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
管住企業高管的“天價年薪”,也是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環。財政部印發的《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明確規定國有金融企業負責人最高年薪為稅前280萬元人民幣。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易憲容認為,高管高薪問題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強政府的監管,也需要進一步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和內部薪資制度,不能僅限于“道德層面”的約束。
擴大中等收入
何謂“中等收入階層”,很難找到嚴格的界定。“中等收入階層”在國外通稱為“中產階級”,但在我國,兩者之間卻存在一些難以言喻的區別。
2005年國家統計局城調隊的一份抽樣調查曾測算出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指標,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萬元,上限是18萬元左右,同時考慮到我國地區間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較大,最終被界定出來的標準是6萬-50萬。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在研究中產階級特征的過程中,采用社科院2006年的抽樣調查數據計算出當年的人均收入,并確定人均收入的2.5倍作為劃分“高收入者”的收入標準,把平均收入線至平均收入線2.5倍之間的人群定義為“中等收入者”。
不論如何定義,這一階層表現出的普遍性特點是:收入來源的主體是工資薪金收入,擁有較高學歷,從事以腦力勞動為主的職業,有能力支付中等水平的個人及家庭消費,在解決溫飽的基礎上,為滿足家庭成員豐富的文化精神需求提供必須的物質條件。
然而,中等收入階層卻面對著四項“硬支出”:交稅、存錢養老、買房子和抵抗通脹。現實中,結構性上揚的通貨膨脹、節節攀升的房價、沉重的稅負和并不樂觀的保障體系,都在殘酷地瓜分收入,拖著中等收入階層遠離富裕。
目前我國收入結構呈現“梨形”,高凈值人群的財富規模快速增長,人口數量變化卻不大,而中等收入階層占社會總人口比重過低。中等收入向上,是“資產狀況良好、幸福感較強的中產階級”,向下,則是“日益為硬支出焦躁的社會底層”。
在西方國家,“中等收入階層”已成為推動現代社會發展、引導社會消費、穩定社會形勢、定型社會規范及主流社會價值觀的主體力量。而相比之下,我國的中等收入階層社會地位還沒有得到廣泛認同,社會作用還未能得到有效發揮,特別是,規模還很小。
“目前中國中產階級的比例為23%左右,但中等收入階層中中下階層占了68.5%,這些人稍不留神,就會成為低收入階層的替補。”資深財經評論員葉檀表示。
如何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將事關“分好蛋糕”的最大份額。
如何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將事關“分好蛋糕”的最大份額。
在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通過完善體制機制,避免財政收入增長擠壓居民收入增長空間,積極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等都在擴大中等收入階層過程中都被寄予厚望。
保障低收入
我國將在“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將貧困標準上調到人均純收入1500元,這比2008年、2009年1196元的貧困標準提高了25%。
盡管2011年的扶貧新標準大幅上升,但和國際水平相比仍然較低。我國目前的貧困線是2008年確定的,農村(人均純收入)貧困標準為1196元,農村貧困人口為4007萬人。2009年繼續實施上述標準,統計局測算,年末農村貧困人口為3597萬人。
目前,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及人均生產總值已超過印度3倍以上,但是即使采用新標準,中國的貧困標準仍低于印度。印度的扶貧標準大致是接近人均每天消費1.2美元的水平(按照購買力平價),與世界銀行人均每天消費1.25美元的全球標準比較接近。
而我國2008—2009年年農村(人均純收入)貧困標準1196元,按照購買力平價測算,只相當于每天0.89美元的水平。
從2001年到2009年,中國扶貧開發取得顯著成就。農村貧困人口從2000年底的9423萬減少到2009年的3597萬,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3.8%。
但據介紹,當提高到1500元標準后,全國貧困人口總數將大增,再回到9000多萬甚至上億都有可能。
據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執行副會長林嘉騋介紹,未來10年,中國政府將把基本消除絕對貧困現象作為首要任務,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作為主戰場,力爭到2015年,貧困人口顯著減少,到2020年,基本消除絕對貧困現象。
除了絕對貧困人口,大量城鄉低收入勞動者群體也是切分蛋糕中必須著力保障的一個部分。
長期以來,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偏低、國民收入分配向國家和資本所有者傾斜的現象一直比較突出。
近年來我國勞動報酬所占國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上世紀90年代以前,勞動者報酬占比為50%以上,2001年后這個比重不斷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41%。
在2000-2008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4%,但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僅增長15.7%。這表明,我國國民收入結構失衡,特別是勞動者報酬所占國民收入比重不斷下降。
來自全國總工會的一項調查顯示,在生活成本不斷提高的近幾年中,從未增加過工資的全國普通工人超過26%。
鑒于此,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斷改善民生、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各項社會福利穩步增長成為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的難點。
制度上,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逐步在各類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健全并落實最低工資制度等將成為改革的突破口。
此外,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水平,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解決公共服務領域的機會公平問題,逐步縮小城鄉差距,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農村各項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也應不斷提上日程并取得實質性突破。
□ 編輯 劉文婷 □ 美編 閻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