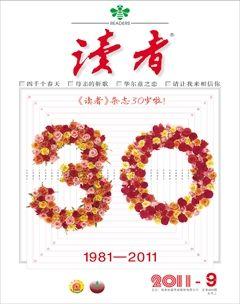大漠·書鴻·飛天
梅寒
公元366年,僧人樂僔路經敦煌,忽見前方金光閃耀,如現萬佛,于是便在他經過的崖壁上開鑿了第一個洞窟。此后禪師法良等又繼續在此洞修行。從那時起,這個叫做莫高窟的地方便被納入人類的文明之路。
公元1035年,為躲避西夏入侵的戰亂,莫高窟里的和尚把經卷畫幅等歷代寶藏3萬余件封藏在這個洞中,并用土墻將洞口堵上,再畫上菩薩像作為偽裝。西夏占據敦煌百余年,當初封藏寶藏的人也不知所終。那些被塵封的寶貝,在那個洞里一睡就是近千年。
公元1900年,看守莫高窟的其貌不揚的王道士,意外地打開了那個塵封的洞室。一面墻被扒開,稀世珍寶重見天日,也迎來中國學術傷心史的開端。
公元1907年,一名叫斯坦因的英國人來到敦煌,他用區區200兩銀子就從王道士手中換走了洞里的24箱文獻和5箱絹畫。
公元1908年,一名叫伯希和的法國漢學家也來了。他同樣以極微小的代價,把那些藏在洞里近千年的精品中的精品輕而易舉地拿走了。那一次考察,伯希和還將自己拍攝的大量的石窟圖片匯集成一本畫冊,取名《敦煌圖錄》。
公元1935年,在法國塞納河畔的一個舊書攤上,一名在法國求學的中國年輕人發現了這本毫不起眼的舊畫冊。輕輕翻開那本畫冊,一個奇妙的世界一下子在他面前洞開。他才知道,自己不遠萬里到法國尋找繪畫藝術的天堂,而真正的藝術天堂竟然就藏在祖國西北的大漠里。更讓人痛心的是,那一幅幅驚艷絕倫的敦煌大幅絹畫不在自己的祖國,而是掛在他國博物館最醒目的位置上。
他待不下去了,辭別在巴黎的妻女,也辭別了那優雅的沙龍畫家生活,獨自踏上了開往祖國的國際列車。那一年,是1936年。
這個自幼酷愛繪畫的年輕人叫常書鴻,出生在杭州一個滿族家庭,14歲考入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21歲時轉任浙江省立工業學校美術教員,后在朋友們的資助下,偕妻子到法國學習西方繪畫。當時,他在國際畫壇上已聲名鵲起,多次獲得當時法國學院派最權威的畫廊巴黎“春季沙龍”金、銀獎。
嬌妻、愛女、如日中天的繪畫事業,全因異國街頭與敦煌的偶然邂逅而改變。常書鴻毅然拋開了優雅舒適的生活,選擇了風沙漫漫的大漠。
那一個轉身,就結下了他與敦煌一生解不開的緣。
常書鴻揣著滿懷的藝術夢想回國,然而國內的現實卻讓他憂憤交加。彼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回國后的他根本無法走近令他魂牽夢繞的敦煌,他只得到北平藝專當了一名老師。此后,經過幾年顛沛流離的生活,從北平到昆明,又從昆明到重慶,直到1943年,在梁思成、徐悲鴻等人的舉薦下,由常書鴻組建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才得以成立。常書鴻任所長,卻是一個“光桿司令”,四處張貼的招聘廣告根本無人問津。無望之際,常書鴻遇到了自己北平藝專的學生,他拉著學生就開始說敦煌。“你想不想去敦煌?”那些天,他不知道對多少人重復過這句話。再面對自己的學生說這一句時,他的聲音里幾乎含著哀求了。敦煌,一個被遺忘了千年的藝術寶庫啊。學生被感動了,學生又去拉上自己的朋友,他們愿意陪著老師去敦煌。常書鴻又通過甘肅省教育廳找來公路局的一個文書和一個會計。一行5人,就是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全部成員了。茫茫的大漠古道上,他們就像中世紀的苦行僧,步履艱難地走向自己心中的圣地。
“當時,我默默地站在這個曾經轟動世界而今已空無所有的藏經洞中,百感交集。這空空蕩蕩、寂靜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地回顧著她的盛衰榮辱,又像無言地怨恨著她至今遭受的悲慘命運。”很多年后,常書鴻回憶起自己第一次站在敦煌莫高窟里的感受時,仍然心痛不已。是的,任何一個有顆中國心的中國人在面對著那些被洗劫一空的洞室、那些斑駁不清卻仍然讓人心醉神迷的佛像壁畫時,怎能不心痛難當!自從王道士將那扇大門打開,此后的十幾年里,那個沉寂在沙漠里的洞窟就成了國際偷盜者的樂園。一批又一批的偷盜者來了,又走了,隨之而去的是大量珍貴文物。而那些殘存下來的洞窟、佛像也因長年的風沙侵蝕而變得千瘡百孔。常書鴻流淚了。
起步是那樣艱難。莫高窟如此珍貴又如此脆弱,因為那些壁畫、彩塑均為泥制,保護工作做起來更顯艱難。在那個只有黑白膠卷的年代里,常書鴻決定和同伴們一起,通過臨摹壁畫來保存那些稀世珍寶的本真面貌。石窟里沒有梯架、沒有照明,他們就在小凳子上作業。一手舉著小油燈,一手執筆,照一下畫一筆。那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臨摹那些壁頂畫時,頭和身子幾乎成為90度的直角,仰頭看一眼,低頭畫一筆。時間一長,人就頭昏腦漲,甚至惡心嘔吐。當時的臨摹量大,紙、筆、顏料等材料都嚴重不足,紙只能用窗戶皮紙裱褙,顏料嘛,自己動手研制。借鑒舊時民間藝人制作顏料的方法,竟然也把那個難關渡過去了。與深處大漠的孤獨相比,物質上的艱苦根本不算什么。為等一個遠方的熟人望眼欲穿,為一封來自家鄉的書信長夜不眠。看到那些陪自己來大漠的同伴們形影相吊、寂寞孤苦,常書鴻也常常覺得不忍。可他還是寫信把遠在內地的妻子勸來了。他希望學雕塑的妻子能同他一樣,在那些大大小小的洞窟里找到快樂天堂。
最初放棄巴黎的優裕生活回國,陳芝秀就曾極力反對,后來跟著他從北一路流亡到南。炮火紛飛、朝不保夕的恐懼日子里,一家人倒也相安無事地過來了。才在重慶將生活稍稍安頓下來,又要她帶著孩子到荒無人煙的大漠。陳芝秀火了,跟丈夫吵,可最終,她還是來了。她也很想見識一下常書鴻所說的藝術天堂。平靜幸福的日子過了不到兩年,那份幸福就被打得粉碎。莫高窟——常書鴻心中的圣地,卻慢慢變成妻子陳芝秀心里的寂寞之地。風沙茫茫的大漠里,見不到人,一年到頭除了風沙還是風沙,常書鴻長年穿梭于那些洞窟間,根本沒有時間和心思顧及她的感受,穿慣了旗袍和高跟鞋的陳芝秀并沒有從洞子里那些彩色雕塑里尋找到快樂。爭吵由最初的言語攻擊到最后的撕扯,曾經的恩愛,在一次次的爭吵里悄然逝去。最終,陳芝秀走了。等常書鴻意識到妻子可能再也不會回到那個曾經充滿溫馨的黃土小屋時,他策馬揚鞭追了出去。那一次,常書鴻在大漠里奔跑了幾天幾夜,最終得到的結果,是妻子在蘭州的報紙上刊登出的與他脫離關系的消息。勞累加上傷心,常書鴻倒在了路上,幸虧被過路的人救起,他才幸免于難。一個幸福的家,終究碎了。此后好多年,他都閉口不愿提及那段傷心的往事。
但這并沒有嚇退常書鴻堅守莫高窟的決心。當國民政府教育部宣布撤銷國立敦煌研究所時,常書鴻四處寫信呼吁、求救。當抗日戰爭勝利、他的同伴們紛紛要回過去的敵占區找親人團聚時,他沒有強行挽留。那些人去樓空的夜晚,大漠里的敦煌寂寥無聲,死氣沉沉,陪伴常書鴻父子的只有遠處的陣陣狼嚎。
在“文革”那個黑白顛倒、是非不明的年代里,遠在大漠深處的莫高窟和常書鴻也不能逃脫政治的大手。莫高窟被定為魔窟,成了毒害人民的精神鴉片。那些他們日夜操勞守護的佛洞成了關押他們的“牛棚”。常書鴻和妻子李承仙常常被打得遍體鱗傷,不能站立。他不怨。事隔多年,對那一段經歷他只用淡淡的一句話來概括:我是個幸存者,一個留下滿身“紀念品”的幸存者。
10年過去了,20年過去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越來越多的人來到敦煌,同常書鴻并肩站在一起,擔負起臨摹、維修、加固、編碼的工作,常書鴻卻一天天老去。
1994年,常書鴻病重之時,在北京的病房里,他給女兒常沙娜安排后事。他說:“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世,不過,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為人,我愿意還是常書鴻,我還要去完成那些未完成的工作。”1994年6月23日,常書鴻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離開常書鴻之后的陳芝秀生活并不如意,對于自己當初的逃離,她只有一句話:“一失足成千古恨。”
如果沒有與敦煌相遇,常書鴻可以優雅從容地走一生,可以為這個世界留下許多傳世之作。可敦煌莫高窟里那些彩衣飄飄的飛天卻可能還要在漫漫的風沙中獨自哭泣,而不知又有多少千年的瑰寶要永久地從敦煌那片熱土上流失。常書鴻的老家在煙雨迷蒙的西子湖畔,然而他卻把自己的墓穴選在了茫茫的敦煌大漠。如今,透過敦煌莫高窟9層大殿敞開的樓窗,可以隱隱看到遠處沙漠里有一個小小的黑點,那就是常書鴻永遠安歇的地方。
(李 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