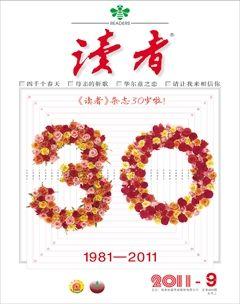也是一場戰爭
凌河
有暇再讀二戰史,說到英國,凡值得炫耀處,無非敦刻爾克萬舟競發,蒙哥馬利諾曼底登陸。彈雨槍林,云涌風起,似乎一個老大盟國,人人金戈鐵馬,除了打仗以外,便不值得一談。掩卷之際,忽然想到“倫敦大街標語案”,雖無一縷烽煙,卻也堪稱一場戰爭。
1940年春夏之間,倫敦街頭忽然跑出一幫“道德家”,自稱主張普濟眾生,反對“為本國一己之利投入戰爭”。其領袖人物,印刷標語于先,集會演講于后,真可謂“策劃于密室,點火于基層”。
彼時英倫,危在旦夕。敦刻爾克退兵未罷,海岸已遭狂轟濫炸。首相關于“我們決不投降”的豪言壯語,本也是全民的共同決定。“英國從未像今天這樣團結”,值此兩黨聯手、同仇敵愾之時,“一小撮人”的胡言亂語,怎不令民憤鼎沸,千夫所指?于是警方出面干預,戰時法庭理所當然升了大堂。
法官人選令公眾很放心。“且看那被納粹奪去二子的波懷恩如何收拾這幫混蛋”已成為報紙的通欄標題。然而審判帷幕降下之時,波懷恩法官話語沉重,竟令公眾失望之至——“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據我理解,我們的戰爭,正是要保護這個自由。我要說,被告幸而生在這個能自由表達他們主張的國家。我宣布他們無罪。”
據我所知,判決似乎并未得到公眾的支持,人們普遍懷疑波懷恩老人為何“寬容”至此。而在如釋重負的少數人中,例如戰時內閣的內務大臣安德遜,卻欣慰地指出,這也是一場戰爭。在英國,僅僅因為抱有不同意見,決不能被看做犯罪,不論其意見多么不合輿論。而“倫敦大街標語案”挑起的公眾激憤,卻使英國的法律面臨真正的進攻。從這一點而言,波懷恩判決的意義,甚至不亞于英國在海岸、在北非進行的抵抗人類文明最兇惡敵人的戰爭!
二次大戰硝煙散去已逾一個甲子,戰爭早已成為歷史的足跡,昔日的恩怨也已為新的合作所取代,然而“倫敦大街標語案”的判決書卻留在世界法制史上,正如戰后一位英國政治家對全體公務人員所說:“自由和國土具有同樣價值,甚至民族的當前危機和憤怒的公眾感情,也不能動搖英國的法律原則。‘倫敦大街標語案就是一個明證。”
而在所有自稱為“公民”的人中,也許波懷恩在宣讀判決時提到的最后一句話,更讓他們銘刻在心——“我宣告你們無罪,但我堅持認為你們應該向前方的戰士們道歉。沒有后者的戰斗,便沒有你們的言論自由。濫用權力的人和濫施權威的人,都不能自稱為這個國家的公民!”
(何鳴摘自《新聞晨報》,圖選自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國際藏書票藝術》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