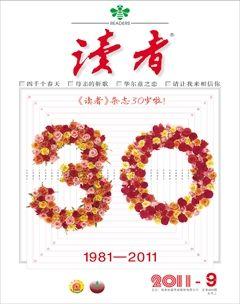請讓我來相信你
趙菲菲
信,還是不信?這是個問題。
今天,“不相信”的情緒已然滲透進許多中國人的生活:吃飯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鐵路部門解決買票難問題的能力和誠意,上醫院不相信醫生的職業操守,打官司不相信司法會保持公正……
有人說,幸福感源自相信。而當懷疑一切成為整個人群的集體意識時,中國人與幸福的距離該有多遠?
一
不相信其實未見得比盲目相信更糟糕,懷疑有時候是一種進步,說明信息渠道多了,社會開放程度增大了。但我們的問題是愛走極端,現實是別人干不出來的我們干得出來,別人想不出來的我們也干得出來。一旦相信,我們就熱血沸騰全國串連畝產十萬斤兒子打倒老子老婆跟老公劃清界限,不相信則心如死灰豆腐不吃了國產奶粉不喝了老人家倒地也不扶了。
如今,懷疑和警惕已經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因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斷發生。住,我們有樓倒倒、樓脆脆、樓歪歪、樓薄薄;吃,我們得小心假煙、假酒、假雞蛋、假牛奶、地溝油、人造脂肪、美過容的大米、藥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藥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條;出門,我們要提防推銷的、碰瓷的、釣魚(執法)的;上醫院,我們擔心假藥、無照行醫、被過度治療;此外,我們還要面對假票、假證、假中獎、金融詐騙、假新聞,等等。
面對如此炎涼世態只能茫然自問:我們究竟應該相信誰?
武漢洪山區“釘子戶”童貽鴻選擇了首都警察。在武漢他被指控扔磚頭傷人,因為不信任當地警方,自己花1000多塊錢坐飛機到北京朝陽區雙井派出所自首。而浙江樂清“上訪村官”錢云會被工程車壓死一案,樂清警方第一時間發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數萬條跟帖絕大部分都抨擊警方撒謊,人們不相信錢云會之死的背后沒有打擊報復。同樣,在有媒體爆出八成火鍋為“化學鍋底”后,中國烹飪協會立即辟謠,但網民并不買賬,并“人肉”出協會相關部門主要負責人乃是某知名火鍋企業老板。
一時之間,“陰謀論”風行中國互聯網。有時候,往往越是被官方或專家澄清的,反而越遭到網民的質疑。英國《衛報》評論說:“人們對此類事件(錢云會案)的猜疑顯示出當局所面臨的信任問題的嚴重性。在所有國家,‘陰謀論在網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國有著尤為強大的吸引力。”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也表示:“不管錢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慮到輿論的偏向,這難道不正揭示了一種危機?如果你是官員,你不應該感到焦慮和擔心嗎?”
二
需要焦慮和擔心的或許不只是政府官員。今天的中國,讓我們“不相信”的土壤幾乎隨處可見且相當肥沃。
“綠豆治百病”的張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初就是被中國中醫研究院下屬的產業部門聘為養生食療專家,開講座,上電視,賣產品,利益共享。作家謝朝平因自費出版紀實文學作品《大遷徙》而遭遇陜西渭南警方跨省拘押,后者在敲開謝朝平租住房前自稱“人口普查的”,后來謝被取保候審。
怪事多發,就見怪不怪了。每件奇聞都會引來人群的圍觀和議論,但很快就被新奇聞的熱鬧所取代。我們是能屈能伸、知足常樂的民族,吃飽肚子就一團和氣。魯迅說過:“我們都不太有記性。這也難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但真相沒有彈性,而且刺目、扎手、揪心。
縱觀中國歷史,我們不僅出產殘缺的身體——太監和小腳女人,也出產殘缺的精神——奴性。魯迅在《華蓋集》中說,中國的尊孔、學儒、讀經、復古,是為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
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路威認為,有好些事情,因為我們做了某一群體的分子,就非做不可,這和真假對錯沒有關系。皇帝什么也沒穿,但大家都夸他的新衣服漂亮。罪魁固然是別有用心的騙子和愚蠢虛榮的主子,但鼓掌叫好的大眾也并非無辜。個人相對于體制是渺小的,但體制又由每一個人構成。于是,正如陳凱歌指出的,站起來控訴的多,跪下來懺悔的少。
我們活著,而且確實“欣然”。任何可悲可恨的事情都可以用笑罵的形式變成娛樂甚至狂歡——只要沒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在挖掘黑色幽默方面體現出無窮無盡的聰明才智,比如“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姜你軍”和“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剛”;我們編出《救助老人安全寶典》,我們在《阿凡達》里看到野蠻拆遷……
三
我們活在兩個世界。現實中,我們不相信一切陌生人,我們明哲保身,安安穩穩做沉默的大多數;家家都安防盜門,低層住戶都裝防盜網;我們不敢讓小孩自己上下學,即使學校門口有警察維持治安;我們對陌生人充滿警惕,人口普查員遭遇入戶難。虛擬世界里,網絡是那件神奇的衣服,把大家全變成了蜘蛛俠。現實到了網絡就完全調了個兒:發言者陷入沉默,沉默者開始發言;權貴默默退后,草民成了主角。
所以,一些人說,現在的人很虛偽。這種虛偽甚至滲入我們的教育。百度百科有個詞條“偽文章”,指的是不惜通過虛構事實來表現真善美的小品文。其煽情和編造手段之虛假嚴重到令人發指的地步,代表作就是入選小學語文教材的《一面五星紅旗》。寫的是一位中國留學生在國外漂流遇險后,寧愿忍饑挨餓,也不肯用國旗換面包,最后暈倒在地,贏得外國友人的尊重和友情的故事。對兒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沒問題,關鍵在于以什么方式進行這種教育。當“偽文章”充斥教科書,虛偽就不僅變得可以接受,而且成了準則。
從某種角度講,許多人的虛偽不是虛偽,而是“務實”,是我們多少年來在理論與實際、語言與行動、書本與生活、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中總結出來的“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我們從小就被灌輸尊老愛幼、助人為樂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老人當街摔倒我們不敢扶,因為有“彭宇”們好心幫助老人反而被訛的前車之鑒。這不等于說滿大街的老年人都準備訛人,相反,絕大多數人都是善良的。但疑慮是一種心魔,一旦迅速傳播就很難治愈。
普遍的強大的疑慮已經成為社會的“精神疾病”。假的我們不信,真的我們也不信。當“77元廉租房”引發的憤怒被證明是一起謠言時,我們也會陷入迷惘:除了自己,我們到底還能相信誰?
也許只能相信小孩子。北京一名11歲的小學生去年在老師的幫助下做了一個簡單的食品安全測試,發現他隨機選擇的14種鮮蘑菇中有13種經過漂白處理。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辦公室進行的調查稱,北京市場上銷售的蘑菇97%未檢出漂白劑,可以安全食用。一個是小學生的隨機調查,一個是政府部門的“權威發布”,你該相信誰?1100多人參與進行的網絡調查顯示,絕大部分人相信小學生的檢測結果,只有8個人說他們對政府部門的檢測有信心。
不只普通人相信小孩子,一些地方有關部門也在公開或半公開地表達著自己對于成年人的不信任。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2009年7月在全區公檢法系統競職筆試中,聘請當地18位少先隊員來監考,結果抓出25個作弊的。公檢法的責任是維持社會正義,他們自己內部的公平卻要未成年人來監督。
四
對陌生人的不信任只是當前“不信任文化”最末端的表現。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國墻》一文中說,中國沒有“柏林墻”,但由高強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會墻”卻存在于社會各個群體和各個角色之間,在政府和人民之間,在資本和人民之間,在窮人和富人之間……不一而足。
信任是人與人交往、合作的基礎。無論夫妻關系還是官民關系,沒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騙,自欺欺人。像那個段子形容的:官員們哄百姓開心做做秀,下級哄上級開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開心做做飯,自己哄自己開心做做夢……哄來哄去的結果,就是魯迅說的比真的做戲還要壞的“普遍的做戲”,也是嚴復所說的“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作于偽,終于無恥”。
縱觀近年來的網絡熱點事件,資深網友黎明如是總結:只要是涉官、涉權的都會出現這個規律:不信——不信——就是不信,老百姓已經變成了“老不信”。黎明認為,解決這場“國民不相信運動”的辦法就是政府退出“經濟競爭”,不與民爭利,更不奪民之利,不作為糾紛或迷案中的利益方出現。
周國平在北京大學做過一次演講,題目叫“中國人缺少什么”。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嚴重弱點是重實用價值而輕精神價值。中國人缺少的不是物質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靈魂生活和廣義的宗教精神,所以沒有敬畏之心,沒有自律。幾十年來的經驗證明,財富未必能帶來尊嚴,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飛奔在致富的道路上,我們更是成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上帝、馬克思、老天爺和十八層地獄都既不能讓我們敬,也不能讓我們怕。當下的游戲規則就是不要規則,不懂這個道理的就是阿甘,或者堂吉訶德,只能等著被淘汰。
最近一項面對上海市民的調查顯示,有超過90%的人認為誠實守信會在不同程度上吃虧。但是,中國有句老話,吃虧是福。西人也說,被騙也比騙人強。歷史告訴我們,判斷事物的標準往往并不在當下。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實踐,更是時間。違背常識的情況無論多么普遍多么強大都不可能長久。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幾十年前的盲目相信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還關系到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
(余娟摘自《國際先驅導報》2011年1月17日,鄺 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