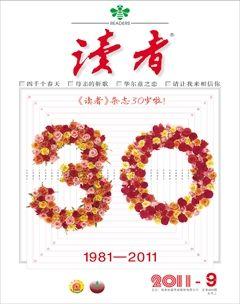和莫里在一起的星期二
江芬

有人曾問莫里·施瓦茨教授:“什么是人生最困難的事情?”教授回答說:“與人生講和。”
社會心理學教授莫里在走過生命中第78個春秋后,因肌萎縮性側(cè)索硬化的頑疾與世長辭。作為莫里早年的得意門生,作家、主持人米奇·阿爾博姆在老教授纏綿病榻的14周里,每周二都飛越700英里上門與他相伴,聆聽他的教誨。于是有了《相約星期二》這本書,讀者遍布世界各地。莫里的墓碑上寫著:一個終身的教師。瘦小的他當之無愧。
莫里說,愛是唯一的理性行為,沒有愛我們便成了折斷翅膀的小鳥。盡管他知道自己將不久于人世,可他并不愿意親人們分分秒秒地陪在他的身邊,他不愿因此打亂別人的正常生活。“不然的話,被病魔毀掉的不是我一個,而是三個。”當一家人有機會坐在一起時,他們常常如瀑布般宣泄感情,互相親吻、打趣,相擁在床邊,幾只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隨著病情的惡化,莫里的身體不可避免地逐漸癱瘓。有時早上醒過來,他會不由得哀嘆自己的不幸,但過不了多久,他就對自己說,我要活下去。莫里仍舊關心時事,他會為半個地球之外的人流眼淚。正如張愛玲所言:“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一天,莫里告訴米奇:“你知道嗎?我比你更能體味那扇窗戶。”莫里每天都從窗口看外面的世界,他注意到了樹梢上的變化,風吹過時的大小。他分明看見時間在窗外流逝的痕跡。
年少青春時,我們看到的世界是隔著紗、蒙著紙的。當我們發(fā)現(xiàn)夢想沒有照進現(xiàn)實以后,我們只能奔波在生存的道路上。學生時代的米奇常常身著舊的灰色無領長袖衫,視有錢為罪惡,襯衫加領帶在他眼里簡直如同枷鎖。畢業(yè)以后,他必須為了錢而工作,一心一意關心著自己的生活。如果不是偶然間收看了《夜線》節(jié)目,莫里也許到死也不會再見到米奇;如果不是報業(yè)罷工讓米奇陷入迷茫,或許他也不會每周飛越700英里去和莫里見面。
16年后,當米奇與莫里再度重逢,米奇明白了什么才是有意義的生活,明白了如何更好地表達自己的愛。“他的勇氣、他的幽默、他的耐心和他的坦然告訴了我——莫里看待人生是和別人不一樣的,那是一種更為健康、明智的態(tài)度。”在他們最后一次見面時,我欣喜地讀到,米奇也開始留意之前從未注意過的一些細小的東西,如山體的形狀、房子的石墻、低矮的灌木叢。
讀著書,我不禁想起了電影《再見巴法納》。電影描寫了曼德拉在被監(jiān)禁的27年里,長期負責看守他的白人警衛(wèi)格瑞格里如何從僅僅堅守職責到同情、理解和幫助曼德拉的故事。曼德拉的人格魅力同樣彰顯在莫里身上。3次《夜線》節(jié)目的采訪,莫里都沒有特意換上新衣服或者打扮一番。他的哲學是,死亡不應該是一件令人難堪的事,他不愿為它涂脂抹粉。看著身體日漸虛弱的莫里,一向冷峻的主持人說:“如果不想進行這最后一次的采訪,我可以馬上結(jié)束這期節(jié)目。”老教授莫里在生命結(jié)束前激發(fā)出了電視業(yè)的同情心。病魔可以奪去莫里的身體,但永遠無法奪去他的靈魂,以及帶給我們的心靈震撼和洗滌。
記得幼時,我身子單薄,時常生病,所以容易放大幸福的定義,能自由地大口呼吸,能在路上行走跑跳,便是我的樂事了。無論小病大病,父親總會第一時間帶我去看醫(yī)生。一次從醫(yī)院回來,發(fā)高燒的我寸步難行,父親一口氣把60多斤的我抱上了7樓。在父親懷里,我能感受到他的呼吸、他的心跳,我告訴自己,現(xiàn)在很安全、很溫暖。就像老了的莫里,覺得不應羞赧于他人的照顧,反而視為一種難得的感受,像是又回到嬰兒時期,被人關切和愛撫。
“人生最重要的是學會如何施愛與人,并去接受愛。”
在家時,父親常晚歸,有時我會下意識地等他,等著從臥室的門縫看到客廳的燈亮了,我才會睡得踏實。看著莫里的故事,我莫名地很想回家,我想回去照顧父母,再為他們準備早餐、清洗衣物、打掃房間。是的,莫里讓我很愿意做這些瑣事,在為家人付出的點滴中有我的幸福。
(劉君民摘自《大學生》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