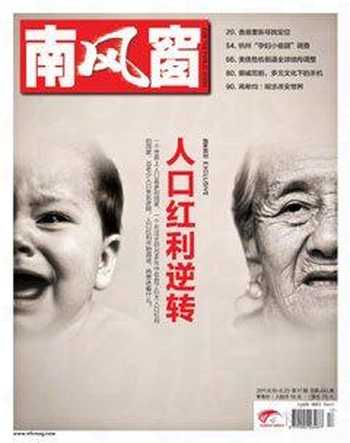叫停“治安聯防費”還不夠
石 勇
8月的輕風吹拂炎熱的南方城市廣州,帶來一個消息,并迅速向全國擴散:面向外來流動人員強制征收的2.5元/月/人的“治安聯防費”,將停止征收。
有很多人形容,這是“7年抗戰”的勝利成果,至少,外來人員在辦“居住證”時,理論上少了被“刮”一次。
從制度設計上來說,當初的“暫住證”和現在的“居住證”,確實有點像“綠卡”,沒有的話,一個“外來流動人口”在城市就沒有取得“合法身份”,類似于“非法移民”。
不過多年來,很多人還是感到迷惑不解:他們只是在自己的國家流動,又不是出國,為什么由國家、憲法和法律所承諾的公民權利、國民待遇,因為他們流動到另一地,就變成了一個問題,或者被公開宣告沒有,或被實際剝奪了呢?
“治安聯防費”多年來,其合理性、合法性一直受到質疑。當一個國家的國民流動到某一城市,“治安”等方面的“管理”本應屬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一部分,為什么還要向他們收錢?這一點,從來沒有人能夠提供在法理上足夠正當的辯護。
廣州取消“治安聯防費”是好事,但還不夠。這既是因為它本屬應該,更在于,比起4.5元/月/人的“流動人員調配費”,“治安聯防費”只是利益的小頭。而佛山、東莞、中山等地,都還沒有取消“治安聯防費”。這和每年都痙攣性地發作一次的“民工荒”,以及“關愛外來人員”的口號,真是構成絕妙的諷刺。這些,只能證明公權力機構其實還貪戀那些在道德上無法論證其正當性的利益。
一個“治安聯防費”其實已經揭露了一切。當本來只和地域有關,和公民權利、國民待遇無關的“外地人”、“本地人”,被公權力機構人為地以“居住證”、戶籍進行相應識別,并讓他們具有不同的權利,分享不同的國民待遇,那么,挑戰既定“社會管理”的禍患就種下了。一個國家的公民群體由此被人為割裂,并在對一部分公民群體的管制中,成全了公權力機構的牟利沖動。
廣州市長萬慶良最近建議用“新廣州人”取代原有 “農民工”、“打工仔”、“外來人員”等稱呼,讓“新廣州人”真正的成為廣州大家庭中的一員,在廣州生活得更有尊嚴、更加幸福,更好地共享幸福廣州建設成果。這個建議得到輿論正面肯定,如何落實,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