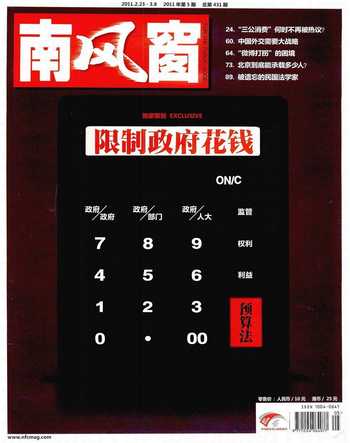公共環境運動的迷思
周雷
真正的公共環境運動和生態革命的出路水落石出:那就是回到城市、回到都市人、回到現代性、回到生活方式的反思、回到污染的元認知。直以來,至少在中國,有關生態問題和公共環境教育有幾個顯著特征。首先,人們往往有個“污染在別處”的遠方想象。搞環保,不做到昆侖山、三江源、黃河源、青藏高原、香格里拉的冰川,好像就沒法在環保組織年終的項目總結上增加亮色。許多環境保護項目,專注于減少中國山川地理原生環境的人類活動,用退耕還林、退耕還草、退耕棄牧等方式,造就了一大批生態移民,使得一大批原住民和自己的祖先、祖靈、祖地永訣。
與此同時,中國都市的設計者和城市資本運作者基本缺乏家園意識和城市的屬靈觀念,也就是說,城市在他們的設計圖和項目運作中,是不會呼吸,沒有疼痛感的物體,而非一個可知、可感的記憶聯合體和生存共同體。多年以來,從上到下,都陷入一種國際、全球、超級城市的拜物教式崇拜,它造成了中國有史以來最為劇烈的城市變革和景觀革命。
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們,雖然有不安的知覺、焦慮的直覺和切身的痛感,他們往往在快節奏和成功至上、生存優先的都市環境里,調低了自己對環境的要求,往往容易對切近的微觀生態問題生出麻木,無法真正反思自己的都市消費習慣、都市造城理念、都市生活方式如何不斷積累對中國生態問題的龐大壓力。
味蕾上的城市
前段時間,筆者再次考察了中國西南部西雙版納的熱帶雨林,注意到一個特殊的現象,在許多村落,他們的生活環境正悄然發生植物學意義上的“城市化運動”,他們自己絲毫沒有覺察。我考察這一區域的傣族村寨至今仍生活在保存較好的熱帶雨林里,原因之一是當地政府將這個有農村社區的自然區域統一整合成一個雨林保護區(傣族社區的編制一般稱為“曼”,相對于縣城這一層級的“勐”),然而這些雨林地帶并非處于完全原生的狀態之中,除了農民在近村落一帶的橡膠和香蕉種植(這一經濟活動已經持續了幾十年),最近一兩年出現了另外一種村落經濟模式,那就是大規模的蔬菜基地。
這些蔬菜基地通常和熱帶雨林連在一起,原來多為水流漫漶的林間沼澤、水田、草場和荒地,一些地方甚至是大象獲得鹽分的半沼澤地。現在都已經開墾成大片的蔬菜基地,統一種植四季豆和南瓜,投資者來自四川,所生產的蔬菜多標上有機的標志統一發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
耐人尋味的是,在我考察期間,正好是四季豆搭竹架,南瓜在塑料膜里培育莖葉的時節,不少農民背著農藥來地里噴灑。所以,即使是產自熱帶雨林的蔬菜,也并不完全是按照“有機”的方式生產的。但是遙遠的西雙版納,僅僅憑借這個遙遠地理,異域的民族風情,已經可以讓一些有機食品公司異地高價賣出自己的“有機蔬菜”。
然而在蔬菜種植過后,才是環境問題的真正開始:當地傣族農民一般在旱季種植蔬菜,當雨季來臨,還是要種植一些水稻,這樣一來蔬菜地的化肥和農藥統統又被水稻吸收了。同時由于當地的灌溉系統與自然水系和雨水地表徑流的聯通,這些污染元素(當然包括橡膠地大量施放的化肥和農藥)一起進入雨林生態系統。
而在城市的另一頭,面對無所不在的環境污染、土地減少、食品倫理的喪失,中國的都市人都選擇去消費這些所謂的有機、生態、綠色農業,這表面上象征著都市在日常消費這一層面上的可持續循環。例如在上海,只要是貼有這些標志的農業產品,可以賣出普通食品3~5倍的價錢,這客觀上造就了都市“殖民”農村的“食品地理學結構”。原來地理和文化意義上的偏遠省份,現在成為一種食物、味蕾上的生產基地。
從大的結構上看,現在的城市化過程成為透支國民生命、體能、陽氣、元氣的巨系統;都市化和新市民階層需要從這些產自原生、自然、綠色、有機環境的物品中獲得補充,保持一種能量的均衡和人的協和。在成都,我看到一家設在中醫館樓上的食療火鍋,里面每一道菜都具有某種醫療用途(在這里吃飯,根本就是治病,而非進食),其中最為重要的功能是補陽和滋陰,例如,普通的蝦米被制成“鎖陽蝦球”。
在問題重重、危機四伏的城市化過程中,中國人的生活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醫療化。
兩套“時間體制”
在看到上面提及的“植物學”意義上的變化以及都市消費行為時,人們應意識到中國山川地理的自然流向——中國的國土基本上有兩套“時間體制”。往西、往北、往西北偏北,基本上是一個“生態時間”,這些地方多為中國文化歷史的原生地之一(許多西南的部族都流傳著遷徙史詩,講述自己的祖輩如何從中國的西部和西北高原地帶,沿著下移平落的山川地理,逐漸往西南和東部轉移,例如藏彝走廊),同時也是自然神性較為突出的地域,為中國少數民族聚居的區域。而往東、往南、往東南偏南,基本上是個“社會時間”,也就是與發展、現代、文明、當代、摩登、都市相關的時間,這里的“人文地理”和社會環境基本上和蠻荒神秘的西部形成一組二元對立。
但是從生態、污染的框架分析上,過多的生態保護注意力和資源大量向西部傾斜,這里主要包括環境項目的知識生產方式、國際及本土大型NGO的布局、環境“課題”組織方式和生態知識的傳播方式。人們往往忽視了其實沿著自然地理的西高東低走向,一種發自東部、產自城市的“污染社會潛流”和“生態惡化的社會學地質變動”正朝著西部逆勢涌動。
備受眾人關注的紙業擴張,對應的正是都市化、標準化、典籍化的生活方式(生活在西部農村的農民也許10年都不會用A4紙打印一份東西,但是都市里“明天9點上班”6個字,都要打印10幾份在辦公樓張貼)。蠶食了整個西南中國的橡膠種植對應的是都市一小時經濟圈區域高速便捷的交通系統和欲望解決機制。占據中國整個西部(經濟學意義上)GDP大頭的水電和礦業開發,對應的是能源饑渴的恐龍型城市和超大城市群。即使是表面上生態友好的生物質能源(如膏桐、木薯)也是替代西部大量本土自然資源的外來物種,而這也是為了滿足都市永無饜足的能源需求和汽車式城市夢。
任何一個有過中國西部游覽經歷的游客也許都有過這樣一種觀察:在中國西部有一種我稱之為“小賣部式都市污染”,也就是說不管你去大理、麗江、稻城、九寨溝、波密、林芝、拉薩,還是桂林、陽朔、香格里拉、黃果樹瀑布、青城山,只要進入一個小城鎮或者旅游區外圍的農村小賣部,你都可以看到大量產自城市的大宗生活消費品(不少為假冒和偽劣,農村是假冒偽劣產品的重災區),這些產品幾乎無一例外都最終成為無法降解的污染品。
但是,在任何一個發達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杭州等,來自云南、貴州、西藏、青海的風物,基本上是代表具有醫療性、審美性、生活時尚、道德性、宗教性、鄉土性的“滋補品”和“自然物品”。
話題至此,真正的公共環境運動和生態革命的出路水落石出:那就是回到城市、回到都市人、回到現代性、回到生活方式的反思、回到污染的元認知。未來中國城市的生態未來,取決于都市人的自覺、自在、自為、自責、自律、自省。
圍繞著城市的現有格局,尤其是城市垃圾的“文明遺產”,應有更多的環境組織和項目進入,不應停留在宣傳欄海報和公益宣傳上,應該通過設計、知識、技術、行為干預來整體修正城市已經惡化的生態環境。
應該對上海世博會的城市主題進行更為立體、持續、深入的研究和知識傳續。中國在經濟上最為富足的城市群不應僅僅進行基于硬件的海量投入,打造一個外表富麗堂皇的列維坦式城市(巨獸式的城市),他們最應該最先發展成為一個城市的智者,而不是一個不斷輸出錯誤模板、破碎理念、低級欲望、高度污染的生態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