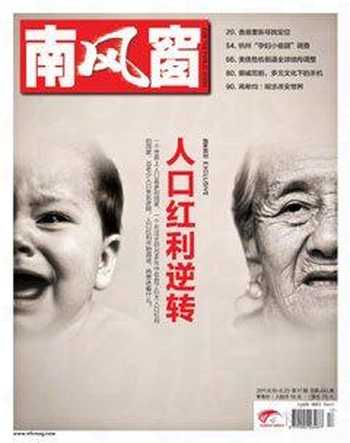紡織業突圍:轉行,還是轉型
李 威


7月的長三角進入濕熱酷暑,崔文的心情卻如掉入冰窟。他年初從父親手中接管自己家的大圓機織造廠,廠子一直處于長時間歇業,接個單子開工,再長時間歇業的狀態,崔文一直處在焦頭爛額的狀態,市場實在壞得太久了。
對于國內紡織行業,真正的大考已經來臨。通貨膨脹推動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擠壓個位數的利潤,再加上傳統的行業淡季,目前已是兩頭堵的局面。面對困境,人們往往喜于談上一次困境,以此渲染走出困局的信心。不過相較于2008年那場紡織業風暴災難,這次崔文的感覺“確實不一樣”,“它不會讓你在第二天早上醒來就發現企業原有的訂單全部消失,銀行跑來提醒借貸日期,這次像溫水煮青蛙,慢慢你會發現訂單幾乎沒有,開工沒有利潤,廠子越做越想扔掉。”
多如牛毛的紡企老板們現在大概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轉行還是轉型?
慘烈的淡季
2008年后,國內紡織業經歷了兩年的復蘇,直到今年一季度,勢頭不減,據中國紡織協會發布的行業半年報顯示,今年上半年,紡織品服裝出口總額1117.25億元,同比增長25.74%。不過二季度的情況突然糟糕起來,上半年出口增速整體逐月放緩。到現在的7月份,行業傳統的淡季,形勢更加惡劣。對此,崔文有切膚之痛。他是常州人,自己家的廠子有40臺針織大圓機,30多名員工,所購原料主要是棉紗,產品主要是供印染加工的坯布,是整個紡織產業鏈中非常細微的一環。
“往年都是6月份之后進入淡季,今年5月份之后幾乎沒有單子可做,即使碰到訂單,也不想開工。”崔文說,做大圓機織造這塊的同行都知道,現在一般所產常規面料價格約在2000元/噸(人民幣,下同),除掉電費、房租、員工工資、稅收等,每噸利潤大約在300元左右,“如果加上客戶回扣以及吃喝費用,利潤幾乎沒了。但想想還是要做,房租要交,員工保底工資要發。”最讓他擔心的是未來的市場,崔文發現企業的脖子在被慢慢勒緊。相較于往年,今年以來的訂單少一半,價格也被壓得很死,人工成本去年以來上升20%,員工每人平均月加薪500元左右。另外,暴漲暴跌的棉紗價格使得企業幾乎無法正常運營,使得本就資金周轉困難的企業雪上加霜。現在崔文的許多當地同行都在賣大圓機,準備轉行,不過,崔文笑言“這玩意現在賣也賣不掉,只能苦撐”。
中小企業占紡織業的99%,崔文的公司表現了現在行業的整體樣貌,根據中國紡織網的價格月度表看,紡織業原料較去年全部上漲,棉花價格從去年10月開始暴漲,在今年4月份達到頂峰,5月份開始下落至今,不過價格整體上漲明顯,7月份的價格比去年1月份仍約高出46%。羊毛價格也上漲明顯,國內毛紡企業主要羊毛產地澳大利亞今年羊毛平均價格已上漲39%。化纖原料價格也在飆飛,如其中最主要的PTA(精對苯二甲酸)價格一路看漲,7月份價格相較于去年1月份上漲約20%左右。人工成本上升也是普遍現象,調查寧波嘉樂集團和江蘇陽光集團等發現,與2009年相比,這些企業的人工成本普遍上漲在20%~30%之間。
成本在漲,訂單卻在下降。金融危機后,許多企業轉向內銷,但目前整體仍以出口為主。查看匯率圖標,2010年1月,人民幣兌美元在6.82元左右,今年7月,匯率已到6.43元左右,人民幣升值殺死了很多國外訂單。此外,影響紡織企業的其他因素還有融資難和電荒。東華大學紡織學院教授王華表示,紡織業的利潤已經被嚴重蠶食,紡織產業鏈大致分為紡織、印染、服裝三大塊,目前紡織印染企業兩頭受阻,利潤約在3%到5%,服裝里面分貼牌服裝和品牌服裝,貼牌服裝利潤大概在10%左右,品牌服裝能夠達到20%以上。“國內行業制造加工環節資源臃腫過剩,服裝業則仍有不少發展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的對比數據時間跨度較長,就是為了印證崔文對于行業越來越惡劣的感覺,同時也說明紡織業各種成本和環境的變化難以逆轉,今年行業逐漸陷入被動則是各種因素積累的爆發,正如王華所言,低成本和出口導向的時代將漸漸過去,未來行業的變革將更加慘烈和廣闊。
痛苦轉型
幾年前,行業就喊出轉型口號,卻雷聲大,雨點小,金融危機時,國家曾通過提高出口退稅等方式挽救外貿企業,此次國家普惠式扶持行業的大動作很難出臺,政府一直存有推動紡織業產業升級的意圖。聰明的商人看到要么盡早收攤,要么必須脫胎換骨。
寧波嘉樂集團董事長嚴厚國就是一個聰明的老板,他正在大刀闊斧地進行“二次創業”。 嚴厚國是地道寧波商人,1979年入紡織行業,通過做日本服裝貿易和貼牌起家。現在,員工有2000多人,在當地頗有名氣。但這樣的基礎并未讓嚴厚國高枕無憂。公司紡織業以貼牌外銷為主,占總體業務70%以上。2008年時,這種業務構成使紡織、印染等幾乎所有的環節虧損。金融危機的沖擊讓嚴厚國重新思考了很多問題,他繼續推動公司的紡織廠、印染廠向江蘇等周邊人力成本等較低的省份遷移,同時,也感到目前公司以制造加工貼牌外銷的架構已經走到山頂,剩下只有或結束轉行,或在紡織行業另辟蹊徑。
這是一個痛苦的抉擇過程,在剛開始的一段時間,嚴厚國曾一度想放棄紡織業,重心轉向資本投資領域。“其實轉行很容易,成立幾家投資公司,什么賺錢投什么,不用怎么操心。”但后來,他又決定繼續堅守紡織業。為什么?嚴厚國說,做了幾十年的行業,有很厚的行業情結。另外一點是顧及和自己一起打江山的那些老朋友。“許多人都過了40歲的年紀,在公司做管理層,他們離開嘉樂,去其他單位很難就業,即使去了,也幾乎不可能拿到我們現在給他們的薪酬。”
如何轉型也曾讓嚴厚國感到疑惑,紡織企業轉型升級無外乎兩條路徑:打造自主服裝品牌和技術革新。嚴厚國和他的團隊最后選擇在戶外用品這個領域施展拳腳。“戶外用品系列目前在國內仍是一片藍海,而且預測利潤空間能夠上升到30%以上。”
其實這已經是嚴厚國第三次發力企業轉型,從他的身上也能折射企業家與行業升級之間微妙的關系。嚴厚國是個勤勞而有眼光的商人,但在與市場的博弈中,他則顯得比較糾結。嚴厚國首次品牌轉型是在1996年前后,當時一批企業通過襯衫和西服樹立了企業品牌,由于缺乏整盤統籌,計劃被擱淺。第二次則是2000年之后,公司為日本名牌貼牌,當時嘉樂集團已初步形成加工鏈條,內外環境俱佳,嚴厚國也請了日本團隊幫助打造品牌,但最終公司貼牌一月有400來萬的收入進賬,企業轉型動力不足,這次努力也未持續太久。
緩慢的腳步
環境逼迫嚴厚國做破釜沉舟式的行為,為了轉型成功,今年,嚴厚國單獨注冊成立戶外用品子公司,并下重金聘請職業經理人以及咨詢公司助自己一臂之力。嚴厚國表示子公司可以以8000元月薪招聘上層。
搭好了臺子,對于嘉樂集團而言,這僅僅是開始。轉型是個龐大而精細的系統工程,如果不理解其中深意,就很難想象企業家為之付出的勇氣和精力。建立自己的銷售品牌與貼牌生產對產業鏈的要求有本質區別,紡織業產業鏈越往上游生產的周期越長,如紗線生產需要18個月,面料生產需要12個月,服裝生產需要6個月,越往下游,應對消費者快速消費需求的壓力越大,上游企業體現為庫存式、計劃式的生產模式,下游則更類似于訂單式的生產模式。也就是說,貼牌更多的是規定動作,零售品牌則加入了市場銷售的變數。如果要建立零售品牌,重塑產業鏈不可避免。難度系數更大一些的是銷售渠道要從零開始,許多貼牌企業自身的品牌知名度有限,對零售非常不利,要得到市場的認可需要重新砸錢打響品牌。另外,目前地皮日益金貴,高昂的成本也成為構建零售渠道的重要障礙。
從制造品牌到零售品牌,這種轉型的艱難行進從江蘇陽光集團身上也能看到縮影。陽光集團是全球最大的精毛紡生產企業,為幾個世界一流服裝品牌供料貼牌,是名副其實的業界翹楚。作為一個制造企業,陽光集團已經做得很好,但作為轉向品牌服裝的經營商,效果并不理想。在2008年前,陽光集團發展了職業裝、高端西服和女裝,但都未在業界產生太大動靜。轉型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王華預計產業鏈調整合理可能需要8年到10年的時間。
狂熱房地產
業務多元化已是多數大型紡織企業的現狀,而房地產則是每個企業矢志奔赴的方向。
江陰市城區200多平方公里,在最繁華的商業街道,隔不遠處就能看見紡織服裝企業海瀾之家的店面,海瀾國際貿易大樓是當地最漂亮的寫字樓,海瀾之家開發的樓盤在當地也頗有名氣。在寧波,雅戈爾幾乎出現相同的景象,自1998年真正進軍房地產,雅戈爾跨出寧波,布局蘇杭,并屢次拿下地王標的。2010年雅戈爾年報顯示,去年雅戈爾房地產開發的營業收入已高于服裝主營業務,利潤率為33.06%,實際上,2002年之后,房地產業務成為公司業績增長的主要動力。嘉樂集團和陽光集團都分別開發有自己的酒店和樓盤。
紡織業結緣房地產有其行業特征,早期,勞動密集型的紡織企業需要大片土地建廠,一家上規模的廠區占地一般都在10畝以上,為了發展當地經濟,政府也樂意蓋章批地。現在,江浙已是寸土寸金,張家港的一位朋友表示,目前張家港村的地一畝能賣到60萬以上,而且只有給村支書送紅包才能搶到。離他家不遠就是村支書300萬的復式別墅,“這些人身價都已經過億。”在寧波市內一畝地的價格則超過600萬。適逢紡織業因成本問題轉移或關閉工廠,利用原有場地開發房地產順理成章,另外,服裝企業大量開設專賣店,也無形中囤積了商業地產。王華表示:“建自己的職工宿舍與進行商品房開發,建自己的專賣店控制銷售終端與轉租收租金,這種轉換并不十分困難。”
紡織企業發展的基礎不同,對房地產發展的界限和定位也明顯不同。實力相對較弱、品牌知名度較低的企業大多數利用原有廠房土地開發賺一票,基本在本地發展。如雅戈爾這些品牌服裝企業除利用原先土地外,還依靠品牌知名度,四處擴張,這類企業會依靠房地產供養服裝業,通過服裝品牌來推動房地產的發展,形成互動之勢。房地產已和紡織業一樣成為其主要業務。
房地產是產業升級中的一個插曲,其催生了行業的浮躁氣息,這種副作用遠大于房地產可能給予紡織業的資金支持。如果看一下大型紡織企業其他業務領域,就會對浮躁的說法有更深的理解。除房地產外,這些企業基本都在圍繞新能源、金融投資幾個有限的領域發展,這是個值得深思的現象。王華講了一個笑話,500個紡織職工創造的利潤不及50個搞房地產的員工,50個搞房地產的員工不如5個做金融投資的員工。對于“紡織強國”的理想來說,這是個很冷的笑話。
技術軟肋
紡織業最牛的環節是在兩頭:材料研究和服裝設計,也是目前我國紡織業最為缺失的環節。要想在世界產業鏈中擺脫“藍領”身份,必須將產業鏈從橄欖型向啞鈴型轉變,走高精尖研發之路。
材料研究在紡織領域的重要性在美國杜邦公司身上找到樣本。杜邦是一個胃口很雜的跨國企業,涉足幾乎沒有聯系的多個不同領域。紡織界知道杜邦是因為萊卡這種衣服輔料,其實萊卡是杜邦旗下的紡織面料品牌,并非一種面料物質,其主要成分是氨綸紗,摻入面料后能極大延展衣服的伸展力和回復性。這種產品由杜邦公司最先研發出來,并在氨綸領域取得壟斷地位,萊卡也幾乎成了所有氨綸紗的代名詞,由于萊卡能夠極大地提高穿著的舒適度和合身感,在全球紡織界掀起了一場面料革命。直到現在,許多服裝設計師都喜歡在自己的作品中用一點萊卡,如今一件衣服若配有“我有萊卡”的三角型吊牌,其身價一定不菲。
我國化纖工業發展近50年,目前,儀征化纖、吉林化纖等這些中國化纖企業,規模在全球范圍內都屈指可數,也具備一定的研發能力,不過其研發水準和影響力都無法與杜邦相提并論。化纖企業整體不是以科技立本,仍依靠量多價低作為主要競爭手段,不少企業等著低成本模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在萊卡之后,杜邦又推出T400面料纖維,吳江盛澤地區的不少企業從杜邦購回原料,經過熔融擠壓,將所產產品冠名為T400,杜邦公司起訴不能用T400的名字。后來這些企業就不用T400的名字,換成T300、T380等。“不過在出售或制作面料時,這些企業會打著杜邦T400的旗號做生意,真是可悲。”
服裝設計這種玩文化的工種與國外的發展水平差距更大,據有關數據顯示,我國紡織服裝行業總從業人數達1960萬人,占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從業人數的14%。但其中從事面料設計工作的人員僅占紡織服裝行業總從業人數的1.5%,創意大師、設計精英等高層次人才則更為稀缺,服裝企業不是請的外援就是剽竊模仿。
針對目前的現狀,技術出身的江蘇陽光集團董事長陳麗芬表示,目前國內首先要重視知識產權保護,陽光集團在呢絨行業曾有過多次的技術革新,不過面世后就會有人模仿,對方以很低的成本獲取同樣的產品。模仿已經大大削弱了這個行業的競爭力,企業靠模仿,不需要人才來搞研發,人才得不到培養,自然就出現斷層,形成惡性循環,這就是為什么許多學服裝設計的學生畢業都去搞外貿的原因。其次學院要注重培養實干型人才,與企業良好互動。
陳麗芬認為,中國紡織業要興起,發展自己的民族服裝不可缺少,某次陽光集團按照意大利某知名外商的設計要求貼牌生產服裝,但在交接的過程中,該設計商表示所產服裝沒有充分體現應有的文化內涵和氣質。“實際上這種有獨特文化底蘊的東西很難超越,如果讓他們生產唐裝,我想他們也無法完全把握服裝的內涵。”這件事給陳麗芬不小的刺激,這也是她現在如此努力打造自主品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