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責任與財政功能
李煒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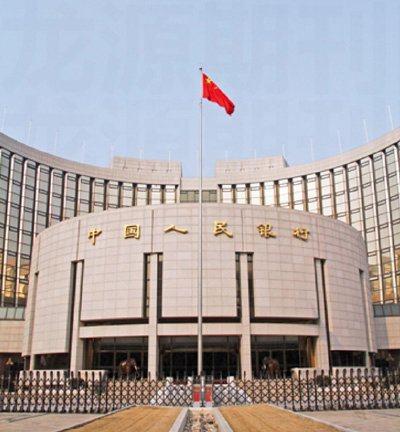
新“顯學”的震撼登場
財政學目前正越過宏觀經濟學而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全民關注的“顯學”,最近的熱議問題,如被網友戲稱為“妻稅”的“婚前房產加名征收契稅”和所謂“月餅稅”,加上稍前些的“鐵公基燒錢”和“預算公開透明”等,其背后反映出的中國社會深層次問題頗發人深思。
一是國家征稅權和用稅權配置的錯位,人民代表大會還沒有完全負起控制、監督稅收和預算的責任,納稅人也沒有完全得到相應的財政事務參與權。國家的財政稅收表面上似乎高度集稅權于上,實際上有一定的隨意性。一個地方機構就可決定開征或增征某種稅,或將納稅人的錢巨量損耗在政績工程、大躍進工程和豆腐渣工程上。二是公民社會權利意識確實在普遍覺醒,對征稅和政府如何花錢等問題前所未有地關注。
這兩個方面,前者是壞事,說明經過30多年改革中國的治稅權還遠未完善。后者是好事,說明中國公民社會正在形成,中國民間顯然走在了政府和人大前面。
中國當代學者很多受計劃經濟時期“大政府”、“總樞紐”財政觀的影響至深,至今難以擺脫。其所理解的財政職能只是“分配”和“監督”。市場改革后,又補充進“調節職能”,但計劃經濟的色彩仍未褪盡。
休謨早在1740年就指出“公共的悲劇”的存在。他說,在共同體中,個人成為“免費搭車者”是符合理性的,但如果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成為免費搭車者,最后的結果就是所有的人都得不到好處,這跟中國的寓言“三個和尚沒水吃”是一樣的道理。這個原理告訴我們,追求自身利益——效用最大化的個人有可能導致公共資源的質量下降。因此,休謨認為,政府財政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個人之間以及個人的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合理配置資源,以實現全體社會成員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政府財政手段進行資源配置,可以找到許多現成的例子,如供水、漁業資源、石油勘探等,大都由政府撥款經營。
由于市場失效的客觀存在,政府活動首先應保證社會資源在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合理配置,并且以不影響私人部門的效率為前提,然后才可以考慮資源在公共部門內部的有效配置問題。此外,當存在外部不經濟時,生產成本等于私人生產成本加上社會生產成本,而決定市場價格的卻是私人生產成本,這就會造成某些產品的過度生產;另一方面,當存在外部經濟時,收益等于私人收益加上社會收益,而決定市場狀況的卻是私人收益,由此又會造成社會消費的不足。為了消除或減輕外部效應,也需要政府發揮財政的配置功能,例如,征收環境保護稅或污染稅,要求污染者按照社會對環境的評價付出相應的附加成本,迫使其調整生產決策,減少產出水平,這就是馬斯格雷夫把配置資源作為財政首要功能的原因。
上述內容有些已經寫進了今天的財政學教科書,卻遠沒有成為中國當代財政學課堂上的靈魂,更遠沒有成為當代中國文明的主流。這導致的一個不良后果,就是一代一代的畢業生從財經院校大門走上工作崗位后,總會有一些人表現得比他們的前輩們還要厭煩別人對他支配資源的權力的制約和監控。
政府權力與公共責任
人們經常談論如何實現政府職能的問題,卻很少問這些職能是從哪里來的。簡單說,政府職能是其行政權力的組成部分,它來自于政府的公共責任規定,而公共責任則來自于公民委托和授權。在政治學的觀念里,只要政府存在一天,就必須依法做某些事或不做某些事,而責任則意味著某些事無論政府愿意還是不愿意,都必須要去做,否則就要被問責。
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共責任就是保護和促進國民利益的職責與任務,不可推卸,更不可倚據權力站在公民利益的對立面上,說一不二。在現代社會中,政府權力被界定為公有物,誰獲得了權力,誰就必須承擔起法定的公共責任。所以,人們早已習慣地把現代政府稱為“責任政府”。現代社會需要好政府,而好政府的標志,就是能對社會承擔起公共責任,即提供最大的公共福利,維護人權、公民權和私有財產權。這是喬治·梅森說的。只有那些知曉權力邊界在何處、正確界定自己的責任并認真地履行好上述公共職責的政府,才可能成為一個得民心的政府。
但在現實生活中,不一定責任和權力就是對應的,有時會是權力很大的政府,責任擔當卻很小;而另一些責任擔當很大的政府,權力卻被該國的法律看得死死,并不顯得很大。而在一個制度環境不大健全的社會里,人們的期待可能只是,政府不做某些事或不履行某些“職責”,對社會來說可能更好一些。
政府的財政功能
財政權力的行使,更是事事相關每個公民的意愿和福祉,公民納稅不是為了供養一個統治自己的政府,而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收了稅的政府必須承擔起相應的公共責任。政府所擁有的處理財政事務的權力不是“天生”的,有授權才有支配資源的權力,無授權則無支配資源的權力。當財政權力被授予出去的時候,國家還應該建立一種完善的以權力制衡權力的機制,如公共預算的外部政治控制機制,它包括公民參與機制以及立法機構獨立審計和全程監督的機制,預算過程和績效接受人民代表大會甚或更大范圍的討論、問責和糾錯。需知,只有經過制度嚴格限定的權力,才可確保稅收用之于民,才可認真負責地承擔起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諸般責任。
市場經濟中的一個基本事實是,由市場決定的初次分配基本上是不公平的,表現在財富、教育水平、技能等等方面,而且資本收入的分配比勞動收入的分配更加不平等。導致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一是財產繼承權的差別,二是非繼承的勞動能力的差別。不平等是“不好”的,這個“不好”還會導致更加“不好”的社會后果:貧困、富裕階層對財富的浪費、社會沖突、低收入群體得不到社會其他成員的幫助而自暴自棄等,在理論上,一般用市場機制的有效法則排斥公平法則來表述。這就需要政府通過財政收支活動進行全社會范圍的再次分配,在社會中形成一種公平分配的機制。
市場交易為什么無法進行有效的再分配,而只能由政府來承擔這個任務?第一,市場中基本不存在以公平為目標的分配機制;第二,私人慈善機構的活動帶有某種再分配性能,但從社會整體來說尚顯規模太小,無法解決全局性的社會問題;第三,政府的獨特地位使它擁有強制性征稅的權力,也就使它能夠大規模地進行再分配活動。并且,政府能夠通過稅制和預算來解決由于要素市場的不完全性與壟斷定價所產生的收入分配問題。這方面也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如義務教育、社會保健、公共醫療、福利服務、住房補貼等等。事實上,希望市場解決全部社會問題不過是一種幻想,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并不在于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而是以其合理的制度安排來促進社會公正的實現。
此外,由于市場在自發運行的過程中很難避免經濟周期問題,也需要政府制定和實施稅種、稅率調整或改變公共支出的規模或方向等宏觀經濟政策,這些政策可以直接作用于物價、就業水平和經濟增長,最終促進宏觀經濟相對穩定狀態的出現。這就是財政的穩定功能。
財政功能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政府面臨的國家政治經濟形勢在改變,它所承擔的任務和職責在改變,財政的功能也隨之而變。在封建專制社會,財政就是為鞏固皇權統治服務;計劃經濟時代,財政就是無所不做、無所不包的“全能財政”;而在市場經濟時代,財政的主要任務就是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改善國民福利。這時候的財政功能,顯然就與前市場社會完全不一樣了。如果這個時候政府仍置自己應盡的公共責任于不顧而繼續在“生產建設”上耗費資財,那就是對自身職能的誤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