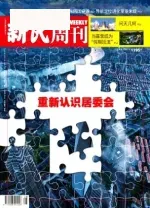告訴你“美式教育”真相
陳丹丹

善良的中國人對美國教育有多少美好的想象?其中有多少是美麗或并不美麗的誤解?美國教育真是一個神話么?美國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到底水平怎樣?
多年前的情景喜劇《成長的煩惱》,鑄就了無數國人對“美國式教育”的烏托邦想象。現如今,我媽在暢想如何教育外孫時,仍舊自然而然地舉《成長的煩惱》為例。而那里面開明幽默的父母,溫和、民主的教育方式,還有亂七八糟的差生邁克,當年也著實羨煞了我等自覺被規訓的“好學生”。
林黛玉有云,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在毛主席那里,這是中國的戰歌。風水輪流轉,現如今,果然有“中國虎媽”的故事在美利堅“咆哮”出場,一時震驚山野。但這所謂的“中國虎媽”,果真是中國的么?
作者蔡美兒女士的背景已告訴我們,這是華裔美國人。很巧合的是,在我知道蔡的故事之前,在廣播里碰巧聽到她的訪談,當時心中就想,這位一定是從小在美國長大的。而蔡女士也傾訴過,小時候因為別的孩子嘲笑她的中國口音,就此發誓改掉。這個成功的法學院華裔教授,用民間早已流行的嘲諷式稱呼來說,乃是一個實質上的“香蕉人”。
實質上的“香蕉人”,其實仍是美國人。所謂《虎媽戰歌》,開場的句子竟然是:“這是個關于一個媽媽、兩個女兒、兩只狗的故事。”尖酸如我,忍不住要對那“兩只狗”說一句“裝”!再忍不住聯想一下虎媽的丈夫,那可憐美國“羊”(洋)爸,竟然連狗的地位都不如?但這是標標準準的“美國敘述”:一座房子,兩個孩子,幾條狗。而曾幾何時,我們也多么贊嘆過美國人民把“狗”都當作朋友,連狗都有“狗權”!
由此可以看出,蔡女士雖有著華裔的血脈,但很難說她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了解何謂“中國”、何謂“中國精神”。她對“中國母親”所做的定義,基本都來自西方人對“中國”的既定印象,遠不能代表現實中的中國父母。固然現實中,中國的父母要與孩子一起戰奧數、搶學校、給老師送紅包,但如蔡女士這樣逼女兒“一晚上做2000道數學題”的,數來數去,怕是只有一個郎朗的爸爸。
說起來,我對在美國販賣的“中國故事”,素來不甚待見,這當然包括很多華裔美國人或在美國求生存的中國人所撰寫的故事。并非只要具有東方面孔,就一定了解中國,因為某些具有東方面孔的人,也許對中國更有偏見。他們與前進中的中國的現實,和其他美國人一樣隔膜;他們或者來自“中國的過去”,或者以聽來的“中國的過去”來繼續描畫“中國的現在”。他們的東方面孔,使得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以“中國”的名義訴說自己的“偏見”。在這樣的中國敘事中,中國是沒有歷史的。
“虎媽”何以轟動?
“虎媽”話題的轟動,自有其現實背景。近年來,隨著美國經濟的低落和中國經濟的繁盛,美國國內的“中國威脅論”,已經甚囂塵上。CNN等電視臺,每每在有大事發生時,推出關于中國的調查,而問句都是諸如:你認為中國是美國的威脅嗎?看得我又好氣又好笑。普通美國人民對中國、中美關系的認知,自然大多來自美國的宣傳,比如中國政府不讓人民幣升值;美國欠了中國債,所以要讓中國人到美國來。“中國”,在美國的傳媒中,正在變本加厲地被塑造為一個美國的強勁對手。
聯想曾經在美暢銷的關于中國的書籍,有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和辜鴻銘的《中國人的精神》。不論是《吾國與吾民》還是《中國人的精神》,力圖展現的都是一個美好、靜謐的“中國”。在西方人眼中,這樣的中國永遠處于“過去時”,與西方相比的“過去時”。我的美國學生在課上讀到辜鴻銘的宏論,每每置之一笑,也就是他們心目中對此并不當真,但目下的“中國威脅論”,仿佛愈來愈真切地向美國人警告:對手來了。
這也是《虎媽戰歌》為何如此刺激美國人的神經,因為書里涉及到中美競爭的問題,并且是關于孩子、關于未來的競爭。奧巴馬總統幾次關于教育的演講,美國人都聽在耳中,記在心里。我班上的學生,就自己發言,講述中國、日本的教育,已經如何如何超過了美國,在這一點上,美國人很謙虛。但同時,他們也有自己的堅持己見。美國人看待世界,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與眼界——某種程度上,這是美國地方新聞遠遠重要過世界新聞的眼界,是隱藏在各種多元文化敘述下的、單一的“老大”心態。
當“老大”發現,對手可能真的來了,能不驚慌?
美國人與在美華人的反應
我很愿意在此介紹一些身邊的美國人(教師、學生)、在美華人對“虎媽”的反應。當然,幾乎所有人(不論中美),都認為虎媽太過極端,但涉及到具體的教育方式,又有不同的意見。我所問過的大多數華人朋友,都不認同虎媽對孩子的嚴格訓誡。這恐怕因為他們多是赴美留學的精英分子,本身在中國受過嚴格規訓,自己又受到高等教育,有更開明的態度。而身邊美國人的態度則可分為兩種。其一,是對虎媽表示同情之理解,并說明自己的父母對自己要求也很嚴格,美國式教育絕非僅僅放縱孩子,對孩子毫無要求。尤其是家長付了昂貴的大學學費,更會對孩子有期待。一個黑人女生告訴我,如果她在高中得到B,那么她的父母就不允許她出去跟朋友玩。而她的高中,則會不斷把C以下的成績單寄給家長。但她同時表示,這完全取決于那個高中的要求如何。其二,則是對蔡美兒持更負面的評價。比如,前副國務卿、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理查德·庫珀(Richard N Cooper),認為蔡美兒想通過自己的孩子再活一遍,是自私的。庫珀教授的觀點恐怕代表了相當多美國人的看法。而財新網《哈佛筆記》專欄作者陳晉,作為一個穿梭于哈佛校園的華人媽媽,則認為蔡美兒書中指出的美國教育的問題,的確存在于大多數美國父母身上。
換言之,思考中的美國人或中國人,恐怕都會先打破所謂“中式教育/美式教育”的本質化定義與對立,好好考慮蔡美兒文章所批評的美國教育的缺點,以及枯燥“訓練”在“成才”中的作用。但“中國虎媽”的標簽,以及四處轉載的那些個“絕對不允許”,恐怕也會更進一步敲定大多數美國群眾對中國的既定印象:專橫的父母、要求服從的文化、婦女沒有權利、沒有受教育的機會……
豆瓣網上有一篇署名“醬油郎獨占花魁”的文章《Brava,Tiger Mom! 我看虎媽和她的家庭教育》,作者是在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文中認為,中美兩種教育方式的不同,“取決于當代美國文化的自私性和中國文化依然強大的無私性”。美國人崇尚個人主義,所以父母怕負責任,不敢干預另一個自我;而父母不要來管我,我以后也不管父母,這使得許多父母在教育孩子時過于小心,老了自動去進養老院。在作者看來,這樣的循環,將形成一個“自我放大”的系統。就我所目睹的美國老人的孤單晚景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
但美國人其實也并非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對孩子放任不管。比如,大學校園中你盡可以看到送新生的家長,美國孩子的學費,也并非都由孩子獨立賺取,其實大部分還是家長付的。我的美國同事告訴我,美國有所謂“舞臺媽媽”(Stage Mother)的說法,即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一力培養其當明星,就此對孩子進行各種訓練,并與好萊塢的經紀人洽談。著名的秀蘭·鄧波兒,就是這么被訓練出來的。
“云計算”?美國初等教育的“放羊”
由“虎媽”現象、中國人與美國人對“虎媽”話題的回應,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深入到下面這些問題:善良的中國人對美國教育有多少美好的想象?其中有多少是美麗或并不美麗的誤解?美國教育真是一個神話么?美國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到底水平怎樣?
讓我們先看看美國的初等教育。一直以來,都有在美國的華人父母,介紹美國小學的優越:不死記硬背、無沉重負擔,老師鼓勵做創造性的作業。這些贊嘆主要是針對中國國內教育的問題(學生負擔過多,競爭太烈)而發,所以都忽視了美國教育本身的重要問題,美國初等教育的程度太淺。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的作家毛尖,談及兒子在國內已做到兩位數乘除,到了美國的小學,只得跟著一年級從頭數8,不禁哭笑不得,但與此同時,孩子又非常喜歡上學,因為去了就可以玩整天,并且作為一個外國人,很快就和同學打成一片,不停地去出席美國小朋友的生日宴會。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小學的確風氣開放,當然,這恐怕也因為這是著名學區的好學校。但試想一個孩子在中國,倘若還需要學習數8,恐怕連幼兒園都無法考取。
美國“數學教育”的淺顯,造就了普遍的美國人民完全沒有心算能力。網上已經流行一個笑話:有中國人在美國,買東西付賬,抬頭看看天,就報出了準確的數字,當即嚇得美國人也抬頭看天,驚恐道:云計算?
美國的初等與中等教育,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階層分化。有錢人,可以每年花一萬到兩萬的學費,讓孩子上私立高中。而好的公立學校所處的地段,就屬于所謂富人區,房價非常昂貴。在波士頓地區,好學區的一套很小的兩居室公寓,房價都要30多萬美元,在一般的學區,已經可以買一個Single Family的單幢獨立屋。而在差的高中,孩子吸毒都有可能。中國的“擇校”瘋狂,在美國,是很“平和”地用“資本說了算”來解決。
誰“殺死”了“祖母”?
美國大學的“嚴厲”
與美國初等教育之“放羊”形成鮮明對照的,乃是美國大學的“嚴厲”。首先,管理嚴格。在國內,有一個不成文的說法是,最天才的學生都是自學的。我一個極其優秀的朋友,談及在北大讀的本科,名言是:“必修課必逃,選修課選逃。”很顯然,即便是北大這樣的學校,也有相當多“雞肋”般的課程(并且大多以“必修課”的面目出現),讓最優秀的學生無法忍受,為了自己學習,只好逃課。但在美國大學,不管是哈佛這樣的第一流院校,還是一般的大學,基本都無此可能。所謂“自由主義”的美國,恰恰在這點上,絕不自由。我在哈佛做核心課程《儒家人文主義》的助教(由杜維明教授任教),每星期都要帶討論課,學生若有缺勤,就要報告給學生宿舍長,“告狀”的電子郵件,抄送與學生相關的各位教師或管理人員,然后可以一級級報上去。換言之,在所謂崇尚“隱私”的美國,學生基本處在幾層“監督”之下,無甚“隱私”可言。你可以選擇逃課,但逃課之后還能得高分的,恐怕很少。
在我自己開始教書后,也要每堂課讓學生簽到,若有曠課多者,立刻報告給相關的院長。我也經常接到院長郵件,咨詢某某學生是否缺席過多。在此嚴格的“全景監控”之下,可憐的美國學生若要想逃課,只好編出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祖母死了”。于是我們同事間互相開玩笑,都說實在不敢多考試,因為一旦考試,就要“殺死許多祖母”。
《圍城》中方鴻漸在三閭大學任教后,念及自己讀書時,最憎恨堂堂點名的教授,故此也想瀟灑走一回,任學生自由來去。孰料教課日久,學生數日漸稀少,不得不開始次次唱名,成為自己鄙視的那類教授。如我和我的朋友這樣,在國內讀本科時頗多逃課,在美國教書后又不免成為“方鴻漸鄙視的那類教授”,不能不感到某種“人格分裂”。
與管理嚴格相聯系的,是美國大學的課程繁重。這在第一流的大學尤為明顯。當然,在好大學里,學生都是自己嚴格要求自己的。曾經有媒體報道過,一個中國媽媽去看望在哈佛讀本科的女兒,發現女兒當日計劃安排的睡覺時間,只有15分鐘,頓時哭了。這個故事頗近于現實。我在哈佛讀博士時上日語課,練習的句子是,你昨天看了《紐約時報》了么?結果說來說去,每個人都是,我昨天沒看,今天也沒有,因為沒時間。有一次,看到在耶魯讀博的朋友在日志里說,一邊在跑步機上跑步,一邊看論文,不禁覺得很好笑。但這在頂級學校,絕非少見。
我個人絕不贊同這樣的“玩命學習”,因為說到底,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但這至少說明了,美國大學教育,是非常嚴格的。同時,當課程繁重,你所有的同學都在拼命,每個人不自覺地都會落入這樣的循環。即使就并非頂尖的學校來說,學生的課程要求,也并不輕松。也就是說,美國的大學教育,基本上可以做到“實打實”。當然,我個人認為嚴格的規章也有弊端,就是無法給天才留出空間,但畢竟對大多數學生而言,一個實打實的大學教育,是必要也更有效率的。
美國大學自然有許多值得中國大學借鑒的地方,比如,小型討論課(seminar),比如,學生多方面發展。但美國教育的這些優點,若推至極端,也會失去平衡,從而損害教育的質量。我個人認為相當多的討論課(甚至包括哈佛的討論課),都有“浪費時間”之嫌,教師不再傳授知識,幾個小時可能就淪為低層次的討論。學生參加校內運動隊自然是好(在我教書的大學,似乎每個學生都會參加一個運動項目),但倘若訓練、比賽的時間過多,又自然會嚴重地影響課業。在美國做老師的確不易,因為要時刻提防刺傷學生的小心靈。在我在哈佛當助教的時候,很可能一個B的分數,就要惹來學生的不滿。而哈佛政府系的曼斯菲爾德教授,也因為批評哈佛教育的“庸常化”和給學生分數過低,遭到學生攻擊。事實上,現代社會已經造就了一種“平庸主義”的傾向。
2004年的美國影片《大人物拿破侖》,講述的就是愛達華州那個頗荒涼的地方,“笨笨”的幾個學生,反而獲得“成功”。在我看來,美國電影,一向善于生產這種對大眾的安慰劑。一方面,固然是聰明家伙們容易心腸更壞(且看高級知識分子的學院爭斗),但另一方面,教育能否繼續保持通往卓越的向度?——這的確已是現代社會的兩難。
(作者為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任威爾斯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