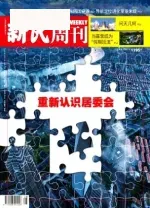人們為什么恐懼?
夏佑至
因為擔心身邊的化工廠可能發生爆炸,成千上萬民眾在正月初八的凌晨離開家門,蜂擁上路,試圖逃離家園。恐慌、寒冷和糟糕的交通狀況導致的車禍至少奪走了4個人的生命。但迄今為止,江蘇省響水縣政府堅持將2月10日的悲劇定義為謠言蠱惑。沒有人出面對民眾的生命財產損失表示歉意,更沒有人愿意承認施政的過失。
這一切如同一出荒誕的戲劇——如果沒有親自到過事發地點,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不解:到底是什么讓人們如此恐懼,以至于要在寒冷的凌晨時分逃離溫暖的家?
要是到過江蘇北部沿海各縣的村莊和城鎮,親眼目睹過那里一家連著一家的化工廠,從村莊邊一直綿延到海邊,看到過那里遍布內河岸線和海岸線的煙囪和廠房,看到過那些縱橫交錯的管道和高聳的煙囪,感受到各種不斷“嘶嘶”冒出白色蒸汽的粗大的管道,并且親自聞到過那里驅之不去的、散發出酸臭味道的空氣,你就會知道,人們的恐懼并非空穴來風。2009年底的一次采訪讓我看到,此次事件的事發地、響水縣陳家港化工園區及其給當地民眾帶來的恐懼,只是一幕更大、更令人擔憂的圖景的一部分。
江蘇有954公里海岸線,無數大小河流從內地流往黃海,三個濱海地區:連云港、鹽城和南通下轄的臨海14個縣,無不以化工業作為發展經濟的優先選項。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連云港市有規模以上化工企業202家,銷售收入151億元。當地政府希望到2012年,這兩個數字能夠分別提高到500家和500億元。要達到這個目標,化工產業必須保持33%左右的年增長率。而江蘇南端的南通現有化工產業的規模是連云港4倍以上。在2012年之前,地方政府希望能夠保持年均13%以上增長率。
對江蘇沿海縣市高密度的化工產業布局來說,這還只是一個開始。《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重申了化工業為這一地區的發展重點。
在江蘇臨海地區中,只有響水縣所在的鹽城是傳統的農業地區,但也在急切地追逐工業、尤其是化工業的增長速度。盡管蘇南化工業污染造成了世界性環境事件——太湖周期性地爆發藍藻,但以承接蘇南化工產業為目標的蘇北地區,仍然以“環境容量”作為招商引資的重要砝碼。陳家港化工園區2002年投入使用,招商公告上長期標明:這個園區“北枕‘蘇北黃浦江——灌河,灌河潮汐落差大,河面平均寬度在1500米,自凈能力強,環境容量大。”
實際上,“蘇北的黃浦江”已被嚴重污染。2007年的數據顯示,灌河河口水質為劣四類,生態環境質量等級為極差。歷史上農歷三月后,成群結隊的虎頭鯨常從黃海游入灌河,在這里覓食交配。2002年后,灌河口的魚類急劇減少,虎頭鯨變得罕見。它們最后一次出現在灌河上還是2005年的事。由于水域污染,灌河一帶的漁民在近海的收獲越來越少,他們不得不購置了更大的漁船,以便到深海作業,或者離開傳統的漁場,南下到其他地方捕魚;那些無力購置大船的漁民最終放棄了水上生活,其中一些人成了化工廠工人。盡管當地政府給予漁民一定補貼,但這些錢甚至不足支付他們從頭開始定居生活所需的開支。
所謂的“環境容量大”,很多時候也許是說,當地政府對環境污染的容忍度更高。國家環保總局等八部委在2009年10月組織了對蘇北地區的海洋環境的檢查。檢查組認為,該地區“存在環境保護工作相對滯后,監管能力不足,監督管理不到位的問題”,其中包括“沿海化工園區較多,存在較大環境污染風險”。
而更大、更直接的威脅是生產安全問題。陳家港園區的噩夢并非首次發作。2007年11月27日,園區內的江蘇聯化科技有限公司發生爆炸,官方通報8人死亡數十人受傷;2010年11月23日,園區內的江蘇大和氯堿化工有限公司又發生氯氣泄漏,導致處于下風向的江蘇之江化工有限公司30多名員工中毒。
但這些并未動搖地方官員發展化工業的決心。2009年2月,一家化工廠違規排放廢水導致鹽城市的自來水水源被污染,政府不得不停止對20萬人的自來水供應。鹽城市市長李強事后接受采訪時“輕描淡寫”地說,人們沒有必要聞化工就變色。在這位年輕的市長眼里,化工業投資周期短,見效快,“毫無疑問”是蘇北經濟發展的首選。
這種不容置疑的決心,不會讓空氣、土壤、海洋、天上的鳥和水里的魚感到害怕——雖然它們同樣是受害者,但人類卻足以因此感到恐懼。當手機鈴響,一條短信傳遞著不祥的預感,人們奪路而逃的心情,你還不能理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