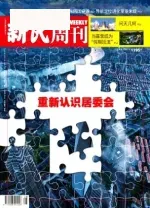兔年,不吃兔子
沈嘉祿
對小動物,尤其是像兔子那樣的弱者,不食,并不影響我們對蛋白質的攝取,相反,有利于修身養性,有利于培養一種憐憫弱者的情感。
猶豫兩天,怕有人譏諷我矯情或虛偽,但終于決定寫下如下文字。緣起春節期間的一次小酌,同席一老外朋友翠西,好奇地問我:“中國人在吃喝方面向來愛湊熱鬧,而且勇敢,兔年一到,會不會吃兔子呢?”
這個問題可能天真,也可能是個套,我沉默了一小會。我知道,兔肉做菜在中國“歷史悠久”,川菜中就不乏以兔肉為食材的肴點,比如陳皮兔、油淋兔、蔥椒兔塊、銀針兔絲、魚香酥皮兔糕等。有一年朋友送我一只纏絲兔,去了頭,拉直了軀體,收縮成一根肉腸狀的肉棍,肉質精細誘人。朋友說,這個纏絲兔是四川的特產,蒸一下,允稱佐酒妙品。但我從小不食兔肉,轉手送了人。幾年后去四川采訪,從成都出發前往三星堆,臨近廣漢時,看到高速公路或小鎮的道路兩邊擺著許多攤頭,每個小販前展開兩三張碩大的竹匾,一種濃油赤醬的拳狀食物堆得小山高。同行的成都朋友告訴我:這就是廣漢有名的小食:鹵兔頭。
廣漢一帶蓄養兔子歷史悠久,現在更是一大產業,加工纏絲兔后剔下的兔頭是下腳料,鹵一下就成了民間小食,當地人好這一口,一買就是五斤十斤,用簸箕兜來稱,全家老小晚上看電視,人手一只兔頭,啃得滿嘴醬油,其樂融融。
以我私見,兔子是弱勢群體中的一員,比之雞、鴨、鵝等更弱一籌。它逆來順受地在窩里呆著啃食一堆草或胡蘿卜,默默長大,絨毛被人剪去做成衣服帽子,軀干被瑜伽后“纏絲”。在今天,貓狗之外,有人還將軟軟愛意獻給了變色龍、鴨子、香豬、巴西龜,但很少有人將兔子寵養起來。也許它不懂得“狐媚偏能惑主”的潛規則,也許它素來淡泊寧靜,也許它拉屎特別臭。
處于食物鏈頂端的人類,一直視動物為天然食材或大補之物,但隨著文明程度的提升,不少美食家終于幡然醒悟,并非每一種動物都是上帝賜予的口福。為了避免中國人的形象繼續被老外誤解,我就對翠西說:“中國人現在大概很少再吃兔子了。如果你看中國還有專供食用的兔子,那就是出口的,專供歐洲美食家享用。”我想她也知道,歐洲人食用兔子是有光榮傳統的,菜譜也比較豐富,燒、烤、燉都有。兔子肉精瘦細膩,蛋白質高,脂肪少,據說還有防病治病的特殊功效,一直視亞洲人吃狗肉為野蠻的歐洲人,刀叉向兔而舉倒毫無心理障礙。
翠西又問我:“你是美食家,吃不吃兔子?”于是我跟她講了一個故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食物供應嚴重匱乏,餓得眼冒金星的上海人滿屋子找吃的,恨不得將四條腿的凳子劈了紅燒。我家鄰居偷偷養了一只兔子,竹籃子就是它的窩,負責養兔的男孩比我大兩三歲,每天跑到淮海公園里去割草喂它,那時候菜場里連一張爛菜皮都找不到。幾個月后,兔子長大了,它的大限也到了。男孩的父親,是個老資格的天吃星,倒提著渾身顫抖的兔子,雄赳赳地走出弄堂來到路邊,找到一條光滑的石階,狠狠地將兔子摔下去。根據一種“很內行”的說法,兔子不能用刀殺,得活活摔死。少不更事的我,跟在一群孩子后面瞎起哄。眼看一家伙下去,兔子居然沒當場斃命,一骨碌翻身過來,朝殺手連連作揖,似乎在祈求留一條活路給它。但天吃星哪肯放過嘴邊的活肉呢,提起來更加給力地一擊,那表情,似乎為自己剛才的一時手軟而氣惱呢。
兔子終于蹬了一下腿,斷氣了,他們家養的活物,似乎就天然地擁有處置它的權力。兔子被征服者提走了,石階上留下了鮮紅的印痕。這一幕永遠烙在我的腦海里。
雖然飼養家兔以及各種市場定位的深加工,不失為一門利潤可觀的產業,但吃不吃兔子倒值得考慮。我覺得,在免于饑餓的今天,面對足夠的食物,我們不妨把禁忌當作與自然取得平衡的前提。對小動物,尤其是像兔子那樣的弱者,不食,并不影響我們對蛋白質的攝取,相反有利于修身養性,有利于培養一種憐憫弱者的情感。在弱肉強食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更應體會到此中的深意。
當然,你非要吃,也不算犯法,我只能像一只兔子那樣看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