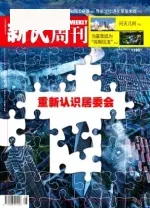你的財富被人“倍”了
金姬

逼近“紅線”
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這種擔憂在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尤為明顯。
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1年各項改革的具體部署中,收入分配改革就位列首位,明確提出要努力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而即將在2011年試點房產稅的重慶和上海,也在地方兩會上率先表態:先是重慶市長黃奇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將基尼系數由0.42降到0.35”(基尼系數0.4為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而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員會(簡稱“民盟上海市委”)也將在上海市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上提出一項有關“增強政府在初次分配中調節作用”的集體提案,因為他們調研發現上海行業收入差距已達6.4倍,而企業內部經營者與普通職工收入之比甚至超過10倍。
《新民周刊》了解到,由于此次民盟上海市委的調研內容只是上海六大行業(制造業、建筑業、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的基本薪酬,這意味著很多“灰色收入”和“變相福利”并不在計算之內。民盟上海市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向記者坦言:“我們做的是問卷調查,被調查者如果要隱瞞一些收入也不是沒有可能。這個話題太敏感了,真實的收入差距可能會讓老百姓更郁悶。”
最近有關“收入鴻溝”的媒體報道已經讓中國大多數老百姓的心“拔涼拔涼的”。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10年12月15日發布2011年《社會藍皮書》,中國社會總收入差距一直在擴大,基尼系數目前在0.5左右。而波士頓咨詢公司去年12月2日發布的《中國財富管理市場:機遇無限 挑戰猶存》則指出,中國內地的富人家庭已居世界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但只占所有中國家庭戶數的0.2%左右,這一比例遠遠低于其他國家和地區,比如美國是4.1%、瑞士是8.4%,而中國香港則達到了8.8%。中國在社會財富增長加速的同時,出現了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傾向(年均12.3%的速度增長,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貧富差距已經逼近國際公認的“紅線”。
2010年第二季度,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GDP每年都保持8%以上的增速,2010年估計也在10%左右。但廣大人民群眾似乎并沒有分享多少這場財富盛宴。“按照經濟學中的比較優勢理論,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國際貿易的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會獲益,從而縮小該國的貧富差距,但事實情況并非如此。”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里克·馬斯金(Eric S. Maskin)在去年也對這個崛起中的東方大國感到困惑。
收入分配是政治問題
“西方學者往往對中國問題說不清楚,因為他們看到的很多數據是有水分的。”近日在上海參加“中國下一站:機遇與選擇”學術研討會的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表示,他的夫人就是搞統計的,中國學者拿到的數據都未必準確,更何況老外呢?“在中國,搞經濟研究并不是純粹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其實在技術層面沒啥難度,但是有時候需要讓出一部分利益給百姓,而不是與民爭利。”
李煒光引用德國政治經濟學家兼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100年前提出的理論:一個經濟長期貧弱的民族在世界上突然崛起,未必是一件好事。它將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這種反差如果處理不好,有可能釀成巨大的災難。
中國民眾缺乏一種對整體利益的認同感,不同階層的分化明顯。雖然2010年的中國年度詞匯是“漲”,但頗具智慧的中國老百姓其實對“被”也很有感受。
當富二代開名車炫富時,十萬蟻族蝸居在北京地下室;當一些地方政府機構為官二代量身定做招聘職位時,幾百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當一個房管局長擁有數十套住房時,買房者為一套蝸居傾家蕩產……現在的中國,這樣的強烈對比并不鮮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曾對媒體表示:中國貧富急劇分化背后有兩大主因,一是腐敗,二是壟斷。非市場因素的“財富集中”,正是當下貧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根源。由于“蛋糕”的切分事關各方利益,最終結果是多與少的轉化,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必不可少地遇到重重阻礙,最大的阻力來源于某些既得利益團體。
面對中國當下的“不均”,復旦大學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研究所李維森對《新民周刊》表示,政府應該對廣大老百姓減稅和加薪。“一方面,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份額在不斷提高,目前已經基本上跟發達國家差不多,甚至高于美國和日本,而大量的財政收入只是肥了政府機構和國有企業,甚至出現年底突擊花錢的荒誕現象,國進民退現象令人擔憂。另一方面,中國普通居民收入落后于GDP增速,而官員的政績只是與經濟增長相掛鉤,一俊遮百丑,老百姓的幸福指數被忽視了。”
在民盟上海市委的提案中,寄希望于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發揮一定作用,例如將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從目前的36%逐步提高到國際公認的50%-60%,限定壟斷企業的工資增長,加強普通員工工資的合理增長,改變個人所得稅針對工薪階層而對高薪階層調節不力的局面……
作為減稅政策的多年擁躉,李煒光更注重再分配環節。一方面,他希望增加中產階層的比重,加快形成穩定的“兩頭小、中間大”的紡錘形社會結構。但目前的稅收政策往往針對中產階層,高薪階層有避稅手段,低薪階層可能還會受到一定政府補助,中產階層是主要繳稅群體,生活壓力不言而喻。而缺乏社會保障也使得很多即便有房有車的人生活得小心翼翼,生怕一場病或者一次意外就變成窮人。
另一方面,李煒光建議取消一些不必要的稅種,不再增加百姓負擔,因為現在的政府已經掌握了相當大的資源和財富,而中國人的稅負也已經很高了。
就拿個人所得稅來說,征稅項目共有11個: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企事業單位承包(承租)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等。工資薪金所得只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類,種類之多以及不同稅率,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中產階層稅負較重。現實生活中我國大部分高收入者恰恰不是以薪酬形式獲取收入的群體,比如私營廠主、企業老板可以只給自己象征性地開一點薪酬,甚至可能完全不開薪酬。本應是高收入者多納稅的個稅政策,卻只是高薪酬者多納稅。
對于重慶和上海即將試點的房產稅,李煒光并不看好。收稅是為納稅人服務的,但是我國財政并不公開透明,每年上繳的稅收具體用在哪些地方,怎么用,效果如何,老百姓只能交錢而沒有十分具體的知情權。而房產稅是否能夠抑制高房價還很難說,這筆稅收是否收得起來,能否用到實處,更是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