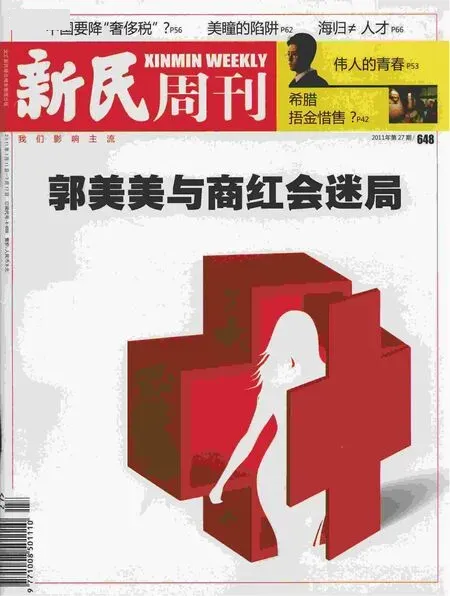抉擇之難
夏佑至
阿基米德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動整個地球。杠桿定律有這種驚人的效果,但前提是支點合適,并且足夠穩固。許多人把改變現實的希望寄托在不恰當的對象上,那情形不像通過杠桿撬動重物,倒像是一個人把全身的力量壓向一根針——結果什么都沒有改變,反而讓自己徒然痛苦。
今年“兩會”以來,由于通貨膨脹已成定局,上調個稅起征點的呼聲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個人所得稅法》隨即宣布修訂,以回應這種呼聲。修訂草案將個稅起征點從2000元上調至3000元,隨即向公民征求意見,收到的反饋意見之多,超過了任何一部公開征求意見的法律草案。大多數意見不認同3000元這個數字,大城市的工薪階層——他們是個人所得稅的主要的征收對象——反對的聲音尤其強烈。人大法工委6月底宣布個稅起征點將維持在3000元不變時,這個群體的失落感是最強的。
很多人以為修訂《個人所得稅法》是一個支點,借助這個支點,我們能提高中間階層的收入,改善不合理的分配狀況。但改善分配狀況是修訂個稅法難以承受之重。寄望越高,失望越深,支點突然變成了一根針,深深刺痛了很多人。不滿的聲音迅速在網絡上傳播,并且超越了對起征點的質疑。抱怨開始上升,個稅的稅制和整體稅負成了抱怨的對象,征稅的法律程序也受到詬病,自然而然地,質疑的聲音最后落到了稅收的支出上——此間公布的關于“三公”開支的數據及貪腐官員向海外轉移財產的數據激起了強烈的憤怒,納稅人有理由相信,他們繳納的稅收沒有得到合理的使用。
納稅人的質疑、抱怨和憤怒都不是無中生有。個人所得稅在各國普遍存在,其目的在于調節收入差距,大多采取以家庭為征收對象,實行累進稅制,也即家庭收入越高課稅越重,但同時輔以各類退稅政策。在中國,個稅由工作單位代扣代繳,最終,缺乏避稅手段、也沒有灰色收入的工薪階層,成為主要的課稅對象。由于累進級數多,征繳以個人而非家庭為單位,并無退稅,整個稅制顯得很不公平。要求全面改進個稅稅制的呼聲由來已久,但數次修訂的內容多限于提高個稅起征點,頂多對累進方式略加調整,對呼聲最高的以家庭為單位征稅毫無回應,并一口拒絕了浮動起征點(根據各地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制定不同起征點、起征點與CPI指數掛鉤)的建議。
對實際負責設計和修訂個稅稅制的專家來說,拒絕在公眾呼聲最高的環節讓步,這種強硬的姿態背后隱藏著進退兩難的困境。要真正改革個稅稅制,就要消除灰色收入,“需要實現納稅人信息申報的實名制,個人全部收入信息應該實現網絡全覆蓋,納稅人申報制度也要健全”。毫無疑問,此方案像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一樣,首先將遭到官員的抵制,因此萬難推行。既然不能做根本改革,回應民眾改革呼聲的途徑只剩下提高起征點一條路,但要持續提高起征點,納稅人范圍將進一步減少,又會影響政府財政收入。就這樣,個稅改革也在民眾呼聲和制度現實兩者間首鼠兩端,難以抉擇。
在這種情形下,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6月30日最終通過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毫無預兆地將起征點定為3500元。這固然對公眾不滿情緒是一種撫慰,但也再次將改革的困窘局面揭露無遺:公眾的改革呼聲高漲,但由于種種力量的掣肘,改革難以深入進行,只能在枝節問題上做文章,由此導致政策選擇面越來越窄。
個稅起征點只是個稅改革的一部分,個稅改革又只是整個稅制改革的一部分。稅改的核心是界定政府在稅收征收和支出兩個環節的權力。在征稅環節,須明確征稅權是立法機構的權限,非經公眾充分討論和立法機構許可,政府不能征稅。在支出環節,政府開支必須接受人大以預算審核等形式進行的監督,財政收支的信息必須對公眾公開,隨時接受媒體和公眾的質詢。因此,稅改不只是財稅領域的改革,也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稅改不能永遠圍著個稅起征點爭辯不休,這一點在很多財稅專家那里并無分歧。問題是,有遠大目標卻無現實路徑,這種改革的困境不是稅改獨有的現象,而是所有領域的改革共同面對的現實。很多年以來,技術官員主導著中國公共政策的選擇。他們賴以決策的依據,不是社會中各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而是相對比較超然的工具理性,也即技術上的合理性。但個稅改革的困境揭示出,公共政策正在民意和利益集團之間搖擺不定:要么跟隨民意,要么堅持現有的利益格局,改革者難以維持自身的超然地位,必須在兩者之間做出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