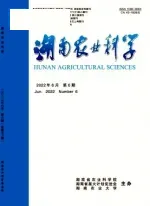水分對側柏林地土壤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
孫曉涵,賀康寧,劉 碩,李玉娥,萬運帆,郭倩倩,李安超,董 梅
(1.北京林業大學水土保持與荒漠化防治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83;2.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森林是地球上分布最廣的植被類型,覆蓋率達13.9%。森林生態系統作為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在全球碳氮循環過程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1]。林地土壤的溫室氣體排放研究是當前全球陸地生態系統碳氮循環和溫室氣體源匯功能方面的一個重要內容。土壤水分是影響土壤溫室氣體排放的關鍵因素之一。目前,國內外許多學者已經對森林土壤水分含量與土壤溫室氣體排放之間的關系做了大量研究[2-4],但均是在野外原位進行觀測,而土壤水分含量變化對林地土壤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未見報道。
側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是我國溫帶地區的主要森林類型之一[5]。據2005年北京市二類清查數據顯示,北京市側柏總面積為88 003.8 hm2[6],是北京低山和平原地區的主要常綠樹造林樹種。目前,我國對側柏做的研究多集中在側柏生物量研究方面[7-11],對側柏林地土壤溫室氣體排放的研究相對較少[12-13],僅集中在側柏林地土壤CO2排放研究上,側柏林地土壤水分與CO2、N2O、CH4排放關系的研究未見報道。筆者以側柏林地為試驗對象,通過室內培養對不同土壤水分條件下側柏林地土壤溫室氣體排放通量進行監測,探討土壤水分變化對側柏林地土壤CO2、N2O、CH43種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旨在進一步研究闡明林地土壤水分與溫室氣體排放之間的關系。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位于北京市西北郊太行山北部。實驗基地高程范圍11.28~1 162.70 m。該區屬華北大陸性季風氣候,春季干旱多風,夏季炎熱多雨,冬季干燥寒冷;年均氣溫12.2℃,最高、最低氣溫分別為39.7、-19.6℃,年降雨量約700 mm,多集中在7~8月[14]。選擇林地土壤結構和發育情況一致區域為實驗采樣區,林地生境條件如下:林地類型為純林地,樹種為側柏,海拔為150 m,林齡為,40 a,平均胸徑為12 cm,郁閉度為30%,坡度30°,坡向為陽坡,土壤類型為棕壤土,林下植被為荊條、繡線菊、胡枝子、野葡萄、白草和大油芒。土壤含水量16.77%,最大田間持水量40%,土壤容重0.942 g/cm3,土壤有機碳含量50.22 g/kg,pH值6.86,全氮23.77 g/kg,全磷0.95 g/kg,全鉀17.64 g/kg。
1.2 野外采樣方法
在林地選取3個5 m×5 m樣地,將每個樣地等分為4個小區,在每個小區正中取1個土樣,共采取土樣12個(圖1)。采集時將PVC管(內徑25 cm、高20 cm)底端放在地面上,插入土壤至PVC管上端與地面齊平為止,保留枯枝落葉層,用鐵鍬取出土柱,用聚乙烯膜封口,盡快運回實驗室。

圖1 野外取土示意圖
土柱取出后,在采點0~10 cm和10~20 cm土層取3個鋁盒和1個環刀用于土壤物理性質分析;取0~20 cm土壤,去除樹根石塊后混勻裝入封口袋帶回實驗室,風干后分別過2 mm和0.25 mm篩測其化學性質。
1.3 實驗室培養與測定
1.3.1 土壤理化性質指標測定 土壤物理性質指標測定方法參照《土壤農化分析手冊》[15]和文獻[16]。土壤化學性質指標由常規化學分析方法分析[15]。
1.3.2 土壤水分控制 把采集的12個土柱帶回實驗室,當日稱重,按最大田間持水量20%、40%(約為正常含水量)、60%和80%進行控水處理,每個處理3個重復,每日8∶00、18∶00稱量土柱總重,低于控水水平時,立即補充至設定土壤含水量。
1.3.3 人工氣候箱控制與氣體測定 根據中國氣象局網站提供數據設置人工氣候箱參數,模擬研究區春秋季節自然條件,設置相同溫度(10℃)、光照和空氣濕度(40%),培養周期30 d。為使采氣裝置嚴格密封,氣體采集箱用外徑25 cm(等同于PVC管內徑)、高18 cm、厚度5 mm白色透明有機玻璃制成,每隔一天上午9∶00~11∶00時間段內采氣,上罩后每隔10 min(0,10,20,30 min)用自動采樣器進行取氣,每次采樣結束后共采4(4次抽樣)×4(4種處理)×3(3個重復)=48個氣體樣品,每個氣樣30 mL,用Agilent7890A氣相色譜儀測定樣品中CO2、CH4和N2O的濃度。根據各氣體濃度,換算成單位土壤的各氣體累計產量,并用累積產量-時間曲線的最大斜率代表培養土壤的氣體產生速率[17]。氣體通量正值表示氣體從土壤排放到大氣,負值表示土壤為氣體的匯。
2 結果與分析
2.1 水分對側柏林地土壤CO2排放的影響
60%水分處理在培養初期土壤CO2排放通量波動較大(圖2),4 d(219.843 mg/m2h)后隨著培養時間的延長,土壤CO2排放通量逐漸下降并趨于穩定。20%和40%水分處理在整個培養周期波動較小,80%水分處理呈波浪式波動,整個培養過程中出現2次高峰值,分別在16 d(89.202 mg/m2h)和24 d(85.962 mg/m2h),最低值為38.638 mg/m2h(2 d)。各處理在培養初期波動相對較大,隨著培養時間的增長,各水分處理CO2排放通量漸趨穩定且各處理間的差異逐漸減小。

圖2 不同土壤水分條件下CO2排放變化
在整個培養過程中20%、40%、60%、80%水分處理CO2平均排放通量分別為21.948、47.912、96.351、63.200 mg/m2h。總體看來,側柏林地土壤CO2排放通量60%>80%>40%>20%(圖2)。
2.2 水分對側柏林地土壤N2O排放的影響
側柏林地土壤表現為60%和80%水分處理在培養前12 d土壤N2O排放通量波動較大(圖3),且隨培養時間增加排放通量逐漸增加,并在培養第12 d同時達到最高值,分別為0.041和0.052 mg/m2h,12 d后隨著培養時間的延長,土壤N2O排放通量相對穩定。20%和40%處理在整個培育周期中波動較小。
在整個培養過程中20%、40%、60%、80%水分處理N2O平均排放通量分別為0.002、0.004、0.015、0.021mg/m2h。總體看來,側柏林地土壤N2O排放通量80%>60%>40%>20%(圖3),但20%與40%在整個培養過程中排放通量差距不大,這可能因為在正常含水量以下,水分含量不是土壤N2O排放主要限制因子。

圖3 不同土壤水分條件下N2O排放變化
2.3 水分對側柏林地土壤CH4吸收的影響
側柏林地在10℃溫度下,土壤CH4通量均為負值,林地土壤為大氣CH4的匯(圖4)。40%水分處理培養前4 d吸收通量較大,培養第2 d達到最大值0.082 mg/m2h,培養后期土壤CH4通量變化相對穩定。其他3個水分處理在整個培養過程中土壤CH4吸收通量值忽高忽低,但波動范圍較小,均在0.001~0.037 mg/m2h范圍內。

圖4 不同土壤水分條件下CH4排放變化
整個培養過程中20%、40%、60%、80%水分處理CH4平均吸收通量分別為0.018、0.038、0.020、0.012 mg/m2h。總體看來,側柏林地土壤CH4吸收通量表現為80%<20%<60%<40%。
3 討 論
森林土壤對大氣溫室氣體濃度具有重大貢獻,同時各溫室氣體的產生和排放量也受其所處環境狀況的影響,土壤理化性質對溫室氣體的排放起著重大作用[18]。試驗中,側柏林地土壤水分變化對3種溫室氣體排放影響如下。
3.1 側柏林地土壤水分變化對CO2排放通量的影響
影響土壤CO2排放的所有非生物因素中,土壤濕度變化是影響土壤CO2排放變化的重要因素[19]。試驗發現,林地土壤水分含量在20%~60%范圍內,隨土壤水分含量增加,林地土壤CO2排放通量有增加的趨勢,超過60%隨土壤含水量的增加而減少。一般認為合適的土壤濕度有利于可溶性有機質含量的增加,促進微生物的生長、活動[18,20]。試驗中土壤含水量為最大田間持水量的60%時土壤CO2排放通量最大,最適宜側柏林地微生物活動。
整個培養過程中60%處理土壤CO2排放通量第4 d達到最大值,明顯高于其它值,這可能是因為風干一段時間的土壤再濕潤會引起CO2排放通量在短期內增加[20]。土壤正常含水量為40%,通過加水到60%,提高了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利于微生物的呼吸,使CO2排放增加,但隨著時間增加,密閉的罩內環境使得CO2濃度增加,抑制土壤微生物呼吸,使CO2排放減少[21]。20%、40%和80%水分處理沒有此現象,可能由于水分不足或過多使土壤微生物活性較低,呼吸較弱,罩內CO2濃度變化不是影響土壤微生物呼吸的主要限制因子。
3.2 側柏林地土壤水分變化對N2O排放通量的影響
水分是影響土壤中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這些生物過程最重要因素之一[22]。試驗中土壤水分含量低于40%時,土壤N2O排放通量變化不明顯;土壤水分含量高于40%時,N2O排放通量隨土壤含水量的上升隨之增加。這可能是因為土壤處于最大田間持水量以下時,硝化作用是N2O的最基本來源,N2O產生主要由硝化作用產生,N2O的排放量隨土壤水分的增加而增加[23]。
側柏林地土壤60%和80%水分處理在培養前12 d隨培養時間增加排放通量逐漸增加,12 d后隨著培養時間延長土壤N2O排放通量相對穩定,這可能是因為培養時2處理加水相對較多,土壤水分變化顯著,土壤的干濕交替使得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交替成為N2O的主要產生機制,同時土壤的干濕交替還能抑制反硝化過程中的深度還原,使得N2O的產生量增大[24]。已有研究表明[25],在土壤含水量較低,土壤水分變化顯著時,會出現N2O通量峰值。
3.3 側柏林地土壤水分變化對CH4排放通量的影響
水分對土壤中CH4的產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是因為CH4產生所需的厭氧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土壤水分狀況,只有當水分阻止了氧的擴散形成嚴格的厭氧環境時,CH4才能產生[26]。研究發現土壤水分含量高于40%時,土壤CH4吸收通量隨土壤含水量的增加而減少;土壤水分含量低于40%時,土壤CH4吸收通量隨土壤水分的增加而增加。可能因為濕度過高使水分更多地布滿土壤空隙,土壤空氣變少,限制空氣擴散,土壤微生物活性從好氣過程變為嫌氣過程,CH4氧化細菌活性受到限制,濕度過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土壤對CH4的吸收[27]。該研究還表明,過低的土壤含水量也不適宜CH4的吸收。
[1] 潘新麗,林 波,劉 慶.模擬增溫對川西亞高山人工林土壤有機碳含量和土壤呼吸的影響系[J].應用生態學報,2008,19(8):1637-1643.
[2] 李海防,夏漢平,熊燕梅,等.土壤溫室氣體產生與排放影響因素研究進展[J].生態環境,2007,16(6):1781-1788.
[3] 董云社,彭公炳,李 俊.溫帶森林土壤排放CO2,CH4,N2O時空特征[J].地理學報,1996,120-128.
[4]劉 實,王傳寬,許 飛.4種溫帶森林非生長季土壤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亞氮通量[J].生態學報,2010,30(15):4075-4084.
[5] 沈國舫,關玉秀,齊宗慶,等.北京市西山地區適地適樹問題的研究[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1980,32-46.
[6] 段 劼,呂 巍,馬履一,等.北京市側柏人工林水源涵養功能的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10,38(9):4956-4958.
[7] 李 朝,周 偉,關慶偉,等.徐州石灰巖山地側柏人工林生物量及其影響因子分析[J].安徽農業大學學報,2010,37(4):669-674.
[8] 王 婷,袁志良,葉 永,等.嵩山國家森林公園不同年齡側柏人工林生物量初步研究[J].河南科學,2009,27(7):817-820.
[9] 閆家鋒,關慶偉,鄧送求,等.徐州云龍山側柏林生物量和生產力研究[J].林業科技開發,2009,23(02):48-50.
[10]閆晨曦,唐光金.油松和側柏的生長及生物量[J].重慶工學院學報,2008,22(12):67-70.
[11]李 朝,王振營,王 宇.間伐對側柏人工林生物量的影響[J].林業科技開發,2010,24(1):68-71.
[12]王鶴松,張勁松,孟 平,等.華北山區非主要生長季典型人工林土壤呼吸變化特征[J].林業科學研究,2007,20(6):820-82.
[13]王鶴松,張勁松,孟 平,等.側柏人工林地土壤呼吸及其影響因子的研究[J].土壤通報,2009,40(5):1031-1035.
[14]嚴 密.鷲峰國家森林公園生態效益評價研究[G].北京:北京林業大學,2005.
[15]鮑士旦.土壤農化分析[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0.
[16]高建峰.農田土壤含水量監測方法研究[J].安徽農學通報,2010,16(14):88-89.
[17]謝軍飛,李玉娥.土壤溫度對北京旱地農田N2O排放的影響[J].中國農業氣象,2005,26(1):7-10.
[18]李世朋,汪景寬.溫室氣體排放與土壤理化性質的關系研究進展[J].沈陽農業大學學報,2003,34(2):155-159.
[19]Subke J A,Reichstein M,Tenhunen J D.Explaining temporal variation in soil CO2efflux in a mature spruce forest in Southern Germany[J].Soil Biology&Biochemistry,2003,35(11):1467-1483.
[20]孫向陽,郭青俊.妙峰山林地CO2釋放量的初步研究[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1995,17(4):22-28.
[21]侯 琳,雷瑞德,王得祥,等.森林生態系統土壤呼吸研究進展[J].土壤通報,2006,37(3):589-594.
[22]Rover M,Heinemeyer O,Kaiser E A.Microbial induced nitrous oxide emissions from arable soil during winter[J].Soil Biochein,1998,30:1859-1865.
[23]Mummey D L,Smith J L,Bolton J R H.Nitrous oxide flux from a Shrub-steppe ecosystem:sources and regulation [J].SoilBiol.Biochem,1994,26(2):279-286.
[24]王智平,曾江海,張玉銘.農田土壤N2O排放的影響因素[J].農業環境保護,1994,13(1):40-42.
[25]杜 睿,黃建輝,萬小偉,等.北京地區暖溫帶森林土壤溫室氣體排放規律[J].環境科學,2004,25(2).
[26]顏曉元,蔡祖聰.淹水土壤中甲烷產生的影響因素研究進展[J].環境科學進展,1996,4(2):24-32.
[27]劉玲玲,劉允芬,溫學發,等.千煙洲紅壤丘陵區人工針葉林土壤CH4排放通量[J].植物生態學報,2008,32(2):431-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