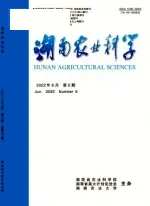湘江流域礦區Cd污染土壤的修復及其綜合利用
宓彥彥 ,譚長銀 ,黃道友 ,楊 燕,萬大娟,余 霞,孫 花
(1.湖南師范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2.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湖南 長沙 410125)
我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食品安全正面臨多方面的嚴峻挑戰,其中,土壤污染已成為影響我國資源、生態、環境方面的突出問題之一,對我國食品可持續生產能力構成潛在威脅[1]。土壤重金屬污染是污染面大、持續時間長、對食品安全和人群健康構成嚴重威脅的土壤污染類型。重金屬具有毒性、不被生物降解、在土壤中積累,并可通過食物鏈危害人體健康。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的“砷毒”、“血鉛”、“鎘米”等環境污染,使得土壤重金屬污染已成為人們當前高度關注的環境問題之一,《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也成為首個獲國務院批準的“十二五”規劃。
湖南省礦產資源豐富,被譽為“有色金屬之鄉”,在湖南省境內已探明有色金屬礦床多達340余處。有色金屬的開采和冶煉在促進湖南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有色金屬礦區產生的廢水、廢渣和粉塵,對礦區周圍土壤造成嚴重的重金屬污染,進而通過食物鏈在動植物體內富集,危害人體健康。湖南大部分礦區分布在湘江流域,礦業活動造成了湘江水質的惡化和湘江流域土壤的污染。自20世紀60年代湘江檢測出Cr、Pb、Mn等重金屬以來,湘江水質一直呈惡化趨勢。現在,湘江水污染中的主要重金屬污染已由Hg轉變為Cd和As,這種變化與該湘江流域有色金屬礦產的開采和冶煉是分不開的,同時這種變化也帶來了以Cd為主的礦區土壤重金屬污染。筆者綜合了近幾十年來對湘江流域礦區土壤Cd污染狀況的調查結果,對湘江流域礦區Cd污染土壤的不同修復措施進行了比較,通過湘江流域Cd污染土壤的綜合利用進行分析,對湘江流域礦區Cd污染土壤今后的污染修復和綜合利用提出了設想。
1 湘江流域礦區土壤Cd污染現狀及成因
1.1 湘江流域礦區土壤Cd污染的現狀
湖南主要的金屬礦區大多分布在湘江流域,如郴州市柿竹園鉛鋅礦區、衡陽市常寧市水口山鉛鋅礦區、株洲市石峰區清水塘冶煉區、湘潭市岳塘區錳礦區、婁底市冷水江市錫礦山礦區等。這些金屬礦產的開采和冶煉也必然給流域內的土壤帶來重金屬污染。據報道,湖南省因有色金屬礦山開采導致的Cd、Pb、As等重金屬污染的土地面積達2.8×104km2,占全省總面積的13%[2]。雷鳴等[3]對湖南9個縣市采礦區和冶煉區附近的水稻土中Cd等五種重金屬進行了調查和分析。在所調查的區域中,有6個縣市采礦區和冶煉區附近的水稻土受到Cd的嚴重污染,其中衡陽常寧市水口山鉛鋅礦區和株洲清水塘冶煉區附近的水稻土受到重金屬的嚴重污染,有四個礦區和冶煉區潛在生態風險很高(表1)。

表1 9個采礦區和冶煉區水稻土中Cd含量、污染程度和潛在風險程度
對湖南郴縣東西河流域的土壤調查結果顯示,該流域土壤中Cd含量本底區<廢礦水污染區<尾礦污染區,尾礦污染區的污染最為嚴重[4]。李小江等[5]對株洲清水塘地區土壤及農作物重金屬含量調查顯示,稻田表層土中除鉛未出現超標外,砷、Cd、汞均有超標現象,而Cd的超標率為100%最大超標倍數3.67倍,并且旱地表土重金屬污染程度比稻田嚴重,稻谷和包菜中的Cd嚴重超標。永州鉛鋅礦尾渣土壤中Cd含量可達105.88 mg/kg,遠遠超出土壤環境質量標準,鉛鋅礦尾渣土壤中重金屬表現出強生態風險性[6]。已有的資料表明,湘江流域礦區土壤Cd污染嚴重,有較高的生態風險。
1.2 湘江流域礦區土壤Cd污染的成因
湘江流域有色金屬的開采和冶煉所產生的“三廢”物質是礦區土壤重金屬的重要來源。采礦、運礦、冶煉和排渣過程產生的大量重金屬煙塵,通過擴散和沉降進入土壤,造成土壤Cd污染。礦物開采和冶煉過程中排放的廢水中也含有大量Cd,未達標排放的礦業廢水是造成土壤Cd污染的另一個原因[3]。郴州有色金屬礦山所排廢水中Cd超過排放標準約1.2~9.0倍,常寧水口山四廠和鉛鋅礦所排廢水中Cd超標265倍,湘江株洲段江底底泥Cd含量已超過日本“骨痛病區”河流中底泥含量的幾十倍[7]。另外,金屬礦山開采、選礦和冶煉等活動產生的廢石、尾礦和廢渣是導致土壤Cd污染的重要來源。這些固體廢棄物的堆放,其中的硫化物礦物長期暴露于地表,與水圈、大氣圈及微生物相互作用發生氧化形成礦山酸性排水,增加了重金屬淋溶和擴散[8]。本底值高也是流域內土壤Cd污染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郴縣東西河流域非污染土壤中的Cd含量遠高于湖南同類土壤的本底值,其Cd、As含量超過了國家土壤環境質量三級標準,屬高本底區[4]。此外,污水灌溉和農業過程(如化肥和農藥的施用)也可能是流域土壤Cd污染的重要來源。
2 湘江流域礦區Cd污染土壤修復實踐
對于重金屬污染土壤的修復,從修復原理上分,主要包括物理修復、化學修復和生物修復方法,實際修復過程中,物理修復和化學修復方法也常常結合在一起使用。湘江流域礦區Cd污染的修復實踐中,物理修復和化學修復應用相對較多,而隨著生物修復技術的日益成熟,生物修復技術的應用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2.1 湘江流域礦區Cd污染土壤的物理和化學修復
物理修復主要是通過換土、客土、深耕翻土、固化或鈍化等措施降低土壤重金屬的濃度或者使土壤重金屬失去活性;化學修復就是通過添加一些改良劑,改變重金屬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態,從而降低土壤重金屬的遷移性和生物有效性。湘江流域礦區Cd污染土壤修復實踐中,投資較大的物理或工程方法應用相對較少,改良劑的應用相對較多。廖立兵等[9-12]以海泡石、膨潤土和生石灰為材料對株洲地區Cd污染農田土壤進行修復,結果顯示,膨潤土、海泡石和石灰的組合對降低小白菜中Cd含量效果顯著。朱奇宏等[13]在湖南省某工業城市市郊Cd污染區進行了田間小區試驗發現,施用改良劑(石灰、鈣鎂磷肥、海泡石和腐殖酸等)有效改變了土壤Cd的存在形態,降低了農作物中的Cd含量,其中施用海泡石可使糙米Cd含量降低37.6%。
2.2 湘江流域礦區Cd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復
生物修復技術(特別是其中的植物修復)主要是通過在污染土壤上種植超積累植物,利用其對重金屬的吸收和積累去除土壤重金屬,由于具有成本低、不破壞土壤結構、不造成地下水及其他環境二次污染等優點,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14-15]。近年來,植物修復技術在湘江流域Cd污染土壤的修復實踐中應用較廣。佘瑋等[16]研究苧麻對湖南冷水江銻礦區Sb、Cd、As和Pb 4種重金屬的吸收富集能力時發現,雖然苧麻體內Cd含量沒有達到超積累植物的含量(富集系數小于1),但苧麻對Cd的轉運能力較強(轉運系數為1.45)。說明苧麻能夠從污染土壤中吸收Cd,并將其中的大部分轉運到地上部分積累于組織器官中。湖南柿竹園有色金屬礦區修復植物的調查發現,礦區植物對重金屬的吸收表現出3種特征:將重金屬累積于體內的富集型植物(如蜈蚣草和苧麻),吸收了大量重金屬但地上部重金屬含量較少的根部囤積型植物(如攀倒甑和木賊)和少量吸收重金屬的規避型植物(如蔓出卷柏和芒草)。其中,蜈蚣草可用于修復As、Cd、Pb、Zn等重金屬復合污染土壤,苧麻是Cd的富集植物,也是As的耐性植物[17]。劉益貴等[18-21]調查了湖南湘西鉛鋅礦區六個礦業廢棄地的植被組成,分析結果顯示:滿天星葉片中Cd含量最高,為310 mg/kg,其次是加拿大楊和地枇杷,其葉片中Cd含量分別為231、212 mg/kg。地上部分Cd含量超過100 mg/kg的植物還有大田灣的醴腸、鬼針草、苦蘵和半邊蓮,以及三立的蒼耳和野艾蒿等,這些植物可能都具有超積累Cd的潛力。
3 湘江流域礦區Cd污染土壤的綜合利用
物理修復、化學修復和生物修復各有優缺點,實際應用過程中往往可組合使用。污染土壤修復的目的是實現污染土壤的安全高效利用,在現有技術和經濟條件下,并非受到污染的土壤一定要修復以后才可以利用。另外,在修復過程中,放棄土壤的利用價值也是一種土地資源的浪費。因此,在污染修復過程中應當根據污染物種類和污染的嚴重程度對污染土壤進行分類綜合利用。
近年來,湘江流域礦區Cd污染土壤的綜合利用有過不少嘗試。綜合利用主要通過兩條途徑:一是通過種植非食用植物,如耐性高大喬木等,這樣可以切斷重金屬在食物鏈中的傳遞;二是根據污染途徑和程度,有針對性的改變農業種植模式從而達到污染土壤的安全高效利用。在湖南安化某鈾礦區采用桑蠶生產模式替代糧食生產模式,這種模式中斷了土壤Cd污染在食物鏈中的傳遞,使污染土壤得以修復,農田年均產值比種水稻提高2 880元/hm2,比種玉米提高8 880元/hm2,耕層土壤Cd含量年平均下降1.33 mg/kg[22]。曾清如等[4]在郴縣東西河流域根據重金屬污染程度不同,考慮不同的栽培制度、收獲部位以及利用方式,采用綜合防治和利用措施,取得了一定的綜合利用成效。
在輕污染區(高本底區)通過施用石灰、鈣鎂磷肥和有機肥來改良土壤,在改良的土壤上種植了水稻、玉米、大豆、辣椒、豆角和茄子等,結果農作物長勢也良好,產量達到正常水平,Cd含量也未見超標。在中污染區(廢礦水污染區),建立繁育水稻良種基地,將繁育的種子在非污染區種植,籽實Cd含量未見超標;種植油菜,其生長良好,產量與品質均未見降低。在重污染區(尾礦污染區)化學改良劑的治理效果差,大部分作物中Cd含量超過國家農產品衛生標準,此區域主要考慮種植非食用植物,如對重金屬具有抗性的經濟喬木和繁育果樹苗木,包括楊樹、果苗(如柑桔、奈李、梨等苗木)及其他花卉苗木。
4 結語
湘江流域礦區土壤(特別是農田土壤)Cd污染嚴重,其成因與湘江流域有色金屬的開采和冶煉產生的“三廢”物質有關,也與流域內本底值偏高、污水灌溉和農業過程等因素有關。在流域Cd污染土壤治理方面已有了物理、化學和生物方法等多種修復方法的實踐。近年來,在湘江流域礦區Cd污染土壤的綜合利用方面也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流域內未來的土壤修復和綜合利用工作有以下幾個思考的方向:(1)多種修復措施的組合與集成,以期對礦區Cd污染土壤(特別是嚴重污染的土壤)取得更好的修復效果;(2)在強調Cd污染土壤修復的同時,通過各種農業技術措施,對輕度污染的土壤進行綜合利用;(3)建立一套比較完善的適合于湘江流域礦區Cd污染土壤的污染修復和高效利用方法體系,并進行大面積示范推廣。
[1] 趙其國,黃國勤,錢海燕.生態農業與食品安全[J].土壤學報,2007,44(6):1127-1134.
[2] 郭朝暉,朱永官.典型礦冶周邊地區土壤重金屬污染及有效性含量[J].生態環境,2004,13(4):553-555.
[3] 雷 鳴,曾 敏,鄭袁明,等.湖南采礦區和冶煉區水稻土重金屬污染及其潛在風險評價[J].環境科學報,2008,28(6):1212-1219.
[4] 曾清如,楊仁斌,鐵柏青,等.郴縣東西河流域重金屬污染農田的防治技術和生態利用模式 [J].農業環境保護,2002,21(5):429-431.
[5] 李小江,易艷紅.清水塘地區土壤重金屬污染現狀及修復技術研究[J].環境科學與技術,2004,27(3):61-62.
[6] 彭暉冰,劉云國,李愛陽.鉛鋅礦尾渣土壤中重金屬的形態及潛在生態風險[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33(3):345-347.
[7] 王秋衡,王淑云,劉美英.湖南湘江流域污染的安全評價[J].中國給水排水,2004,(20):104-105.
[8] 張 溪,周愛國,甘義群,等.金屬礦山土壤重金屬污染生物修復研究進展[J].環境科學與技術,2010,33(3):106-109.
[9] 廖立兵,姜 浩,何茂乾,等.礦物改良劑在重金屬污染土壤修復中的應用—湖南株洲地Cd、Pb污染土壤的修復實驗 [J].礦物學報,2010,(S1):162.
[10] 龔海軍,劉昭兵,紀雄輝,等.新型土壤改良劑對水稻吸收累積Cd、Pb 的影響初探[J].湖南農業科學,2010,(3):50-53.
[11] 王永強,肖立中,李伯威,等.不同改良劑對復合污染重金屬形態與再分配的影響 [J].安徽農業科學,2009,37(34):17027-17029,17037.
[12] 李榮林,王秀軍,李優琴.礦物改良劑調控蔬菜重金屬污染研究[J].江西農業學報,2009,21(9):163-165.
[13] 朱奇宏,黃道友,劉國勝,等.改良劑對Cd污染酸性水稻土的修復效應與機理研究 [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10,18(4):847-851.
[14] McGrath S P,Lombi E,Gray C W,et al.Field evaluation of Cd and Zn phytoextraction potential by the hyperaccumulators Thlaspi caerulescens and Arabidopsis halleri[J].Environ Pollut,2006,141:115-125.
[15] Terry M.Phyto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s from soils[J].Adv Biochem Eng/Biotechnol,2003,78:97-123.
[16] 佘 瑋,揭雨成,邢虎成,等.湖南冷水江銻礦區苧麻對重金屬的吸收和富集特性[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10,29(1):91-95.
[17] 雷 梅,岳慶玲,陳同斌,等.湖南柿竹園礦區土壤重金屬含量及植物吸收特征[J].生態學報,2005,25(5):1146-1149.
[18] 劉益貴,彭克儉,沈振國.湖南湘西鉛鋅礦區植物對重金屬的積累[J].生態環境,2008,17(3):1042-1045.
[19] 楊中雄,吳桂容,曲芬霞,等.錫冶煉廠周邊果園土壤和果樹重金屬污染研究[J].湖南農業科學,2010,(4):67-69.
[20] 吳桂容,敖子強,林文杰,等.黔西北土法煉鋅區土壤重金屬污染及其治理對策[J].廣東農業科學,2010,37(6):107-109.
[21] 李勁峰.冶煉廠重金屬污染物對周邊農田土壤動物生態效應的影響[J].安徽農業科學,2010,(4):1937-1939,1942.
[22] 王凱榮,陳朝明,龔惠群,等.Cd污染農田農業生態整治與安全高效利用模式[J].中國環境學報,1998,18(2):9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