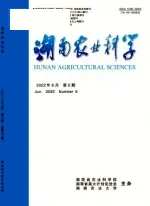喀斯特地區土壤微生物量效應研究
吳小玲
(湖南農業大學生物科學技術學院國家植物科學實驗中心,湖南 長沙 410128)
喀斯特地區是世界典型的溶巖生態脆弱區,土壤微生物是土壤有機質和養分轉化和循環的動力,又是土壤養分的儲存庫,對土壤中養分的轉化和供應起著重要的作用。土壤微生物是土壤中物質循環的調節者,同時也是有機物質庫和速效養分的一部分[1],其本身含有大量的養分。土壤微生物的數量分布,不僅是土壤中有機養分、無機養分以及土壤通氣透氣性能的反映,而且亦是土壤中微生物活性的具體體現[2-3]。土壤微生物量(MB)是土壤活的有機質部分,指土壤中除去活的植物體(如植物根系等)和動物外,體積小于5×103μm3的生物物質的總量,其主要生物類群有細菌、真菌、藻類和原生動物等[4],廣義的微生物量包括 MB-C、MB-N、MB-P 及MB-S等[5-7]。研究從土壤微生物量的效應著手,通過測定土壤碳氮含量,探討退耕還林還草后土壤內在機制的變化,以期為該地區的生態安全和生態恢復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選取了4個位于自然恢復演替階段(草叢-灌叢-次生林-原生林)作為研究對象,試驗樣地的基本情況見表1。
通過野外勘查研究區自然植被分布,確定不同植被典型樣地,于2006年6月(雨季)和12月(旱季)采集土壤樣品。喀斯特植被演替過程4個階段樣地結合調查地上植被多樣性的樣方:草叢(5 m×5 m)、灌木叢(10 m×20 m)、次生林和原生林(20 m×40 m);除草叢外,其余樣方均分成4個等面積的小樣方,選擇其中3個小樣方,每個樣地按“S”形確定5~8個取樣點,采集表層0~15 cm土壤樣品混合成一個混合樣品。對于農業耕作土壤,選取典型樣地,隨機選取3個取樣小區(3個重復),每個小區按“S”形選取15~20個取樣點,采集表層0~15 cm土壤組成一個混合樣品(混合均勻)。樣品過2 mm無菌篩,部分樣品保存在4℃冰箱中用于平板培養與微生物碳氮等分析;余下樣品風干保存用于土壤理化性質分析。

表1 試驗樣地的基本概況
1.2 方法
微生物量碳、氮的測定:氯仿熏蒸K2SO4提取法。提取液中C采用總有機碳自動分析儀測定,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的計算:BC=EC/kEC。式中:EC=熏蒸土壤浸提的有機碳-不熏蒸土壤浸提的有機碳,kEC為轉換系數,取值0.45。提取液中N采用流動注射儀測定,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計算:BN=EN/kEN。式中:EN=熏蒸土壤浸提測定的全氮-不熏蒸土壤浸提測定的全氮;kEN為轉換系數,取值0.45。
土壤基礎呼吸作用測定:堿液吸收-TOC儀測定法:稱取25 g上述測定土壤微生物碳氮用的新鮮土樣于500 mL培養瓶中,并將土壤均勻地平鋪于底部,將一只25 mL小燒瓶放在培養瓶內的土壤上,然后吸取1 mol/L的NaOH溶液10 mL放入其中,將培養瓶加蓋密封,在25±1℃培養24 h取出于TOC儀上測定C濃度并計算CO2-C釋放量,同時做空白對照。
土壤呼吸R=未熏蒸土壤釋放CO2-C/10,R的單位為 mg/kg·d,呼吸熵(qCO2):形成單位微生物量C所需呼吸的CO2-C量;qCO2=R/微生物量C×1 000,單位為 mg/g·d。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植被恢復后土壤的物理屬性
從表2可以看出,隨著退耕還林后植被恢復的正向進行,除次生林以外土壤的pH值是逐漸增高的,表現出原生林>灌叢>次生林>草叢。容重則正好相反,表現出草叢>灌叢>次生林>原生林。但pH和容重在每個恢復階段的季節之間變化不明顯,說明在短期時間里,pH值和容重基本是穩定的,受外界環境影響較小。因為土樣采集時間的不同(6月是雨季,12月是旱季),在每個恢復階段中差異較大且土壤的含水量均為6月>12月。隨著植被恢復,土壤植被類型的不同,各階段的土壤含水量也存在差異,6月土壤含水量是:原生林>次生林>灌叢>草叢;12月除原生林是0.29外,也是:次生林>灌叢>草叢。因為植被類型是影響土壤化學和生物化學性質的主要因素,其直接影響到土壤的含水量。原生林可能因其蒸騰量較大,根系從土壤中吸水較強,導致其土壤的含水量較次生林小。但在不同的月份,其土壤的基本屬性(pH值、容重和土壤質地)相同,因此不會對以下的分析造成影響。

表2 不同植被恢復后土壤的物理屬性
2.2 不同植被恢復后土壤微生物量、呼吸強度和qCO2值分析
土壤微生物量是指土壤中體積小于5×103μm3、具有生命活動的有機物質的總量,是土壤物質和能量循環轉化的動力,是表征土壤肥力特征的重要參數之一[8-9]。從表2可以看出,不同植被恢復后土壤微生物量差異顯著,微生物量碳從高到低為:次生林>原生林>灌叢>草叢,在季節上草叢和原生林都為12月份大于6月份;灌叢和次生林為6月份大于12月份,結果6月份次生林是原生林的1.31倍,灌叢的1.93倍,草叢的7.91倍;12月份次生林是原生林的1.19倍,灌叢的2.55倍,草叢的4.14倍。微生物量氮除灌叢外均表現為12月份高于6月份且是草叢的3.37倍,次生林的1.20倍,原生林的2.42倍,不同的演替階段6月份為:次生林>原生林>灌叢>草叢,12月份是:原生林>次生林>灌叢>草叢。微生物量碳和微生物量氮與土壤有機碳、全氮變化趨勢基本相同。
Jenkinsont研究認為,在無外部因素干擾的情況下,土壤微生物量并不能完全反映微生物的活性、結構和功能,因此在分析微生物量的絕對量外,還應考慮微生物量碳、氮在全碳、全氮中所占的比例,從微生物學角度揭示植被恢復過程中土壤生物學質量的變異[8]。從表2可以看出,不同植被恢復后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占全碳、全氮的比例變化不同,其中6月份微生物量碳占全碳的比例為2.70%~4.97%,微生物量氮占全氮的比例是2.47%~5.94%;12月份微生物量碳占全碳的比例為2.93%~3.74%,微生物量氮占全氮的比例是3.58%~6.98%。在6月份從草叢到灌叢其微生物量碳增幅較快,比例最高的是次生林為4.97%;12月份沒明顯的規律,但次生林的比例還是最高為3.74%,其微生物量氮也沒什么規律,但草叢的比例最高。在6月份其微生物量氮從草叢到次生林是逐漸增加的且增幅較大,在原生林又快速降低。有研究報道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占有機碳、全氮的比例分別為0.27%~7.0%、2%~6%。本研究發現,微生物量碳和氮所占比例相對偏高,在退耕還林的喀斯特地區土壤有機碳和氮素含量較貧瘠,微生物代謝功能期短,要維持植物生長所需要的碳源、氮源和營養物質,則必須提高微生物量在有機碳和全氮中所占比例和持續性來維持高的有機物代謝和物質循環。
微生物量碳氮比可以反映土壤微生物種類和區系。在植被恢復過程中,由于植被的不同,植被凋落物與根系統物質分解過程中所誘導形成的微生物區系差異導致土壤微生物量碳、氮比例也不同。表2顯示,在每個階段微生物量碳氮比均是6月份高于12月,這與土壤有機碳氮比是一致的。說明由于植被、環境的影響和微生物自身的因素,土壤氮素含量較高后續供應能力較強,在12月份微生物活動較6月份活躍。
土壤呼吸作為土壤質量和肥力的重要生物學指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壤養分轉化和供應能力,表征著土壤的生物學特性和物質代謝強度。在生態恢復過程中,植被的變化通過吸收養分和歸還有機物等影響著土壤的物理、化學和生物學性質,土壤微生物呼吸隨之變化,指示著系統恢復中土壤質量的演變過程。如表3所示,植被恢復后土壤微生物呼吸強度是逐漸增強的,表現為原生林>次生林>灌叢>草叢,和有機碳變化過程相同,說明作為呼吸基質的有機碳對呼吸強度有重要的控制作用。季節變化也影響土壤微生物呼吸強度,表現出與微生物量碳氮比相反的規律(12月份大于6月份)。

表3 不同植被恢復后土壤微生物量、呼吸強度和qC02值(n=3)
代謝熵(qCO2)是基礎呼吸強度與微生物量碳的比率。qCO2效率高,則形成單位微生物質量所呼出的qCO2少,qCO2較小;qCO2效率低,說明利用相同能量而形成的微生物量小,qCO2較大,釋放的CO2較多,微生物體的周轉率快,平均菌齡低。由表2可以看出,從草叢到原生林qCO2是12月份的效率高于6月份的,這與土壤微生物呼吸強度表現出相同的規律。由于植被的恢復,減少了人為的干擾,從草叢到次生林qCO2逐漸降低,保證了高的代謝效率,使土壤有充足的活性有機物,維持較好的土壤性狀和可持續利用潛力。原生林由于無人為干擾且各方面都趨于收支平衡,qCO2升高。次生林的qCO2效率最高,可能因為在適度的干擾下,物種增多,為微生物代謝提供可利用的物質變豐富,微生物群落的食物網復雜化,其能量基本用于維持自身正常的生命活動。
3 總結與討論
隨著退耕還林后植被恢復的正向進行,除次生林以外土壤的pH值是逐漸增高的,表現出原生林>灌叢>次生林>草叢,而容重變代表現出相反的規律。同時土壤含水量也存在差異,6月土壤含水量是原生林>次生林>灌叢>草叢;12月除原生林外也是次生林>灌叢>草叢。因為植被類型是影響土壤化學和生物化學性質的主要因素,其就直接影響到土壤的含水量。
不同植被恢復后土壤微生物量發生很大變化,微生物量碳從高到低為次生林>原生林>灌叢>草叢,在6月份從草叢到灌叢其微生物量碳增幅較快,12月份沒明顯的規律。在季節上差異表現為草叢和原生林都為12月份大于6月份;灌叢和次生林為6月份大于12月份。微生物量氮除灌叢外表現出灌叢和次生林微生物量碳同樣的規律,在6月份其微生物量氮從草叢到次生林逐漸增加,且增幅較大,在原生林又快速降低。而且這兩種都與土壤有機碳、全氮變化趨勢基本相同,但與全碳、全氮的比例變化不同,6月份微生物量碳占全碳的比例為2.70%~4.97%,微生物量氮占全氮的比例是2.47%~5.94%;12月份微生物量碳占全碳的比例2.93%~3.74%,微生物量氮占全氮的比例是3.58%~6.98%,這與前人研究相似,但比例偏高,使得微生物代謝功能期較短,須提高微生物量在有機碳和全氮中所占比例和持續性來維持高的有機物代謝和物質循環。
在每個階段微生物量碳氮比均是6月份高于12月,這與土壤有機碳氮比是一致的。說明由于植被、環境的影響和微生物自身的因素,土壤氮素含量較高后續供應能力較強,在12月份微生物活動較6月份活躍。植被恢復后土壤微生物呼吸強度是逐漸增強的,表現為原生林>次生林>灌叢>草叢,和有機碳變化過程相同,季節變化也影響土壤微生物呼吸強度,表現出與微生物量碳氮比相反的規律(12月份大于6月份)。從草叢到原生林qCO2表現同土壤微生物呼吸強度隨季節變化相同的規律,且草叢到次生林是逐漸降低的,可能因為原生林在適度的干擾下,物種增多,為微生物代謝提供可利用的物質變豐富,微生物群落的食物網復雜化,其能量基本用于維持自身正常的生命活動,使其qCO2升高。
[1] 李香真,曲秋皓.蒙古高原草原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特征[J].土壤學報,2002,39(1):98-104.
[2] 龍 健,李 娟,滕 應,等.貴州高原喀斯特環境退化過程土壤質量的生物學特性研究[J].水土保持學報,2003,17(2):47-50.
[3] 張茹琴.氣候變暖對玉米生長及其土壤微生物數量的影響[J].安徽農業科學,2010,(12):6409-6411.
[4] 陳國潮.土壤微生物量測定方法現狀及其在紅壤上的應用[J].土壤通報,1999,30(6);284-288.
[5] 何振立.土壤微生物量及其在養分循環和環境質量評價中的意義[J].土壤,1997,2:61-69.
[6] 劉益仁,徐陽春,李 想,等.有機肥部分替代化肥對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及礦質態氮含量的影響[J].江西農業學報,2009,21(11):70-73,79.
[7] 李倩茹,符夏梨.紅樹林土壤微生物與土壤酶活性分析[J].廣東農業科學,2009,(7):93-96.
[8] 薛 莛,劉國彬,戴全厚,等.不同植被恢復模式對黃土丘陵區侵蝕土壤微生物量的影響[J].自然資源學報,2007,22(1):20-27.
[9] 沈寶明,肖嫩群,楊春曉,等.保護性耕作方式對土壤微生物的影響研究進展[J].湖南農業科學,2010,(1):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