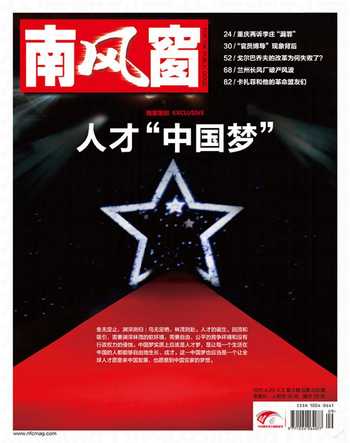改革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防止“三權(quán)交易”
李永忠
權(quán)錢交易、權(quán)色交易、權(quán)權(quán)交易等“三權(quán)交易”作為隱秘性越來(lái)越深、腐蝕性越來(lái)越大、滲透性越來(lái)越強(qiáng)、危害性越來(lái)越烈、風(fēng)險(xiǎn)性越來(lái)越高的現(xiàn)代典型腐敗現(xiàn)象,引起了黨和政府以及反腐敗職能部門的高度關(guān)注。
對(duì)于利用政策制訂調(diào)整的決策權(quán)、行政審批管理的執(zhí)行權(quán)、執(zhí)法執(zhí)紀(jì)的監(jiān)督權(quán)、干部選拔任用的人事權(quán)等搞官商勾結(jié)、權(quán)錢交易、瀆職侵權(quán)的腐敗案件,從中央到地方加大了懲治力度。近10年來(lái)查處的省部級(jí)高官就達(dá)100多人,其中處以死刑的有胡長(zhǎng)清、成克杰、王懷忠、呂德彬、鄭筱萸、段義和等6人。截至2009年,全國(guó)共查處商業(yè)賄賂案件6.92萬(wàn)多件,涉案金額165.9億元。中國(guó)公眾對(duì)反腐敗的滿意度、公眾認(rèn)為消極腐敗現(xiàn)象得到一定遏制的程度和國(guó)際社會(huì)的認(rèn)同度都有明顯上升。
“三權(quán)交易”為主要特征的腐敗現(xiàn)象從主觀上講是世界觀、權(quán)力觀、地位觀的扭曲。歸根到底,反腐敗斗爭(zhēng)的過(guò)程,就是腐敗形式不斷多樣化和反腐敗方略不斷制度化的博弈過(guò)程。
深化以“獨(dú)立性”為趨向的體制創(chuàng)新
早在2000年前,秦漢王朝就進(jìn)行了監(jiān)察機(jī)構(gòu)獨(dú)立于執(zhí)行機(jī)構(gòu)、監(jiān)察區(qū)域大于行政區(qū)域的配置實(shí)踐;近百年前,列寧就提出要從制度上保障專門監(jiān)督機(jī)關(guān)的“最大限度的獨(dú)立性”,并將這一原則細(xì)化落實(shí)為“兩個(gè)平行”(黨內(nèi)監(jiān)督機(jī)構(gòu)與執(zhí)行機(jī)構(gòu)相平行、黨的領(lǐng)導(dǎo)班子成員之間表決權(quán)和監(jiān)督權(quán)相平行)的制衡體制。近些年來(lái),為了打好反腐敗這場(chǎng)“沒(méi)有硝煙的戰(zhàn)爭(zhēng)”,中央不斷總結(jié)和借鑒各方經(jīng)驗(yàn),加大反腐敗專門機(jī)構(gòu)的體制改革和創(chuàng)新,發(fā)揮專門機(jī)構(gòu)的“監(jiān)督制衡力”。
面對(duì)“三權(quán)交易”的滋生蔓延,特別是防范和治理“權(quán)權(quán)交易”中各種權(quán)力對(duì)監(jiān)督權(quán)的侵占、掠奪、替代或異化、虛化、弱化,中央注重從改革黨內(nèi)派駐制度和巡視制度入手,深化紀(jì)檢監(jiān)察體制和司法體制改革,強(qiáng)化審計(jì)機(jī)關(guān)職能,積極探索監(jiān)督權(quán)的獨(dú)立配置問(wèn)題,力求變同體監(jiān)督為異體監(jiān)督。推行派駐機(jī)構(gòu)統(tǒng)一管理,指導(dǎo)基層和地方探索派駐機(jī)構(gòu)分片、分線、分層組建;創(chuàng)新黨內(nèi)巡視制度,強(qiáng)化巡視機(jī)構(gòu)和力量,延伸巡視對(duì)象和領(lǐng)域;完善紀(jì)委書記、法院院長(zhǎng)、檢察院檢察長(zhǎng)、公安局長(zhǎng)等反腐敗機(jī)構(gòu)主職官員異地任職制度;出臺(tái)一系列關(guān)于加強(qiáng)地方和基層各專門監(jiān)督機(jī)構(gòu)建設(shè)的政策措施,從經(jīng)費(fèi)、裝備、人員上給予保障和支持,逐步解決“再鋒利的刀刃也砍不了刀把”的監(jiān)督與被監(jiān)督一體化的問(wèn)題。
當(dāng)前我國(guó)監(jiān)督力量分散,監(jiān)督成本居高,監(jiān)督效能偏低的問(wèn)題較為嚴(yán)重,不能有效適應(yīng)“兩個(gè)仍然”的反腐敗形勢(shì)和防治“三權(quán)交易”腐敗的新要求。因而,在中央的統(tǒng)一部署的支持下,各地開(kāi)展了一些有導(dǎo)向意義的探索。2010年以來(lái),廣東佛山市學(xué)習(xí)借鑒香港廉政公署權(quán)責(zé)統(tǒng)一、有效打擊和遏制腐敗的成功經(jīng)驗(yàn),開(kāi)展了反腐敗體制改革的調(diào)研論證工作,邀請(qǐng)全國(guó)知名反腐專家集聚佛山研討謀劃改革路徑,分析改革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佛山市紀(jì)委30名干部在《南方日?qǐng)?bào)》發(fā)文呼吁將市檢察院反貪局和反瀆職侵權(quán)局從檢察機(jī)關(guān)分離出來(lái),與監(jiān)察、審計(jì)職能重組合并,組建市監(jiān)察審計(jì)和反貪局,與市紀(jì)委合署辦公;成立一個(gè)由檢察院管理的對(duì)辦案機(jī)構(gòu)及其人員進(jìn)行監(jiān)督的專門機(jī)構(gòu),人員由檢察官、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民主黨派人士、記者及社會(huì)各方人士組成。同時(shí),考慮將市紀(jì)委機(jī)關(guān)和派駐機(jī)構(gòu)進(jìn)行精簡(jiǎn)重組優(yōu)配,加大上級(jí)紀(jì)委對(duì)下級(jí)紀(jì)委的管理力度,強(qiáng)化監(jiān)督職能,有效整合區(qū)域內(nèi)的反腐敗資源和監(jiān)督職能,試圖打造“內(nèi)地第一廉署”。
構(gòu)建防止利益沖突的監(jiān)管機(jī)制
賄隨權(quán)集。社會(huì)轉(zhuǎn)型時(shí)期,制度的漏洞成為“三權(quán)交易”滋生的土壤和條件。特別是隨著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建立健全,公務(wù)活動(dòng)中公共利益與黨員干部個(gè)人及家庭的私人利益之間的沖突越來(lái)越明顯,并引發(fā)了一些“三權(quán)交易”的典型腐敗案件。近年來(lái),中央先后制訂《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黨員領(lǐng)導(dǎo)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zhǔn)則》、《國(guó)有企業(yè)領(lǐng)導(dǎo)人員廉潔從業(yè)若干規(guī)定》、《關(guān)于黨政領(lǐng)導(dǎo)干部辭職從事經(jīng)營(yíng)活動(dòng)有關(guān)問(wèn)題的意見(jiàn)》、《關(guān)于嚴(yán)格禁止利用職務(wù)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dāng)利益的若干規(guī)定》等相關(guān)法規(guī),規(guī)范調(diào)整公共利益與領(lǐng)導(dǎo)干部個(gè)人利益、公務(wù)活動(dòng)與經(jīng)營(yíng)活動(dòng)、政治活動(dòng)與市場(chǎng)活動(dòng)的關(guān)系,逐步構(gòu)建防止利益沖突的制度監(jiān)管機(jī)制。
近日,中央紀(jì)委頒布《〈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黨員領(lǐng)導(dǎo)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zhǔn)則〉實(shí)施辦法》,明確了對(duì)于領(lǐng)導(dǎo)干部違反52個(gè)“不準(zhǔn)”行為的具體處理依據(jù)。對(duì)于領(lǐng)導(dǎo)干部“違規(guī)經(jīng)商辦企業(yè)”、“配偶子女違規(guī)經(jīng)商辦企業(yè)”等行為,除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給予黨紀(jì)處分外,還明確了相應(yīng)的組織處理措施;對(duì)于領(lǐng)導(dǎo)干部“違反規(guī)定多占住房”、“兼職取酬”等行為中涉及的物質(zhì)利益,根據(jù)有關(guān)規(guī)定明確了追繳措施。
針對(duì)日益嚴(yán)重的商業(yè)賄賂和跨國(guó)(境)商業(yè)賄賂等新型“權(quán)錢交易”問(wèn)題,先后制訂《采購(gòu)法》、《反壟斷法》、《招標(biāo)投標(biāo)法》等一系列制度法規(guī),重點(diǎn)治理工程建設(shè)、土地使用、資源審批等六大領(lǐng)域以及銀行信貸、證券期貨等方面的商業(yè)賄賂行為,依法打擊跨國(guó)(境)商業(yè)賄賂行為。同時(shí),健全領(lǐng)導(dǎo)干部報(bào)告事項(xiàng)制度,將領(lǐng)導(dǎo)干部的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yè)等情況列入報(bào)告內(nèi)容,完善領(lǐng)導(dǎo)干部出國(guó)(境)管理制度,防止“出逃門”事件發(fā)生;并推進(jìn)金融實(shí)名制度、公民信用保障號(hào)碼制度立法工作,為實(shí)行財(cái)產(chǎn)申報(bào)制度奠定基礎(chǔ)。
針對(duì)易發(fā)多發(fā)的“權(quán)色交易”問(wèn)題,2007年5月中央紀(jì)委首次將近親屬、情婦(夫)等“特定關(guān)系人”納入懲治法規(guī)制度之中;同年7月,“兩高”將情婦(夫)這類在“權(quán)—錢—色”腐敗鏈條中扮演樞紐角色的“特定關(guān)系人”納入《刑法》懲治范圍;2009年10月,“兩高”又確定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等罪名,將受賄罪的主體擴(kuò)大到國(guó)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和已經(jīng)離職的國(guó)家工作人員以及非國(guó)家公職人員,加大對(duì)“三權(quán)交易”的懲治力度。
針對(duì)資本市場(chǎng)內(nèi)幕交易等信息賄賂問(wèn)題,國(guó)務(wù)院辦公廳2010年11月轉(zhuǎn)發(fā)了中國(guó)證監(jiān)會(huì)等五部門《關(guān)于依法打擊和防控資本市場(chǎng)內(nèi)幕交易意見(jiàn)》,旨在加快建立內(nèi)幕信息的保密制度、知情人登記制度、信息披露和停復(fù)牌制度等,健全完善“操縱市場(chǎng)”和“內(nèi)幕交易”等行為的認(rèn)定指引和舉證規(guī)則。
針對(duì)用人上的“權(quán)錢交易”和“權(quán)權(quán)交易”問(wèn)題,組合式地構(gòu)建、集成式地發(fā)布干部選拔任用監(jiān)督制度。特別是近年來(lái),黨中央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升到“改革有風(fēng)險(xiǎn),但不改革黨就會(huì)有危險(xiǎn)”的高度來(lái)認(rèn)識(shí)和推進(jìn),基本上形成了事前要報(bào)告、事后要評(píng)議、離任要檢查、違規(guī)失職要追究的干部選拔任用監(jiān)督管理制度體系。
提高黨內(nèi)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的導(dǎo)向力
國(guó)際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dòng)實(shí)踐特別是蘇東劇變教訓(xùn)表明,制度最核心最具實(shí)質(zhì)的是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新時(shí)期的制度反腐,必須是主體以新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而非舊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為載體而開(kāi)展的反腐敗斗爭(zhēng)。健全有效的制度必然是科學(xué)合理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以“議行監(jiān)合一”為主要特征的“樹(shù)型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是權(quán)力變異和腐敗的“總病根”。徹底根治“三權(quán)交易”等腐敗現(xiàn)象,根本出路在制度改革,科學(xué)分解、合理配置黨內(nèi)的決策權(quán)、執(zhí)行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推行“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類型轉(zhuǎn)換”,不斷完善適合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尤其是我們黨內(nèi)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
因而,繼十七大首次明確部署“決策權(quán)、執(zhí)行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xié)調(diào)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建設(shè)問(wèn)題,十七屆五中全會(huì)又特別強(qiáng)調(diào)“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shè)計(jì)和總體規(guī)劃”。這既是我們黨對(duì)30多年前鄧小平提出并試圖解決的“權(quán)力過(guò)分集中”的“總病根”問(wèn)題認(rèn)識(shí)的深化和提升,又表明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類型轉(zhuǎn)換,即黨內(nèi)決策權(quán)、執(zhí)行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配置改革問(wèn)題已被作為政治體制改革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設(shè)的“頂層”目標(biāo)。
實(shí)踐中,近些年來(lái),中央鼓勵(lì)各地結(jié)合實(shí)際,不斷加強(qiáng)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的實(shí)踐探索和試點(diǎn)運(yùn)行總結(jié),逐步勾勒出黨內(nèi)“頂層設(shè)計(jì)”的方向標(biāo)和線路圖。
首先,通過(guò)擴(kuò)大黨代會(huì)常任制試點(diǎn),摸索黨內(nèi)決策權(quán)建設(shè)問(wèn)題。黨代會(huì)常任制按毛澤東50年代的想法,是要形成一個(gè)黨內(nèi)的“國(guó)會(huì)”,黨內(nèi)有人大常委會(huì)那樣的常設(shè)機(jī)構(gòu)來(lái)進(jìn)行黨內(nèi)決策。根據(jù)毛澤東的這一設(shè)想和八大的制度設(shè)計(jì)及其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中央不斷擴(kuò)大黨代會(huì)常任制試點(diǎn)。“十三大”后布點(diǎn)12個(gè),“十六大”后擴(kuò)大到近20個(gè),“十七大”后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開(kāi)展不同層級(jí)、不同區(qū)域的常任制試點(diǎn),推進(jìn)黨內(nèi)權(quán)力分解和黨內(nèi)決策權(quán)建設(shè)。
其次,通過(guò)擴(kuò)大縣委權(quán)力公開(kāi)透明運(yùn)行試點(diǎn),摸索黨內(nèi)執(zhí)行權(quán)分解問(wèn)題。包括我國(guó)在內(nèi)的世界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大都是按照140年前馬克思總結(jié)的巴黎公社革命政權(quán)模式,即“同時(shí)兼有立法和行政”的 “議行合一”模式建立的。實(shí)踐中,執(zhí)行權(quán)已取代或侵占了決策權(quán)、控制或異化了監(jiān)督權(quán),致使目前相當(dāng)多的地方和單位形成了空前的“一把手”體制,“權(quán)力過(guò)分集中”成為黨群疏離、三權(quán)交易、作風(fēng)變異和群體性事件多發(fā)的“總病根”。因此,中央從縣權(quán)改革入手,科學(xué)分解執(zhí)行權(quán),合理配置權(quán)力架構(gòu)。2009年3月,中央紀(jì)委、中組部分別選擇東部的江蘇睢寧、中部的河北成安、西部的四川武侯試點(diǎn)探索縣級(jí)黨委權(quán)力變革問(wèn)題。一年半后,中央決定試點(diǎn)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推開(kāi)。2010年11月,中央紀(jì)委、中組部印發(fā)《關(guān)于開(kāi)展縣委權(quán)力公開(kāi)透明運(yùn)行試點(diǎn)工作的意見(jiàn)》,著手在縣一級(jí)建立健全決策權(quán)、執(zhí)行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xié)調(diào)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和運(yùn)行機(jī)制,特別強(qiáng)調(diào)要編制職權(quán)目錄,尤其要加強(qiáng)對(duì)縣委書記職權(quán)的規(guī)范,暢通監(jiān)督渠道,形成制約監(jiān)督和反映問(wèn)題處理機(jī)制。
第三,通過(guò)擴(kuò)大監(jiān)督體制改革試點(diǎn),摸索黨內(nèi)監(jiān)督權(quán)配置問(wèn)題。當(dāng)前,黨內(nèi)監(jiān)督體制基本上是一種同體監(jiān)督,監(jiān)督權(quán)配置獨(dú)立性不強(qiáng),依附和受制于黨內(nèi)執(zhí)行權(quán),致使出現(xiàn)“看得見(jiàn)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jiàn)”的問(wèn)題。因此,中央在加強(qiáng)巡視機(jī)構(gòu)和派駐機(jī)構(gòu)兩個(gè)異體監(jiān)督的支點(diǎn)建設(shè)的同時(shí),支持地方進(jìn)行監(jiān)督體制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如江蘇東海縣紀(jì)委有效整合紀(jì)檢監(jiān)察力量,把分散在全縣24個(gè)鄉(xiāng)鎮(zhèn)和36個(gè)縣城機(jī)關(guān),承擔(dān)同體監(jiān)督任務(wù)的紀(jì)檢監(jiān)察干部,統(tǒng)一集中到縣紀(jì)委,分成8個(gè)工作室實(shí)施異體監(jiān)督,其中6個(gè)對(duì)農(nóng)村鄉(xiāng)鎮(zhèn),兩個(gè)對(duì)縣城機(jī)關(guān)。繼連云港市推廣后,江蘇省也在全省予以大力推廣。再如,2010年10月28日,十一屆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第十七次會(huì)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村民委員會(huì)組織法》從法律上明確規(guī)定“農(nóng)村應(yīng)當(dāng)建立村務(wù)監(jiān)督委員會(huì)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務(wù)監(jiān)督機(jī)構(gòu)”。
第四,通過(guò)擴(kuò)大基層選舉試點(diǎn),摸索權(quán)力來(lái)源的合法性問(wèn)題。因而,中央鼓勵(lì)地方開(kāi)展一定形式的試點(diǎn),貫徹落實(shí)“權(quán)為民所賦、權(quán)為民所用”的馬克思主義權(quán)力觀,探索權(quán)利制衡權(quán)力和權(quán)力回歸權(quán)利的規(guī)律性。2001年12月,四川遂寧市市中區(qū)步云鄉(xiāng)采用全鄉(xiāng)選民直接選舉產(chǎn)生唯一的鄉(xiāng)長(zhǎng)候選人,然后交鄉(xiāng)人代會(huì)進(jìn)行等額選舉的方式。同時(shí),2002年以來(lái),湖北、四川、江蘇、云南等地進(jìn)行了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的選舉試點(diǎn),分別出現(xiàn)了湖北楊集的“兩推一選模式”、咸安的“兩票推選模式”以及四川成都市新都區(qū)的“公推直選模式”。十七屆四中全會(huì)以后,全國(guó)各地加大了基層民主直接選舉、差額選舉制度和競(jìng)爭(zhēng)性選拔制度改革試點(diǎn)。
一部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史,既是一部權(quán)力擴(kuò)張與權(quán)力制約的歷史,也是一部腐敗與反腐敗的斗爭(zhēng)史,更是權(quán)力與權(quán)利的博弈史。防治“三權(quán)交易”,最大的公約數(shù)是權(quán)力和權(quán)利,最能發(fā)現(xiàn)問(wèn)題的機(jī)制是監(jiān)督,最有效的控制力量是制衡,最終實(shí)現(xiàn)制衡的法寶是民主與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