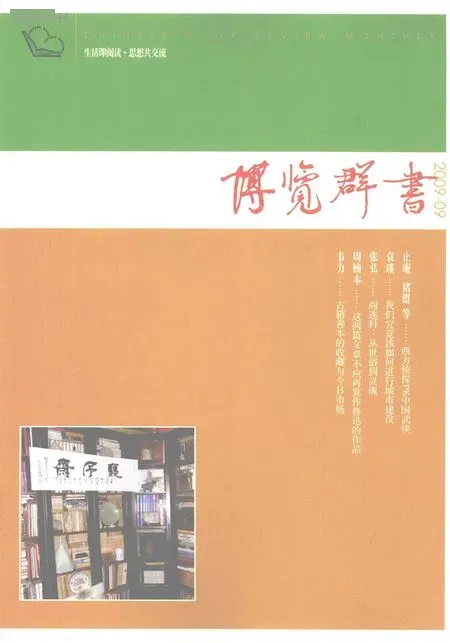四種妖魅作鄰居
○李俊領
四種妖魅作鄰居
○李俊領

《四大門》,李慰祖著,周星補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學術視野下的鄉村信仰世界
四大門是指四種具有神圣性的靈異動物,即狐門(也稱胡門,狐貍)、黃門(黃鼠狼)、白門(刺猬)和柳門(也稱常門,蛇)。這些靈異動物不是仙,也不是神,而是處在修仙階段的妖魅。在民國時期北平西北地區的鄉村中,人們普遍信仰四大門,并對它們保持著一種既敬畏又依賴,既利用又合作的復雜關系。要全面了解這個時期的平郊鄉村社會,就不能不了解四大門信仰。
自古以來談妖魅鬼神的文字作品多矣。從《墨子》到《抱樸子》,從《太平廣記》到《閱微草堂筆記》,從《子不語》到《聊齋志異》,可謂應有盡有。不過,《四大門》(李慰祖著,周星補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版)從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角度研究四大門信仰,還是破天荒的頭一次。當時就讀于這所大學的李慰祖先前對平郊鄉村的四大門信仰并不熟悉,完全是這個信仰世界的局外人。為了了解四大門的來源、特征及其在平郊鄉村中扮演的角色,作為鄉民與四大門對話的靈媒——“香頭”的選擇與儀式,他運用了人類學的“局內觀察法”,通過訪談鄉民,學習當地鄉村的地方性話語和知識,采集了大量生動的案例,對四大門信仰進行了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解釋。
鄉民生活中的四大門
四大門都是自開靈性的動物,但有家仙和壇仙之分,家仙直接住在普通的農戶家中,壇仙則住在“香頭”的家中。四大門中的每一門都是良莠不齊,有的務本參修,有的胡作非為。務本參修,就要內煉丹元,外修功德,目的是得道成仙。
四大門的修功德,主要是幫助鄉民生財致富,治病救災,解難決疑。其中生財功能頗受鄉民喜歡。比如黃門會幫全子修家多收幾擔瓜,常門會幫從山東逃荒到肖家莊的王老三迅速發家成一個大莊園主。(P16、17)一旦鄉民得罪了四大門,就會損失財產。清華園南邊有位楊姓鄉民靠著四大門發了家,后來對四大門的信仰逐漸淡薄,家中遂不斷發生不幸的事情,像牲口常死,有時牲口無故走失等,家道由此敗落。(P18)更嚴重的,四大門還會“拿法”鄉民,致其生病或瘋癲。
不是所有的四大門都具有鄉民無以對付的法力,有時也要對鄉民妥協一下,互利共處。《四大門》講了幾個這樣的例子。比如,平郊村黃則岑家的財神“白爺”在其豆腐房旁的干草堆中生了五只小“白爺”,黃則岑太太便給這些“白爺”供上飲食。幾日后,一只小“白爺”咬住了黃家的一只小雞的腳。黃則岑則祝念道:“我可沒錯敬了您,您要是禍害我,我可讓您搬家了。”次日,所有的“白爺”自行搬回了黃家的財神樓。(P24)
四大門在與鄉民交往中十分講究倫理的尊卑。在稱謂上,屬于“家仙”的四大門稱“胡爺”、“黃爺”等,屬于“壇仙”的四大門稱“老爺子”、“大仙爺”、“二仙爺”等,少數被稱為“姑娘”。顯然,四大門比普通的鄉民高出一個輩分,二者并不平等。壇仙往往秉持著“男女授受不親”的信念,也就是說,通常男患者由男的壇仙來治,女患者由女的壇仙來治。壇仙為患者治好病后,患者要燒香、磕頭為報。
四大門的法力雖然超人,但并不能支配一切的人,它們最怕人間的達官顯宦。后者的道行往往超過了四大門,而且四大門“雖然道行高深,畢竟屬于邪道,所謂邪不壓正,就是這個道理”。(P28)另外,還出現了強悍之人殺死常門的事情。《四大門》記載稱,民國初年,一位很喜歡吃“五毒”的旗人印某用石頭打死了燕京大學東南三里許的保福寺村張家財神樓住的一位“常爺”。(P8)
四大門是平郊鄉民難以回避的鄰居,它們或成為鄉民的家仙,或成為社區的壇仙。成為壇仙的四大門會強行選擇一些人作為自己的“當差的”,這些人被“拿法”之后,即為四大門代言行道(即醫病、除祟、禳解、指示吉兇等方術),并負責供奉四大門。這些“當差的”就叫做“香頭”,“香頭”的確立要經過“認師”、“安爐”、“安龕”、“開頂”一系列的典禮儀式,還要準備神壇的塑像、香爐、蠟燭等設施,平時每天要早中晚三次上香。平郊西北區的香頭們還要定期到圣山進香,即“朝頂”。他們所謂的圣山是北京當地的天臺山、東岳廟、丫髻山、妙峰山、李二寺(在今北京通州)和潭柘山的岫云寺,總稱“五頂”。
四大門的香頭“朝頂”主要拜的是道教中的女神碧霞元君,即泰山老奶奶。碧霞元君怎樣成為總司四大門的女神,是一個十分值得探討的問題。但作者對此沒有交代,只是提到“東大山(即丫髻山)、妙峰山、天臺山三處的娘娘乃是親生的三姊妹,總管各地的四大門仙家,四大門對于娘娘便等于屬員對于上司的身份一樣”(P25);四大門的大本營在丫髻山,該處由王奶奶直接統轄,而“‘老娘娘’(即‘碧霞元君’,又稱‘天仙圣母’)又是王奶奶的直轄上司”。(P56)
《四大門》記錄了很多四大門與鄉民鄰居交往的案例,但沒有數量的統計和分析。這給人的印象是,平郊鄉村中四大門的故事經常發生,但不知道一個村莊一年中會發生多少這樣的故事。不過,四大門的故事并沒有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終結,而是頑強地延續下來。
我所耳聞目睹的一些怪事
讀《四大門》,我不由地想起自己耳聞目睹的一些“見鬼”經歷。
那是1994年夏天的一個夜晚,在家鄉縣城魯西南賓館臨街的樓下,我和兩個同學打地鋪,準備露天而眠,八九米外就是車來車往的馬路。晚十時余,我們正準備休息,忽見地鋪右邊兩米處有一只白色的兔子。我十分驚奇,誰家的兔子這么晚了還出來逛街?按理說,城里人不會在大街上放養兔子啊。為了弄個究竟,我起身去追這只白兔,剛靠近一步,它就沿著樓房的墻根閃過幾步。當時我想,這里不是樓房,就是水泥鋪的空地,看這兔子能跑到哪里去,索性接著追。不幾步,這兔子在距我不到一米的地方貼著墻不見了。這時心里閃出一個念頭,撞上邪氣了。第二天,我將這件事告訴了父母,他們說我可能是遇到“萬年白”了。
依照家鄉的說法,“萬年白”是成精的狐貍。據說修煉千年的狐貍呈黑色,而修煉萬年的狐貍呈白色,故民間有“千年黑,萬年白”的說法。后來知道這種情況在別地兒的鄉村也發生過,人們將“千年黑,萬年白”的靈異狐貍叫做“仙皮子”。看來“狐門”并沒有銷聲匿跡,還在不斷地上演和人類交往的故事。當然,有人說兔子也可以成為靈異的動物,稱為“白門”。(P6)
黃門和狐門一樣,還在和人打交道。2010年我在北京平谷區的太后村做調查,從該村黨支部書記李成國那里得知,當地一位常年獵捕黃鼠狼的農民獵手的老母前不久被黃門“拿法”了。原來這位獵手近期打死了一只老黃鼠狼,用其毛皮做了一件大衣的領子。為了報殺身之仇,這黃門用其法力“拿法”了獵手的老母,借其口大罵獵手喪盡天良,還瘋瘋癲癲地砸壞了家中的不少器具,攪得左鄰右舍不安寧。獵手感覺了黃門的厲害,急忙擺供上香,向黃門請罪。幾經折騰,后來這黃門總算放了獵手的老母。
此外,我曾拜訪過類似四大門香頭的靈媒。2001年,在作家畢玉堂的幫助下,我見到泰安城中的一位靈媒賈老太太。印象中,她住在泰安市長途汽車站附近,家里單獨辟有一間敬神的凈室,香案上有五六位神像,其中有道教的神仙呂洞賓,其他的神不知出自哪一門(呂洞賓與四大門關系密切,《四大門》附錄的《乩壇實錄》中特地記錄了呂洞賓與狐門的朋友關系)。據她說,不必天天為這些神上香,每天誰當班,就給誰上香。幾乎天天都有前來向靈媒問事的人。問事者的基本禮節,是給當班的神下跪磕二十個頭,給賈老太太的香火費則不拘數額。要特別說明的是,賈氏所頂的神們有個禁忌,即不接受處在月經期的女性的跪拜,這倒是和四大門中壇仙的禁忌沒有兩樣。(P27)賈老太太上香后,先看燃香的火光,判斷神是否樂意接受問事者的供祀。然后,她連續打幾個哈欠,接著開始代神說話,解答問事者的疑慮或其他所求。這與《四大門》中講的京郊西柳村的香頭王姓下神的方式是一樣的。(P69)
賈氏頂神的靈驗問題是我最關心的。據熟悉她的作家畢玉堂介紹,賈氏頂的神確有靈力,但她所判斷的事情有些很準,有些很不準。比如這位作家曾請她幫忙找一份自己忘記放于何處的房產證,后來果然在其指點下找到了。再比如,賈氏曾向所頂的神問自家兒媳所懷的娃是男娃還是女娃,神說是男娃,但后來兒媳生的是個女娃。賈氏代神斷事的準與不準,倒不是依據通常理性判斷是與否的概率問題,而應看成是她以某種我們還不熟悉的方式獲取信息多與少的問題。
前面說過,四大門的總管是泰山老奶奶——碧霞元君。這位女神也不是僅僅活在人們的精神世界中,而是像四大門一樣可以降神附體,并可以與其信眾對話、逗樂。民俗學專家葉濤教授在《泰山香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中說,他曾實地采訪過山東省鄒城市的泰山香社會首劉緒奎,這位會首登泰山后石塢元君廟就會降下碧霞元君的神靈,為隨行的信眾、香客解困答疑,賜福禳災,還能代碧霞元君識別出前來供奉的香客誰是誠心的,誰不是誠心的(參見《泰山香社研究》P172—175)。很難說降神附體是劉緒奎的騙術,但也很難解釋他的那種類似“他心通”的超常獲取信息的能力。
四大門及其主管神靈與人交往的故事還在繼續發生,但這些故事只和某些普通的民眾有關系。對于沒有這樣的經歷,也不相信這些靈異動物存在的人而言,《四大門》不過是民國生活版的《聊齋志異》而已。
怎樣理解四大門信仰的奧秘
李慰祖在考察平郊鄉村四大門信仰時提出了兩個問題,至今仍值得進一步思考。
第一,四大門信仰屬于何種宗教信仰體系。在李慰祖看來,平郊鄉村的四大門信仰和佛教、道教有些關聯,但并不屬于任何宗教信仰體系。周星則認為四大門是一種民俗宗教。如果嚴格從西方文化對宗教概念的界定來說,不宜說四大門是一種多神信仰的民俗宗教,因為鄉村的四大門信仰沒有系統的教義,即使是比四大門信仰更具有組織形態的泰山香社也不宜被視為一種信仰碧霞元君的宗教。
在我看來,四大門信仰更像是一種類似薩滿教的巫術,而且這種巫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復的可操驗性。李慰祖曾提到北平南長街土地廟的王香頭可以現場“下神”,證實給前來抄家的警察看。(P81)不易解釋這種巫術的內在機理,但似不宜簡單地將它視為騙術。
李慰祖認為,四大門信仰的基礎是精氣信仰與“萬物有靈”的理論。不過,他并沒有作進一步的解釋。依據佛教、道教的看法,“萬物有靈”論真實地反映了世界的本相,而且原始社會的人類祖先普遍具有這種觀念。當然,文化水平較低的鄉民并不能深刻解釋四大門信仰背后的認識方式、思維方式以及世界本相等問題,但他們依靠世代相傳的經驗和自身的直覺,能妥善處理好自身與四大門的鄰居關系,正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
四大門信仰反映了什么樣的世界本相與秩序呢?從《四大門》的諸多案例可以歸納如下:世界有五個層次,即神、仙、人、妖、鬼。神界如碧霞元君,仙界如王三奶奶,人界如黎民百姓,妖界如四大門,鬼界如某些人死后的鬼魂。這五界的能力有高下,地位有尊卑,以神為最高,其下依次為仙、人、妖、鬼。
第二,四大門信仰與香頭制度在社區中表征著什么,又扮演著什么角色。李慰祖認為,四大門的仙家是農民道德理想的結晶,也是尊卑禮教的維護者。(P108)香頭是鄉民生活的指導者、鄉民貧富的調節者、鄉民家庭的保護者,還是社會關系的核心。一言以蔽之,他認為“以四大門信仰為基礎,香頭制度的功能是維持社會秩序”。(P110)
香頭制度是因為“有功能所以存在”,不是因為存在而有功能。(110)香頭制度的這種功能并不是建立在鄉民無知的基礎上。李慰祖明確說道:“有人認為,信仰四大門乃是鄉民無知的表現,香頭乃是欺騙愚人的。此種說法完全不合事實,從許多方面看去,鄉民的知識比較我們的絕不為少。他們辨別是非的能力,并不比我們弱。”(緒論,P2)但直到今天,仍不乏對草根社會四大門信仰不屑一顧的傲慢與偏見。
香頭制度存在的一個重要基礎是治“邪病”,這也是我們認識世界本相與秩序的一個重要窗口。周星在補編里提到,在華北鄉村社會中,鄉民所患的醫院無法治療的所謂“邪病”或“虛病”不能不請香頭治療。(P185—186)這種治療往往費用少,效率高,很少被鄉民看作是迷信。當然,這不是說沒有投機者裝神弄鬼,借機斂財。季羨林先生在《憶往述懷?寸草心》中講了其亡母的魂靈附體在自家一位女親戚身上說話的故事,直覺到“邪病”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精神意識狀態,它意味著世界可能還有另一種被遮蔽的本相與秩序。南懷瑾近年反復提到一個問題,即重新認識中國傳統的認知科學與生命科學。也許,從這里可以找出對四大門信仰更具有解釋力的答案。
在傳統文化已經斷層的今天,能否真正理解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傳統鄉村社會,尤其是鄉民的四大門信仰與生活禮俗,而且不會有“隔”的感覺,這考驗著我們這一代學者的功力,更考驗著我們的良知。
(本文編輯 宋文佳)